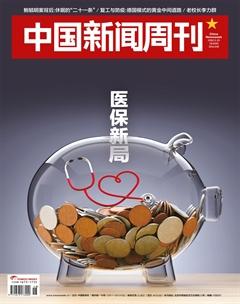杜倫:英格蘭小鎮的詩與生命
曹然

威爾河與大教堂。
“詩”與“生命”是中國詩人顧城給杜倫的獻辭。1987年秋,他應好友、在杜倫大學任教的詩人北島的邀約,來到這座孤懸英格蘭東北、遠離所有中心城市的小鎮。他將自己的詩集《黑眼睛》簽贈給了杜倫大學,并在襯頁上寫下了這兩個簡單而精妙的詞。
今天的杜倫和顧城題辭的時代沒什么區別。從南方駛來的、日常晚點的火車經過一座凌空的大橋,首次北上的旅客會驚嘆于窗外的景象:郁郁蔥蔥的山林間,宏偉的大教堂及城堡巍峨聳立,臨于小鎮之上。威爾河在這里折返,留下蜿蜒的河道,孕育了英國賽艇運動。
大教堂是小鎮繞不開的風景。無論是在北島多次流連的古橋橋頭,還是在濃蔭匝地的河畔小徑,抑或是在野兔和松鼠出沒的草坡,抬頭一望,諾曼式的莊嚴高塔必然出現在眼前。自征服者威廉建杜倫鎮以來,一千余年,一直如此。

開學典禮時的大教堂內景。

威爾河上的賽艇比賽。
12世紀的盎格魯-撒克遜詩人詠嘆大教堂“建于石壁之上,聲名彰于全境”。并非因為有幾位圣徒埋骨此地,而是因為,從諾曼征服直到1707年英格蘭和蘇格蘭正式合并、組建大不列顛王國,一代代杜倫主教和諾森伯蘭公爵是英格蘭的守護者。他們在北部邊疆抵抗蘇格蘭進攻,一晃就是600多年。
在杜倫讀書時,我有時會去大教堂的圖書館自習。那里屏蔽網絡,三三兩兩的學生坐在寬大的木桌前查閱古籍。1215年起草的《大憲章》的幾個早期抄本就保存在這個圖書館,最早的是抄于1216年12月的一個不完整本。近千年前,圖書館所在之地是僧侶們的宿舍。蘇格蘭人逼近時,他們枕戈待旦,隨時準備在威爾河對岸的密林中與敵廝殺。
杜倫大教堂是第一批世界文化遺產、諾曼建筑的象征,現在是杜倫大學舉行開學和畢業典禮的會堂,也是很多電影的取景地:霍格沃茨魔法學校的中庭、漫威宇宙中奧丁的宮殿。考古學家仍不時從這里掘出蘇格蘭戰俘的頭骨。
感受大教堂最好的方式,是聽一次教堂音樂會或管風琴演奏。前年年底,從這里走出的西敏寺管風琴樂手回歸故里。那樂聲仿佛是順著厚重的石板升起,又仿佛是從穹頂傾瀉而下,令聽者顫栗。杜倫大教堂流傳著許多恐怖傳說,據說有不少冤魂在里面飄蕩,或許,跟這從天而降般、威嚴而壓迫的“天籟之音”也有關系。
17世紀的光榮革命后,北部無戰事。1832年,英國議會通過立法,正式建立英格蘭第三所大學——杜倫大學。杜倫主教范米爾德特捐出整座城堡,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向大學圖書館捐獻了自己的詩集。
華茲華斯成為杜倫大學授予的第一位榮譽文學博士,這似乎奠定了杜倫大學獨特的詩歌傳統。我所在的特里維廉學院,因為當年的第一次開學典禮上有新生家長演奏為學院創作的小夜曲,從而形成了重視音樂的院風。這位家長,就是憑《桂河大橋》配樂拿下奧斯卡小金人的馬爾科姆·阿諾德。
不過,杜倫大學的文藝氣息并不完全來自華茲華斯代表的浪漫主義思潮。小鎮往東三公里,一座古樸的莊園隱藏在精致的法式花園之后。這是9年前停止招生的烏肖學院,她源于歐洲大陸的保守主義,由一群躲避法國大革命的天主教僧侶創建。
1863年,一位年輕人踏上烏肖學院主樓深紅色的木地板。人們很難想象,從杜倫最保守的學院走出的希臘學生帕特里克·赫恩,很快就因描寫日本風物的小說成為19世紀末溝通東西方文明首屈一指的作家。他甚至給自己取了一個日本名:小泉八云。
今天,穿過小鎮南郊埃爾微山的幾條小徑,小泉八云的紀念碑豎立在一片四季常綠的山坡上。上世紀末,北島曾無數次爬上這段山坡,走向一棟古樸的老宅。200年來,小鎮與大學不斷融合,大學的院系零散分布在城里與郊外的各個角落。即使后來興建了主校區,游客依然可以在街邊的二層小樓前看到“杜倫大學哲學系”這樣的招牌。
北島走向的是他任教的東方學院。上世紀50年代,英國政府出于冷戰需要,資助杜倫等六所高校大力開展東方學研究。令英國的麥卡錫們沒想到的是,杜倫最大的一筆東方學經費開支并不是用于政治研究,而是從杜倫校長、外交家馬爾科姆·麥克唐納手中買下他的全部瓷器收藏。麥克唐納1962年曾到訪過中國。
今天,游客們可以在杜倫東方博物館里看到這批英國規模最大的中國瓷器收藏。精美的白瓷和藍釉的三彩器是海外罕見的珍品。樓上是馳名世界的埃及文物,包括獨一無二的公元前14世紀寫實主義女孩木雕。
這座英格蘭小鎮與東方還有更深的淵源。在新冠病毒肆虐的今天,許多杜倫人會提起現代流行病學的奠基人之一約翰·斯諾。他曾在紐卡斯爾的醫學校受訓,那是杜倫醫學院的源頭之一。他的老師之一是杜倫首位生物學教授詹姆斯·約翰斯頓。
就在約翰·斯諾首次發現倫敦霍亂流行方式的同期,約翰斯頓寫出了他的代表作 《日常生活中的化學》。這本書很快從威爾河畔傳播到長江兩岸,1890年由傅蘭雅等譯出中文本《化學衛生論》。8年后,一位在南京求學的紹興青年讀到這本中國最早的生化科普讀物。受這些譯介新書的影響,他東渡扶桑學醫。再之后,他棄醫從文,取筆名“魯迅”,并在《吶喊》自序中回顧了這段讀書經歷。
2019年夏季的一天,我在杜倫大學主圖書館的移動書柜間翻查,發現一套未經登記的書。那是1934年,魯迅已成名于文壇,他和鄭振鐸合作刊印《北平箋譜》,隨后分贈歐美高校和圖書館,杜倫這套或許是其中之一。
這里還有老舍、蕭乾等中國現代作家的簽贈本。有些書的源流,東方學院前院長司馬麟也說不清楚。不過,它們都印證著杜倫人常感慨的話:“這里離塵世很遠,卻離世界很近。”
告別杜倫前,我將一批從歐洲各地淘來的中英文舊書留給了學院圖書館,圖書管理員欣然接受了這點心意。離開學院時,我看到他的新作剛剛掛上學院的墻:五幅抽象的油畫,用濃重的色彩光譜和宇宙星空般的排列象征著學校與人的深層關聯。
我突然感受到了顧城那句“生命”的含義。這里掛著畢加索和安迪·沃霍爾的真跡,也展示師生員工們的藝術創意;這里有小泉八云和魯迅的傳說,人們吟誦著從司各特到比爾·布萊森等西方名作家贊美杜倫的詩文,也傳閱不時出現的學生詩集。
在現實中流動的詩意與聯結,構成了這座小鎮和大學的生命,讓她成為一首永遠也寫不完的長詩。

東方博物館的埃及人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