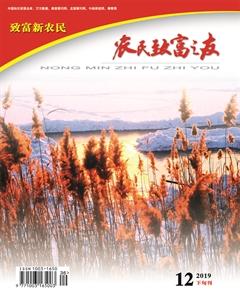北方常用造林樹種的選擇
董鑫
樹種選擇是造林成功的關(guān)鍵因素之一,本設(shè)計(jì)能達(dá)到長春四季綠化、三季開花、樹木茂盛的效果,并能持續(xù)多年,讓環(huán)境不受到污染、生態(tài)效益也日益上增。總體來說就是使樹木適應(yīng)當(dāng)?shù)氐臍夂蚝屯寥罈l件。
一、樹種的選擇
樹種以鄉(xiāng)土樹種為第一,邊緣樹種為輔。禁止因地制宜地種植變化較大的樹木。用材樹種挑選:用材樹種要求主要體現(xiàn)在“速生、高產(chǎn)、質(zhì)量高”的目標(biāo)上。并且,要選擇抗風(fēng)性強(qiáng)、不折斷、不枯枝的樹種,以適應(yīng)北方環(huán)境。
二、樹木的選用及常見的植被
1、喬木
這是一種木本植物,樹干直立,有5米或以上之高。與矮灌木相互對(duì)應(yīng),一般見到很高很大的樹大部分都是喬木,像松樹、樺樹等等。喬是根據(jù)在旱季落葉又或是冬季落葉,可分為落葉和常綠。
2、灌木
主莖不明顯,基部多分枝的木本植物叫灌木,像玫瑰、映山紅等。
3、亞灌木
矮生,生長多年,莖上部有草,開花后凋謝,莖木質(zhì)的基部,就像長春花等。
4、草本植物
草本植物的莖含有少量木質(zhì)細(xì)胞,整株或地上些許易枯萎或死亡,如菊花等,分為不同年生的草本植物。
5、藤本植物
一種有長莖的植物,不能直立并被其他東西攀爬的植物。根據(jù)莖的性質(zhì),可分為木質(zhì)和草質(zhì),一般都能見的紫藤是一種木質(zhì)藤蔓植物,在中國,鄉(xiāng)土壤快速生長的樹種較多,如落葉松、楊樹等,很有前發(fā)展的速生樹種。可以成為山地造林的主要樹種,木材產(chǎn)量高的有楊樹等等。
三、起保護(hù)作用的林樹種
北方常見樹種有:雀舌黃楊、直柳樹、銀杏、櫻花等等,都是可以起到保護(hù)作用的樹種選擇。
1、農(nóng)田保護(hù)林樹種
農(nóng)田防護(hù)林樹種要選擇抗風(fēng)性強(qiáng),枯枝不易被風(fēng)折斷和風(fēng)干。樹木長得快而茂盛。使用壽命長,穩(wěn)定增長,任何時(shí)候都有保護(hù)作用,并且樹木有很好的木材創(chuàng)造能力。
2、水土維持林的樹種
水土保持林的目的是控制水土流失,能夠減少、吸收和阻擋地表徑流,覆蓋土壤,防止水土流失,提供木材。以下條件可以讓水土保持林樹種:長得很快,樹枝很繁密,落葉多;根系發(fā)達(dá),土壤耐酸性很好。
3、薪炭林樹種
薪材林是以創(chuàng)造燃料和薪材為主的,薪炭林樹種具有生長迅速、高產(chǎn)量、很強(qiáng)的適應(yīng)力、易繁殖等條件。而且發(fā)育強(qiáng),可反復(fù)再生;并且能作為柴火使用,燃燒力很大。一般來說,育苗方法不會(huì)被樹種和土壤條件限制,適用于大多數(shù)樹種和各種土壤條件。所有綠化苗木根系較完整,地上部分發(fā)育良好。在干旱、水土流失嚴(yán)重、植被茂盛、動(dòng)物危害嚴(yán)重的地區(qū),該方法的成活率高于造林。苗木從苗圃條件優(yōu)越的移栽到造林地,往往要經(jīng)歷一個(gè)適應(yīng)期,從慢苗期到慢苗期,苗期是不同的。造林初期,幼林生長快于播種方式,造林種苗量少,造林種苗多,造林面積大。但育苗過程復(fù)雜,人工多,成本還大。播種深度,考慮到種植后土壤會(huì)下沉,一般要求苗木根頸的種植深度比原土封高2cm-5cm。苗木由于種植淺,根系外露或表層土干燥,容易受旱,不利于根系呼吸,影響地面部分枝葉的生長。
四、怎么才能適地適樹的挑選
樹種適應(yīng)土地和樹木的基本途徑有三:第一選擇,換句話說,它包括選擇正確的樹和地方。第二,改變土地以讓樹木適合生長,第三,改變樹木以適應(yīng)土地,可以通過訓(xùn)練、精選和育種來改變樹種的某些特征。不同樹種造林密度不同,高密度經(jīng)濟(jì)林通常需要獲得不同類型的產(chǎn)品。一般來說,需要足夠的光照條件,另外,經(jīng)濟(jì)比較密集,種植過程不需要間伐,所以密度小。不同樹種的生物學(xué)特性不同,造林密度也不同。喜歡陽光的樹種和速生樹種,造林密度不宜過高。適應(yīng)性強(qiáng)的樹種,可以少種,適應(yīng)性差的樹種,造林密度可以多一點(diǎn)。同一樹種在不相同立地要求下造林密度不一樣,場地條件好的地方,樹木長得快,密度小。在立地條件差、幼苗很難存活、樹木長得慢、密度適當(dāng)增大的地方。為了判斷土地和樹木是否適合種植,應(yīng)重新檢查和調(diào)查以下幾點(diǎn)。一是活下來的,也就是說,在造林樹種該有的要求下,如果造林技術(shù)很好,苗木可以存活,不發(fā)生凍害或溫度損傷,或者在幼年發(fā)生一些損傷,隨著樹齡的增加,苗木能夠更好地生長;二是能夠正常生長,在一定年齡,種植者可以達(dá)到一定的樹高和胸徑水平,而不縮短快速生長期。四是不早凋零,是指樹木正常生長發(fā)育的提前終止,如枝條的生長、枝條的減少、死梢等。事實(shí)上,上述原則是對(duì)各種自然和經(jīng)濟(jì)條件下造林密度的限制,根據(jù)這些原則一般可以基本確定造林密度,但在山區(qū),造林地的立地條件很差,可以盡快封山育林,達(dá)到封山育林的目的。然后,在適當(dāng)?shù)臅r(shí)間通過砍伐樹木來獲得樹的最佳生長密度,以獲得柔性或小直徑木材。
綜上所述,樹種選擇是否合理是衡量造林成敗的主要因素,可以根據(jù)當(dāng)?shù)氐臍夂蚝屯寥罈l件,一般原則是使樹木適合場地,在樹種選擇上,以鄉(xiāng)土樹種為主,邊緣樹種為輔,嚴(yán)禁因地制宜。
(作者單位:154822黑龍江省依蘭縣松花江農(nóng)場林業(yè)科)
- 農(nóng)民致富之友的其它文章
- 健全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管理機(jī)制提升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
- 新時(shí)期加強(qiáng)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管理工作的策略及建議
- 農(nóng)村勞動(dòng)力流失對(duì)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影響及對(duì)策
- 產(chǎn)業(yè)振興是實(shí)現(xiàn)鄉(xiāng)村振興的必由之路
- 關(guān)于農(nóng)業(yè)轉(zhuǎn)型期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管理學(xué)科發(fā)展的思考
- 基于新農(nóng)村建設(shè)背景下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管理創(chuàng)新策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