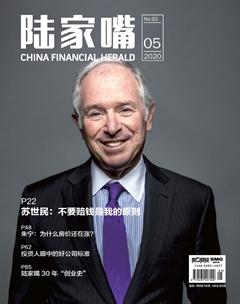復旦教授孔愛國:應對疫情需要企業家精神
在這個時代,政府應該做的是刺激企業的成長,讓企業家去填補技術,填補未來的市場空白。
我將立足于企業的視角,分析疫情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在影響,并從歷次危機的經驗教訓中,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議。
疫情對經濟影響的特殊之處
新冠疫情與2003年的非典都是突發性事件,但是這一次為什么不同?一是截至目前科學家沒有查到病毒的來源;二是新冠病毒的潛伏期較長,有一部分無癥狀感染者,交通的便利使得病毒在全球范圍內迅速傳播。
從經濟發展階段來看,2003年非典與2008年金融危機都發生在中國經濟增長的上行期,而新冠疫情暴發在中國經濟增長的下行階段,有點像雪上加霜,無論對中國人民,還是全世界人民,都非常痛苦。
疫情剛開始的時候,大部分經濟學家預測疫情會影響GDP增速0.5%~2%,從最近兩個月的情況來看,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有兩個數據已經出來,投資和消費的數據都是高臺跳水,消費下降了20%以上,投資下降了20%左右。
從目前看來,第一季度的經濟數據肯定是負的,第二季度也不容樂觀,因為外貿受到非常大的沖擊,需要一個緩慢的恢復過程。如果今年的GDP能保持去年的水平,那已經是相當了不起了。
不管哪個國家,啟動經濟的時候要注意兩點,一是解決短期的民生問題,用短期的修補連接當下與未來之間的坎,跨過這道坎很重要;二是不能忽視長期的目標,如果短期刺激太大,就會對長期產生一定的副作用。
長期目標追求什么?就是中國經濟在全球的競爭力,競爭力不僅僅表現在外貿出口的規模,這是短期的目標,更主要表現在外國對中國的依賴性,外國找不到替代品,就說明我們有競爭力。
中國在逐步邁向市場經濟后,經歷過幾次大的沖擊,前面幾次沖擊,特別是2003年“非典”與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在短缺時代,而最近這次危機發生在過剩的時代。
區別在哪里?在短缺時代,尋找政策工具相對來說比較容易,九十年代我們缺家電,2000年之后我們缺房子、缺車子,而現在這些東西我們都有了,你現在也沒法說你缺什么,可能你只能回答缺錢。
所以過去政府會推出強有力的經濟政策,因為在短缺時代,誰都知道應該發展什么,不應該發展什么。但在當下,如果再爆發危機,我們很難找到一個比較好的經濟政策,或者比較好的工具來刺激經濟成長。
在過剩時代,經濟政策的著力點不應該是具體的產業,因為預測未來的發展很難,而是應該刺激企業的成長,讓企業家去填補未來的市場空白。這個時候,我們不能夠完全由政府來投資,必須發揮企業家的作用。
貨幣擴張的正反兩面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政府推動了一系列固定資產投資,包括四萬億刺激政策、十大產業振興規劃,短期非常有效,但是后遺癥也非常明顯。
刺激的背后往往是貨幣超發。貨幣擴張到底好還是不好,首先我們要了解中國的貨幣擴張帶有一種體制性的因素,只要國有銀行敢把錢貸給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就不要擔心了,不愁以后銀行不貸,一定用新貸款去覆蓋老貸款。國有銀行一旦被綁架,最后會去找央行解決問題,讓央行松綁。
所以央行承受了很大的體制性壓力,每次關鍵時候央行都要出手相救,救到最后,使得貨幣供應量剎不住腳,貨幣供應量如果剎不住腳的話,經濟的負面性效應就會潛移默化形成。在社會上,說得不好聽,貨幣擴張后,很多得到貨幣的人都變得浮躁了。
以四萬億為例,政府拿四萬億投資,相當于四萬億資金流向國有企業,但絕不僅僅是4萬億,這4萬億起到引導性的作用,直接導致銀行資金也向國企業集中。可能政策初衷不是這樣,但事實上造成了全社會的資源最后向國有企業集中,最終導致民營企業失血。
民營企業沒有辦法獲得正常的資金,就尋找非法的地下錢莊的支持,借來的高利貸一年以后基本崩盤,資金鏈斷裂,然后民營企業家就開始跑路。
隨后這些年GDP增速的期望值不斷往下降,也就是說我們找不到投資方向,凡是政府能夠找到的投資方向,事實上都已經過剩,而且老百姓也不寬裕,因為房地產價格太高,很多人一輩子賺到的錢都在房地產里面,老百姓的資金流動性遇到了很大的問題。
當下比任何時候都需要企業家精神
如果經濟增速往下掉,或者說經濟不增長的話,就會產生另外新的問題——中等收入陷阱。過去經濟發展的方式走到了極限,國外的市場空間越來越小,國內的市場空間也受到束縛,在人均GDP一萬美元的時候,如果經濟增長找不到出路,很有可能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從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數據可以看出,2010年到2014年,消費與投資已不分上下,但是2015年以后,消費的馬車已經明顯超過投資的馬車,告訴我們一定要去研究消費、需求,而投資找不到太多增長點。
如果消費主導一個經濟體的話,就帶來了一個新的挑戰,就是當下比過去更需要真正的企業家。過去三十五年,政府決定投資就可以,雖然效率低一點,但是總的問題不大。
但是現在政府已經沒辦法做這個決定,因為消費主導經濟的話,消費的需求不統一了,我們十四億人不可能同時決定今天吃面包,也不可能同時決定今天開新能源車,消費需求的特點是分散、靈活、多樣的,就是不統一。
真正的企業家怎么做?就是看準人們明天喜歡什么,而不是看準現在需要什么,一個好的企業家最大的特征是不停地升級自己的產品、服務。為什么現在MBA、EMBA這么火爆,因為市場需求太大,未來的市場需要真正的企業家。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如何發力?
除了產業政策,貨幣政策的工具也非常多,當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時,一定要有配套的手段將貨幣引入到實體經濟中來,否則投機性的事件就會上升。
這一點應該向美聯儲學習,美聯儲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實施了三次量化寬松,最后一次是通過央行每個月花400億美元無限期地購買次級債,這個政策效果很好,托住次級債市場,公司就可以進一步發債,就相當于把貨幣資金引入實體經濟。
貨幣擴張要體現公平性原則,目前我們的貨幣傳導機制缺乏效率,因此總量的擴張效果會差,就涉及到中國銀行信貸體系的進一步市場化完善,我們就不在這里展開。
財政政策主要是政府支出增加來刺激經濟增長,但是大家有沒有想到,為什么不通過減稅的方法去刺激經濟?經濟學上有個概念叫做擠出效應,在貨幣供應量不變的時候,財政支出增加會導致貨幣需求的上升,導致利率上升,而企業投資相應下降。過去我們財政支出所產生的擠出效應應該是很大的。
再比如,政府可以通過增加稅收或者通過發債來完成政府融資,大家可以想象,過去是稅收為主,現在全國人民都趴下來,下一輪一定是發債的高峰,我覺得發債比收稅強很多,要跟富人借錢,給窮人補貼,跨過目前的這道坎。
從短期看,要達到修補經濟的目的,建議如下:
1. 政府發行債券,直接補貼救助受到傷害的民眾與企業,不能將員工失業的痛轉嫁到企業頭上。
2. 發放消費券,解決貧困的問題。
3. 大幅度降低個人所得稅與企業負稅。
4. 下調貸款利率,下降準備金,量化寬松。
從長期看,建議如下:
1. 完善個人所得稅的征收方法,按家庭征收,而且要考慮地方性差異的因素,大幅度降低居民負稅。
2. 大幅度降低科技型企業的各種稅收,建議按照研發投入比例來制定征稅方案,促進全社會的企業轉型升級。
3. 大幅度調整公用事業收費,特別是油價絕對價格接軌而不是相對價格,大幅度降低高速公路收費標準,目的在于真正建立全國性的大市場。
4. 增加對醫療、教育的投入 。
政策展望的背后,希望的是政府改革,縮小規模,降低政府非生產性的支出費用。
最近出現頻率很高的新基建,我們肯定需要,但是新基建怎么建?一定要發揮政策杠桿的引導作用,要發揮資本市場的選擇功能,慢慢選、慢慢建,這樣才會有好的經濟效益。
最近有個報道,上海市政府圍繞新基建做了很多重大項目的投資,我覺得這很重要,但只是第一步,我希望上海給將來使用新基建的公司“松綁”。
目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還不夠多,新基建也沒地方用,要先鼓勵現存的企業進行數字化改造,政府一定要支持,比如數字化轉型的企業稅收統統減半,我們新基建價值就非常大。
今天的經濟是一個全球經濟,不僅僅是一個國別經濟,新基建的建設,如果沒有很多的企業去應用,可能給發達國家數字轉型的企業提供了更優越的環境,從這一點上來講,我希望政府要兩手抓,一手做新基建,一手刺激微觀企業轉型。
我擔心什么?我擔心的是大家都去做新基建,像過去老基建一樣產能過剩,現在很多小城市的碼頭沒人用,很多落后地區的高速公路沒人用,所以我勸那些想投資新基建的人,跟風要跟得謹慎一點。
當然,最為重要的一點,我們希望政府的刺激政策,既要注重短期的民生,也要追求長期的目標,刺激經濟的長期意義之下,必須注重企業家精神的維護,必須注重市場環境的改善,不要隨便把他們擠出去。
未來需要更大的開放
等疫情過去,為什么需要更大的開放?貿易增長是一個方面,另外一個主要方面,是學習如何產業升級,如果產業不升級,我們未來的路會越來越窄。
如果產業不升級的話,用上面經濟學的術語,就是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進一步開放了,我們要去學什么?
1. 為什么高科技都產生在那幾個發達國家?表面上看,中國的科研能力很強,但是一些技術為什么不發達?
2. 科技如何才能真正落地應用,改變人們的生活?如果科技的應用沒有市場化,科技的發明與發現就會停止。
3. 美國經濟每一次衰退是怎樣復蘇的?其經濟增長當中的核心力量是什么?
發達國家有很多方面是我們學習的目標,暫時還不構成競爭的目標,因為我們對它們的高科技有相當的依賴性。
Q&A
Q:歐美紛紛開啟無限量QE的背景下,未來是否會發生滯脹?
A:以美國、英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治理宏觀經濟的歷史應該追溯到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在增加貨幣供應量的時候,由于過去沒有經驗,導致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滯脹。
但是從九十年代以后,美國幾乎不產生滯脹,物價非常低,因為他們一手在增加貨幣供應量,另一手會引導貨幣走向創新階段。
他們在實施政策時說,貨幣增加無限量,但是只要經濟好轉,他們馬上會剎車,他們治理經濟的經驗、能力,時機把握等考慮問題的深度跟廣度不一樣,值得我們學習,不用擔心他們。
Q:如何看待美國經濟未來的趨勢?
A:美國經濟當中的制度,已經把企業家解放了,我們需要的是什么?本質上要解放我們的企業家,維護我們的企業家精神,把企業家的問題都解決了我們就不怕了。
美國未來經濟的趨勢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因為美國的技術進步,新的技術代替了舊的技術,讓美國的產業在更高的層次上往前成長,這是重要的。回頭100多年的歷史可能發現,每一次經濟增長都與新的技術革命有關。
Q:疫情之后,有些國家實施了逆全球化的舉措,長遠來看對中國制造會帶來什么負面影響?
A:到現在為止,中國的產業對國外高科技的依賴性仍然很大,事實上疫情一旦過去了,它們供應鏈就會產生相應的變化,未來的世界不會封閉,一定是開放。
疫情造成的不是逆全球化,而是讓全球化趴下來,等疫情過去,我們所有人就會站起來,一定是開放的世界,為什么?因為科技文明跟工業文明都需要互相共享。
英美這些國家的產業不是上下游的關系,但貿易總量還那么大,因為它們仍然實現了市場的互補,雖然產業鏈可能在未來發生一些變化,但是隨著人們需求的變化,貿易還會繼續增長,競爭還會促進科技的進步。
(2020年4月2日,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孔愛國教授在“瞰見云課堂”系列課程中,以“疫情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在影響”為題進行授課。《陸家嘴》作為合作方,經主辦方和講者審閱授權發布課程內容。文章整理俞趙杰,篇幅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