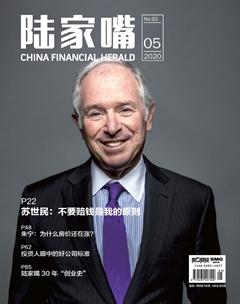“反情懷”的內容創業方可持續
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發給許多行業籠罩上了陰影,影視產業可以算是受影響最大的產業之一。不僅2020年的賀歲檔全部擱淺,至今影院仍未開門迎客,影視劇、電影、綜藝的拍攝也暫停了許久。疫情導致了影視行業的低迷,不過這并不能代表整個文化產業的現狀。
文化產業的宏觀機會
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是第42年,其間經濟飛速發展,如今我國一、二、三線城市人民的物質生活基本是飽和的,除了每過幾年想換一輛車,再過十年要換一套房子之外,日常生活中的物質需求是比較飽和的。那么,我國的消費升級就主要產生在精神消費領域。十年前,人們一年會看幾場電影?雖然現在疫情期間電影行業非常慘痛,但是疫情完全緩和之后,人們都會涌向電影院,電影行業還是會存在的。
現在大家宅在家里也會更多地刷互聯網上的嗶哩嗶哩、愛奇藝、騰訊視頻和抖音等,這些都是精神消費。未來消耗大家錢包和時間的,越來越多會是在精神消費的場景。精神消費不僅僅是看電影、看話劇、看音樂會,還有很多場景:我們去一家小資情調的餐廳吃飯,并不是真的為了去填飽肚子,而是為了打發時光、為了某種小資情調。這些都是精神消費。
如今,中國的人均GDP超過了1萬美元,我們對精神消費的需求是非常強烈的,精神消費在未來將占據我們的大部分時間和錢包。可見,內容創業的“風口”、宏觀機遇是存在的。
文化產業的定義是什么?我認為,所有滿足人們精神生活消費品的生產、流通,以及促進這些精神產品生產、流通的技術,都可以定義為廣義的文化產業。
傳統意義上的文化產業、新聞出版、影視演藝等是狹義的精神消費產業,或狹義的文化產業。
狹義的文化產業有一定風險,特別在市場環境變化的情況下,經營風險比較大,在某些時刻有立即歸零的可能性,所以狹義的文化產業并非最好的創業機會。在小圈子之外的廣義的精神消費產業,則有更廣闊的機會。包括體育、旅游、素質教育、時尚以及為了這些精神產品的生產流通做技術支持的全息技術、VR技術等,都是為了人們的身心愉悅服務的消費,相對傳統文化產業更加市場化,風險也較小。所以廣義的文化產業更加適合創業,創業風險相對較小。
泛文化產業即廣義的精神消費產業也有五個細分賽道:
文娛、文體、文旅、文教和文創。
前四個很好理解,應該怎樣理解文創?比如說一件衣服上面貼了一個Hello Kitty,我們并不是只把它當成一件衣服來穿,而是要展示自己的某種喜好和心情,所以時尚產業也是對原有第二產業的改造和升華。女性購買故宮的口紅也不僅僅是沖著口紅去的,更多的是購買IP的精神含量和文化價值。
另外,影視產業里面還有很多科技含量、科技支撐,賣水的、賣工具的、賣場子的,那么這些東西我覺得一定要全面地、辯證地、清晰地給它分清楚。內容創業也是屬于文化產業的創業。核心是什么呢?我這里舉了一個比喻,房地產開發的核心、地段,你在差的地段,請建筑大師去設計房子,它可能也賣不掉。在好的地段設計稍微差那么一點點,裝修不要那么好,可能賣得也不錯,它的核心價格是由它地段所構成的。
首先,文化產業不等于影視產業。在整個內容創作領域,IP是核心。打個比方,房地產商開發一個樓盤,如果地段非常差,設計再好也很難賣,如果地段很好,設計裝修差一點也不愁賣,房子的核心價格就是由地段構成的。那么內容創業的核心就是IP,如何認識IP?IP不僅僅是一個小說、一個段子或者一個故事,而應該具備三個核心元素:情感喚醒或夢想孕育、易于傳播和推廣、可迭代。
我們可以從好萊塢的經典IP去理解“情感喚醒或夢想孕育”:變形金剛系列非常熱血,迪士尼系列豐富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好的IP不能只有你自己懂,而應該能夠被一眾人所了解和喜愛,才能成為產業,所以必須易于傳播和推廣;“可迭代”,比如007推出了一部接一部的電影,迪士尼的人物形象已經從鉛筆畫、鋼筆畫一步步成為了現在的3D形象。
用商業和金融語言解讀優質IP
好IP是市場檢驗的產物,而非某個大佬或藝術家自娛自樂、自說自話的產物,而且還要經過市場和時間的檢驗。
內容創業者一定要尊重市場,站在用戶的角度思考產品,而不是“我想做什么”。如果做出的作品觀眾看不懂或票房不好、商業變現不成功,作者反而怪觀眾和用戶沒有素質,實際上是陷入了自戀的誤區。所以好的內容創業有必要建立企業內部的產品經理,站在用戶立場思考內容。
作為投資人來看內容創業,有一個大坑,就是情懷。
羅永浩開始在抖音直播,因為他創業失敗導致負債累累。他創業失敗的原因就是講情懷。羅永浩曾經在路演的時候說,“我不是為了輸贏,我就是認真。”認真是創業的必要條件之一,但絕對不是充分條件。商業化創業就是為了要贏,要賺錢。亞馬遜雖然17年都沒有賺錢,一直在用VC的錢,但是它最終還是為了賺錢,因為它解決了社會的痛點。
還有幾個例子:
曾經新三板有一個表現非常好的掛牌公司——云南文化。這家公司擁有楊麗萍這個大IP而獲得了很多投資者的信任,但是投資人卻沒有看到其商業模式的本質,陷入了“明星藝術家的幻覺”。楊麗萍老師是優秀的藝術家,卻不是一個好的商人,云南文化難以盈利,市值已經砍到了腳踝。
小馬奔騰這家公司做了很多知名電影、電視劇,在大氣候極度適宜之時開放股權,備受追捧,超過40家PE機構參與搶籌,融后估值達30億元。但是2014年初董事長李明去世,其遺孀金燕接任董事長職務,公司就陷入姑嫂之爭,幾乎破產。當時陷入了“知名電影電視幻覺”的投資人血本無歸。
在體育行業也有很多幻覺,最典型的就是“奧運體育幻覺”。今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東京奧運會要推遲一年,造成了很大的經濟損失。1988年,韓國漢城奧運會塑造了韓國的民族品牌——三星,所以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上,很多人希望復制三星的崛起之路,把國產品牌推向世界,但是北京奧運會有沒有把聯想這個贊助商打造成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民族品牌?我認為是沒有的,相反后來收購IBM還將聯想拖入了一個困局。2008年華為并不是奧運會的贊助商,卻發展成了現在中國在世界上最有競爭力的消費品品牌。類似的,2008年奧運會開幕式上非常令人驚艷的清明上河圖卷軸,是由一家叫水晶石的公司制作的,后來水晶石獲得了很多國內地方政府的訂單,也負責了2012年倫敦奧運會官方數字圖像服務,但是后來并未能成功地開拓歐洲市場,因此水晶石在倫敦奧運會砸進去幾千萬的贊助費后并沒有獲得收益。再加上后來“國八條”的限制,國內的訂單也大幅萎縮。它的投資人以為蹭上了好流量,但是能不能變成真金白銀還是未知數。
可見,內容創業千萬不要講情懷,講情懷的是文化事業,有很大概率不可持續。不管是創業者還是投資人都要防止陷入這些幻覺中。從投資人的角度出發,我認為要冷靜、理智地看商業模式,去看報表、看管理團隊,非常冷冰冰,但是這就是商業。在我眼里有兩類內容創業者:文化人和文化商人。文化人常常以自我為中心,當商業變現出現問題的時候這類人可能會認為觀眾不行;而文化商人會以用戶為中心,積極吸納用戶的反饋,生產出來的是持續迭代的產品,而不是吃老本。有兩個案例:
第一個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開心麻花。2003年開心麻花創業,做喜劇話劇,經過12年的積累,在2015年從話劇跨界電影,拍的第一部電影《夏洛特煩惱》一炮而紅,票房14.4億。在電影之前,《夏洛特煩惱》已經在劇院里演了三四百場,不斷接受觀眾的反饋,經歷了很多次迭代,到了最后的電影,很多段子都來自于人民群眾的智慧,而不是最初編劇寫出來的版本。開心麻花的文化就是要謙虛地接受消費者的反饋,最后利用電影把所有迭代積累一次性升華,迅速爆發。后來開心麻花的每一部作品都經過這樣的迭代,而且他們認識到自有IP也會枯竭,大膽運用了國外的IP,結合中國文化,做巧妙地改造,就拍成了《西虹市首富》。開心麻花是一家“俗”文化創業成功的典范。
一個比較嚴肅、“高大上”的案例是財新。我們在2016年投資了財新,當時很多人不看好,認為太“高”了,但我堅信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來越多人需要這種高質量、負責任的內容,我相信一個講真話的媒體一定有商業機會。財新幾乎是國內第一個在公眾號、網站上做內容付費的媒體,這次疫情財新做的內容限時免費,也吸引了更多讀者的訂閱,疫情期間,財新APP的流量獲得了井噴式的增長,也許疫情過去后會有一些流量損失,但也會沉淀下來很多用戶。當然財新也恪守國內的監管底線,同時堅信真實的新聞是稀缺的,雖然熬了若干年,但是等到現在,獲得了應有的價值認同,商業上也獲得了一定的成功。
總結一下,99%的情懷創業是會失敗的,內容創業,讓情懷見鬼去吧!另外,疫情期間我們習慣了線上交流,這是技術的更新對人們精神消費升級的加持,因此,我們要抓住人們精神消費的升級,同時抓住技術的更新和迭代。
(本文系上海榮正投資董事長鄭培敏在陸家嘴創投課上的分享,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