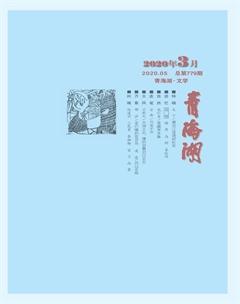轗軻者點燃膏火照亮的博大詩境
馬鈞
一
昌耀先生生前出版過6本詩集,以最后面世的《昌耀詩文總集》收錄的作品最夥、時間跨度最大。因其辭典般的厚度和硪石般的重量感,它只宜于置放在書桌、幾案上翻閱,而不適合隨身帶在背包、捧在手里閱讀。中國古代線裝書的妙用與體貼,在于它的湊手和輕便,可以攤平來讀,也可以在庭除行吟而讀,指甲蓋大的武英殿仿宋字體和文津閣手抄本書體,更是予人雅飭、親切、不傷眼神的好感和爽適。如今,世人一面蜘蛛似的盤絲于網絡世界,一面又熱衷于戶外活動和離家遠游。精明殷勤的出版社,早已為讀者量身推送著一冊冊精美輕便的書籍。我記起上世紀50年代末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過一套巴掌大的“文學小叢書”(靈感或許源自1935年英國出版商創意的“企鵝叢書”),所選的古今中外佳作,字數不多,篇幅不大,隨身可帶,隨時可讀。眼下,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這本昌耀詩歌選,選編者謹守昌耀生前審定的作品篇目,留下體量龐大的詩作錨泊于原先的港灣,而解纜輕快的“舟楫”在新的水域犁出雪白浪花。
詩集在視覺美感上,素來美在苗條和素雅,弄到極致,宛如美的一粒緩釋膠囊。帶著這么一冊薄書上飛機、坐火車、乘輪渡,想想,就有一種松泛感先行襲來。
此前,除昌耀選編的版本,由他人選編的首個選本,當屬2002年由山東美術出版社出版的《乃正書昌耀詩》。朱乃正先生以199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昌耀的詩》為藍本,選錄34首作品。其友鐘涵先生在序言里說:“選錄在這里的只是昌耀詩中很少的一部分,由于書法的限制,又以短章為主。但是書家與詩人之間在精神與文化上的相互了解默契,使選詩不但沒有遺落詩人主要的光彩,而且用視覺語言之妙造傳譯而把它更發揮出來了。”心同此理,在昌耀先生逝世20周年之際,編輯家從《總集》里選錄一些短制來滿足讀者新的閱讀需要,實在是順時、體貼之舉。況且,出版社不想僅是“熱熱剩飯”,而是煞費苦心、鄭重其事地搜羅到有關昌耀先生的照片、手跡、信札、名片、工作證、獲獎證書,甚至昌耀給家中孩子的畫兒上落下的題記等文獻資料。它們陡然間提升了這個新選本的附加值和含金量。這些資料因為罕見或者首次披露而愈發顯出珍貴。作為讀者,盡管我們在對一些作家創作精品佳作時的“本事”毫不知情的情況下,仍然能夠有所知會和賞析(如同不懂典故也能讀懂原詩,但你讀不出煙涵在典故里的秘義),如果我們合法地掌握有作家的某些鮮為人知的往來書信、創作背景,一些珍貴的留影、手跡(尤其是那些被作者涂來改去的草稿,比之謄抄一新的稿本更能透露作者的心跡和文思),那么我們就會有一些新的感覺新的發現。比如新年伊始,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公開了著名詩人T·S·艾略特與其知己艾米莉·黑爾之間的千余封信件。研究者們陡然間有一種變身為文學領域的福爾摩斯的職業興奮,他們不僅探知到艾略特一些杰出詩句的靈感來源就源自黑爾,還進一步清晰化著《荒原》中“風信子女孩”黑爾的形象。再比如蘇珊·桑塔格評論本雅明的名篇《在土星的標志下》,開筆就是從本雅明的四張肖像照開始她的精彩論述。這是我們的傳統文論里罕見的一種思考路徑。這類超越單純的語言文本的闡釋路徑,其生氣和生機就在于把任何一個文本視作開放的文本,把任何一冊文字的結集視作意識的依舊潺湲流動、依舊接納網狀支流補給的河流,而不是圈成一湖連清風都吹不起半點漪淪的死水。以往人們看到的書籍,要么是滿紙密植文字,要么配上一些考究的木刻版畫,傳統圖書帶給人們的享受也就到此讓人嘆為觀止。而這本文圖渾成的書,不論站在什么角度,絕對是一本能讓讀者的閱讀感覺“弧面轉接”的圖書。它的圖片來自現代世界的攝影術——一種能夠通過光影蟬蛻出事物原真樣貌的復制技術。它比文字和畫像更能恒定、準確地記錄下已逝事物瞬間凝固的諸多原真信息。昌耀生前僅在兩本詩集的扉頁留下肖像照。現在,這本書里收錄的昌耀先生的這些留影、手跡,不單可資讀者睹物思人重拾昔日時光,其間彌散隱動的氳氛,還可視作一種富含啟示和潛對話張力的潛文本,成為開放式循環闡釋的酵母,成為閱讀前后助益理解的一種心理暗示。我將此視為本書的第一個創意,這也是編輯發出的邀請,邀請有心的讀者,捫摸、會意詩人心跡,誘導讀者尋索相片、手跡與詩人詩作之間隱然映發的蛛絲馬跡。本書的第二個創意,則是網絡時代賦予圖書的一項嶄新功能:借助微信掃碼,將二維碼中存儲的聲音文本,憑借配樂朗誦藝術對昌耀詩歌的聲音塑造,傳輸給讀者的聆聽。如此,語言、視覺、聲音三種介質相互編織相互映射,渾化為秉具多維度感覺的柔性織體,一個超級文本。此種境況乃是現代人所心儀的多重閱讀體驗,更是昌耀詩學極度崇尚的審美狀態。
如此,這本被標識為“昌耀詩歌圖典”的選本,得以重回“圖書”老樹萌發新枝的語境。移用錢鐘書《談藝錄》引言里的一句舊話:“僧肇《物不遷論》記梵志白首歸鄉,語其鄰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茲則猶昔書、非昔書也,倘復非昔書、猶昔書乎!”值此機緣,這本書原有的書香不能不飄進新的馨香,其效用如同萬花筒——圓筒里的那些花玻璃碎片還是已有的那些花玻璃碎片,可是隨著轉動,經由三棱鏡反射出來的圖案卻是隨轉隨變,花樣不斷翻新。
二
忽然之間,我會意到“轗軻”二字之于詩人昌耀命運的玄秘聯系。
這兩個帶著車字旁的漢字,比之于人們習見慣用的“坎坷”一詞,它更與昌耀如影隨形,甚且與詩人一生的遭際焊在一起,有如隱入皮肉而終生不得挑出的銳刺,時時傳感牽連全身的疼感信息。昌耀21歲時曾因寫下《林中試笛》而罹禍,其中一首詩題便是《車輪》。從此草蛇灰線似的埋下其一生遭際蹇頓顛簸、艱辛危苦的轍跡。眼下這本詩歌選集又以《高車》命名,又在冥冥之中發酵著玄妙。熟悉昌耀詩歌的讀者只要稍加留心,就會發現昌耀不同時期的詩作里,頻繁地出現跟“車輪”相關的詩句和意象。我這里只捎帶提及兩處重要的關聯。《車輪》里寫道:“在林中沼澤里有一只殘缺的車輪/暖洋洋地映著半圈渾濁的陰影……”(“殘缺的車輪”可不正是“轗軻”一詞富于包孕的意象呈示!)昌耀晚年,在我命名的屬于“遲暮風格”(替換薩義德的批評術語“晚期風格”,使之榫卯于中國文評的話語框架)的一系列作品里,有一篇1996年寫下的《時間客店》如此寫道:“剛坐定,一位婦女徑直向我走過來,環顧一下四周,俯身輕輕問道:‘時間開始了嗎?與我對視的兩眼賊亮。我好像本能地理解了她的身份及這種問話的詩意。我說:待我看看。于是檢視已被我攤放在膝頭的‘時間,這才發現,由于一路輾轉顛簸磨損,它已被揉皺且相當凌亂,其中的一處破缺只剩幾股繩頭連屬。”時隔四十年,當年“殘缺的車輪”轉為“破缺”的“時間輪盤”!引語中的黑體字部分,細細玩索,語義里仍舊留有“車輪”“輪轉”的視覺剩余。《大智度論》里,直接就以“車輪”作比,兼及“輪轉”之用:“世界如車輪,時變如輪轉,人亦如車輪,或上而或下。”一忽而是輪轉帶來的加冕,一忽而又是輪轉帶來的脫冕,昌耀的命運之輪與佛學所言若合符節。
寫下《高車》《車輪》四十多年之后,昌耀在《故人冰冰》里,憶及他作為“勞改犯”在西寧南灘監獄“最后一次駕在轅軛與拉作幫套的三四同類拽著沉重的木輪大車跋涉在那片灘洼起伏之途的情景”。“轗軻”之含蘊,之水印般再次顯影的“車輪”,正是如此這般在昌耀身上投下揮之不去的心理陰影,又在他的筆下轉化為“淘的流年”難以磨蝕的審美投射。
在這里,我想簡捷地引入與“車輪”相關的大道別徑。昌耀生前在寫給駱一禾的信中對其在長篇論稿中揭示的有關“太陽”的“一系列光感形象”表現出歆羨式的驚奇。因為車輪上的輻條酷似巖畫或兒童畫上太陽發出的道道光芒,為此車輪在東西方都被作為太陽和宇宙動力的象征。杰克·特里錫德在《象征之旅》里說:“與車輪相關的神靈一般都是太陽神或是其他全知全能之神——古亞述人的主神阿舒爾、巴比倫神話中的太陽神沙瑪什、近東地區的貝爾、希臘神話中的宙斯、阿波羅、狄俄尼索斯以及印度教中的毗瑟拏·舒亞。”添上《楚辭·離騷》中“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的書寫以及注釋家“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的神話意象,人類間基本相近的心理結構皎然可識。而車輪和日輪,就這樣在昌耀詩歌的字里行間淡出淡入。
三
現在看來,昌耀踏上高原,絕對是有備而來。
一個之前對青海毫無感性認知的湖湘之子,在他來到青海的短短幾年里,就好像未飲先醉地美美吸食了幾口青海的精髓,獨自以詩歌的方式破解著一個個青海的密碼。那些不久之后從民族、地域、方言、風情里熟化出來的一行行詩句、一串串響字,即便是高大陸世居者中的俊才,也不得不嘖嘖稱嘆昌耀探囊取物般的文學才情。仿佛他事先踩點,銘刻下有關青海山河人文的重要穴位,只待假以時日,將自己修煉成日后詩歌的“葵花點穴手”。
1959年,才來青海不到3年的昌耀,便寫下了《哈拉庫圖人與鋼鐵》。如此短暫的時光,詩人仿佛幾天前才落下的種子很快就把自己的根須扎入青海大地,突然破土而出,抽枝展葉,迅速生長。每讀一遍“鋼鐵”,恍如置身于哈拉庫圖村人在上世紀大煉鋼鐵的歷史情境。不說那撲面而來的民風、熟諳的鄉間規程、地道的民間敘事,單說這首詩上篇第三節里兩行復沓重疊的民歌式句段——
跳呀,我們跳鍋莊,九里松,1 2 3……
跳呀,我們跳鍋莊,九里松,1 2 3……
詩句里出現的“鍋莊”,是藏族民間一種由眾人手牽手起舞的圓圈舞。詩句里的“九里松”,不是生活在青藏文化圈里的讀者,讀到這里一定會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絕大多數讀者一定會把它望文生義地理解成“九里長的松林”。須知這里的“九里松”不是漢語,而是藏語,是藏族人對數字1 2 3的一個發音,其譯音通常會記作“久”“尼”“松”。昌耀僅有的這個“藏翻漢”,明顯帶有文學化、雅化、漢化的傾向。后來隨著昌耀對青海大地日益深化、廣化的了解,只要在涉及地名、人名或專屬名詞時,他一直恪守“名從主人”的原則。比如“扎麻什克人”“丹噶爾”“土伯特”“老阿婭”“多羅姆女神”“古本尖橋”“卡日曲”“阿力克雪原”“哥塞達日孜”……最為典型的是《瑪哈嘎拉的面具》,詩題里的“瑪哈嘎拉”一詞,昌耀既沒有選擇使用漢譯里通行的“大黑天”,也沒有選擇生僻的藏語譯音“貢保”,而是選用了古奧的梵語譯音——一個更為久遠的源語(翻譯理論里叫作“出發語”)——瑪哈嘎拉。在詩中擅長使用人名地名,是昌耀詩學給中國詩壇的一項重要饋贈。錢鐘書在《談藝錄》里專門討論過這一中外詩歌創作中的神秘經驗。其在修辭學層面上的審美功能,如同西方文評家李特之言:“此數語無深意而有妙趣,以其善用前代人名、外國地名,使讀者悠然生懷古之幽情、思遠之逸致也。”如同中國古典詩論里妙契于心的體悟:“詩句連地理者,氣象多高壯”;如同史蒂芬生在《游美雜記》里論美國地名時的感慨:“凡不知人名地名聲音諧美者,不足以言文。”昌耀作為詩藝的全方位勘探者,把這一神秘經驗無師自通地化作了自己的詩歌地標。1961-1962年,來到青海只有六七年的年輕的昌耀,在《兇年逸稿》里就借用抒情人物的口吻,篤定而深摯地宣告:“我是這土地的兒子/我懂得每一方言的情感細節。”驗之以昌耀后來眾多的詠青詩作,此言絕非虛言大話,實則是夫子自道。
如果說對地名人名方言的詩學修為只是昌耀在詩歌藝術上的小試身手,那他更超絕的功夫在于,遙承唐代詩人煉字、煉句的傳統,而在煉意、煉境上獨步當代,超絕群倫,運斤如風。下面聊舉三例——
《去格爾木之路》:“沒有遮陰的土地。/是齁咸的察爾汗的土地。”青海由于高寒缺氧和特殊的地質構成,在一些高海拔地區往往寸草不生,在人們目力所及的范圍里往往見不到一棵綠樹和高大喬木投下的陰翳。對于常人所能表達的經驗,昌耀采取了“眾轍同遵者摒落,群心不際者探擬”的寫作策略,戛然獨造,自辟新境。一句“沒有遮陰的土地”,便把當年柴達木盆地沒有喬木生長的環境以宛曲新穎的方式一語道出,使后來的書寫者很難再有附加其上的高質量文學表達。
《山旅》:“高山的雪豹長嚎著/在深谷里出動了。/冷霧中飄忽著它磷質的燈。/那靈巧的身子有如軟緞,/只輕輕一抖,便躍抵河中漂浮的冰排,/而后攀上對岸銅綠斑駁的絕壁。”這可能是新詩里第一次書寫雪豹的形象。昌耀寫雪豹的聲音,寫它棲息之處的幽僻,最妙之處是寫豹子的目光和它動作的輕盈敏捷。冷霧既是氣象的交代,更是幽悄氛圍的營造。“磷質的燈”完全是昌耀自創的新語。從前所謂的燈,是焚燒油膏以取光明,這里拿“磷質”來作為限定詞,一方面是精準地摹寫了豹子的目光如同黑暗中白磷可以自行發亮的物性。另一方面,磷光在暗夜幽暗的光亮,又賦予豹子一層神秘感,強化其目光的幽悄冷逸。這樣的選詞,還透露著昌耀對地質類名物的特殊嗜好,以及沉淀于他經歷里的物事和識見。1961年,昌耀在《荒甸》的結尾就蹦出過這個“磷”字:“而我的詩稿要像一張張光譜掃描出——/這夜夕的色彩,這篝火,這荒甸的/情竇初開的磷光……”聯想到昌耀當年流放于祁連山,他一定在那個富含礦藏的寶山,見識過諸如方解石、螢石、石英、重晶石等磷化物發光的現象。諸如此類的詞語就是這樣被詩人焐熱,帶入他的體溫和汗息。艾略特說:“詩人的心靈事實上是一個捕捉和貯藏無數感受、詞句、意象的容器,這些感受、詞句、意象一直擱在那里,直到所有分子都匯齊,于是結合起來構成一個新的復合體。”昌耀不是在字典里搬運字詞,他是在他的身體里像蚌殼一樣化育珍珠般的詞語。“軟緞”的喻象用得更是精彩至極。作為大型貓科動物的雪豹,其身體本不輕盈,它的輕盈來自它在運動中對自身肉體重力的巧妙控制、轉化與消解(猶如杜甫筆下化重為輕的描寫:“身輕一鳥過”或“微風燕子斜”)。“軟緞”的比喻之后連用的“抖”“躍”“攀”三個動詞,義脈流轉,將運動中的重力和輕盈一氣貫通到恰如其分的地步。
《莽原》:“遠處,蜃氣飄搖的地表,/崛起了渴望嘯吟的筍尖,/——是羚羊沉默的彎角。”超乎常人的精敏細微的觀察,是昌耀作為詩人的又一過人之處。描寫高原生靈的詩作和詩人不在少數,但沒有一人從大氣光學現象的角度,去寫藏羚羊出沒的環境。“蜃氣”,通常發生在海上或沙漠。在青藏高原的戈壁、沙漠地帶,由于晝間地面熱,下層空氣薄于上層空氣,光線經過不同密度的空氣層后發生折射,高出地面的空氣里便會出現透明光波的顫動,這就是“蜃氣”的一種表征。把羚羊的尖角比喻為植物里的“筍尖”已屬出人意表的聯想,詩人還要在此基礎上給喻體配上意態化的音效——“嘯吟”。昌耀在這里使用了一種語義結構波折多轉的曲喻修辭術。冒出土層的竹筍嫩尖與尖狀的羚羊角相似,此外再無所似。可是昌耀用他的奇情幻想引申到人們用竹子可以做成用以吹奏的竹笛,于是筍尖便可“嘯吟”做聲。這一修辭術古已有之,錢鐘書是它的發現者和命名者。《談藝錄》首次披露唐代詩人李賀精于此道。它的修辭原理就是 “以一端相似,推而及之于初不相似之他端”。“如《天上謠》云:‘銀浦流云學水聲。云可比水,皆流動故,此外無似處;而一入長吉筆下,則云如水流,亦如水之流而有聲矣。《秦王飲酒》云:‘羲和敲日玻瓈聲。日比瑠璃,皆光明故;而來長吉筆端,則日似玻瓈光,亦必具玻瓈聲矣。……古人病長吉好奇無理,不可解會,是蓋知有木義而未識有鋸義耳。”即便今人,解悟曲喻的作家學者也不在多數。在《圣詠》里,昌耀再次使用曲喻法締造詩意:“樓頂鄰室的縫紉機頭對準我腦顱重新開始作業,/感覺春日連片的天色隨著鍵盤打印出成排洞孔。”縫紉機可以把成塊成片的布片縫紉起來,連成片狀的天色自然也可以如布料似的縫紉在一起。如此奇異美幻、急轉腦筋的聯想,非昌耀者難以擬想。而且,其意境由居室日常的戶內空間,切換、擴展至戶外廣闊的天空,我們能不嘆服其造境的樸素、遙深與宏廓!
毫無疑問,這類只有具備語言自覺方能獲取的巧思奇想,是昌耀詩學活化潛力永在的重要元素。我在這里順便呈示一些昌耀詩歌里的修辭術。
——分喻:肯定相似的一端,同時否定另一端,最后轉回到比喻的本體。《莽原》:“遠處,蜃氣飄搖的地表,/崛起了渴望嘯吟的筍尖,/——是羚羊沉默的彎角。”這里的分喻隱去了否定的一端——不是筍尖,直接以肯定來隱示那否定的一端,這是邏輯上的一個原理:肯定命題預先假設著否定命題,否定命題又預先假設著肯定命題。《頭像》:“樹干上/一只啄木鳥。——不是鳥。是伐木者隨意剁在樹干的一握Boli斧。”仔細體味,我們能夠直接感受到詩人文思跳轉的過程:“一只啄木鳥”顯然是詩人的第一感覺,后面的表述是對具有迅捷性、直接性、本能意識等特征的第一感覺的修正。“Boli”疑似外文,查閱英語詞典,找不到這個單詞的蹤影,只有與之相近的“Bole”,意思是樹身,樹干。是誤植還是拼音?一時難以解會。我倒樂意將此種情形視作昌耀以文為戲的“戲筆”,正如昌耀在給SY的一封信里落款為“W耶夫”。W是昌耀姓氏的字母代稱,耶夫則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白夜》里的人物名稱。昌耀留給世人的印象偏多于冷峻肅穆,實際上他還有著不被常人察覺的天真、憨氣和被苦澀包裹著的幽默感。多數詩人只具有單向的秉性氣質,而昌耀則兼具復雜綜合的秉性氣質,葉嘉瑩評論杜甫時稱謂這種情形為“健全之才性”。
——拆散法:將詞語或詞組慣常的搭配、習慣的組合拆散,從而產生新的意義,揭示因為詞語或詞組長期的捆綁、因循固化而遮蔽的真相。《一天》:“有人碰杯,痛感導師把資本判歸西方,/唯將‘論的部分留在東土。”“資本論”原先的詞組表示的是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一部經典著作,而拆散后釋放出的嶄新語義,則是對資本只專屬于資本主義制度這一偏狹觀念和死守理論的本本主義者、務虛之流的尖銳諷刺和深刻質疑;《一個中國詩人在俄羅斯》:“看哪,滴著骯臟的血,‘資本重又意識到了作為‘主義的榮幸,而展開傲慢本性。”。
這是對“資本主義”這一形同焊接在一起的詞組進行了斷然的分割。拆散前,“資本主義”是個固定詞組,表示資本主義國家所實行的一種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的制度。拆散后,早已硬化的語義獲得了空前的活力釋放,恢復了生動、感性的社會面孔。“資本”一詞還原為在經濟學意義上所指的用于生產或經營以求牟利的生產資料和貨幣,“主義”的概念一方面表示主導事物的意義,另一方面表示某種觀點、理論和主張。昌耀這一語言修辭的經典性還在于他沒有僅僅停留在拆散上,他還通過擬人化處理,給這個概念注入了活靈活現的意識和情感,使拆散后的“資本”“主義”兩個干巴巴的詞語,彰顯出物質時代把金錢重新供奉為圣主后渾身上下散發出的那種耀武揚威、趾高氣揚的優越感與傲慢;《和鳴之象》:“不賄以供果。/不賂以色相。”拆散“賄賂”一詞,在白話詩中貫穿古漢語句式和聯句,猶如木心所言:“古文今文焊接得好,那焊疤極美。”《眩惑》:“黃土揮霍成金。”拆散成語“揮金如土”,產生新的意義。《燔祭》:“夜已失去幕的含蘊,/創傷在夜色不會再多一分安全感。”拆散“夜幕”一詞,釋放出夜色無從撫慰、掩飾隱秘的嶄新樣態。
——“冤親詞”:也叫悖詞,是一種矛盾修飾法,將兩個不協調或相互矛盾的詞合在一起表達某種意思。《生命的渴意》:“硫磺一樣骯臟的冷焰”;《在雨季:從黃昏到黎明:“誤點的快車失去時間橋梁在路旁期待”;《意義空白》):“……吶喊闃寂無聲空作姿態”;《一天》:“一切的終結都重新成為開頭”;《晚云的血》:“文明的施暴”;《冰湖坼裂·圣山·圣火》:“他感到一種快樂得近于痛楚的聲音/他感到一種痛楚得近于快樂的聲音”;《西鄉》:“再生如同土崩”;《眩惑》:“我們降生注定已是古人。/一輩子僅是一天;”《詩章》:“音的雕砌”;《盤庚》:“焦黑的黎明”;《20世紀行將結束·殘編3》:“死亡的刀尖,自由的大門。”
——倒果為因:昌耀筆下有許多匪夷所思的詩句,這是他有意顛倒了因果關系而使語義陡然化為陌生和新奇,是昌耀式倔聱詩風的一種體現,它一般止步于語句的尖新,而孱弱于哲理性深意的表達。《關于云雀》:“但我確知在寂寞的云間/一直飄有懸垂的金鈴子,/只被三月的曉風/或是夏夜的月光奏鳴。”《春天即興曲》:“天邊/有一人綰發坐在礁石梳理海風。”《幽界》:“星空補丁百衲。/路,因狗吠而呈坑洼。”《冷太陽》:“卵形太陽被黑眼珠焚燒/適從冰河剝離,金斑點點,粘連煙縷。”《燔祭》:“美麗憂思/……/如一架激光豎琴/叩我以手指之修長/射如紅燭。”“燈光釋放黑夜”。
——戲擬:《鶩》:“君子何曾坦蕩蕩。∕小人未許常戚戚。”改寫《論語·述而》里的名句:“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將既成的、傳統的東西打碎加以重新組合,揭示新的內涵,新的人性狀態。
——套喻。昌耀的比喻法里,還有一種極為特殊的、未被人們識別和命名的比喻,即在比喻中套入兩個喻體,以增加語意的密度和精度。因為很像俄羅斯著名的玩具套娃(空心木娃娃一個套一個),我把這種嶄新的比喻法命名為“套喻”。《莽原》:“他們結成箭形的航隊/在勁草之上縱橫奔突。”喻體里分別套接和壓縮進“箭形”和“航隊”兩個意象,使語義陡然轉向繁復。《幽界》:“列車在山腳啟行,龍骨錯節/發出一陣鏈式響尾;”《詩章》:“食人巨蟻烽火臺般聳布的魔宮”;《酒杯》:“……一只拇指般大小、冰甲一般脆薄的玻璃酒杯斟滿礦泉水般明凈的銀液汁”;《生命體驗》:“移情的花廳/歌樓鳳冠的亮片誨淫誨盜呼應山中晚霞的寶石”;《頭戴便帽從城市到城市的造訪》:“A國學者W側轉他那列寧式的椰果似的腦顱”;《圣詠》:“看不到的穹蒼深處有一葉柳眉彎似細月。”這些套喻,事實上是昌耀詩歌凝練化表達在句子層面的一個表征,它還關聯著詩人在篇章層面整體性的詩行壓縮技術。它通過省略、刪除、合并等手段,使詩章由句到篇從意義的流離、繁蕪、瘠薄趨向意義的妥帖、精粹、豐贍。昌耀還在更高層次上,使用當代詩歌里罕見的時空壓縮技術,即他自己發明的“將痛苦的時空壓縮”為“失去厚度的‘薄片”(《我的死亡——〈傷情〉之一》)。
還有一些比喻,昌耀并沒有使用特別的技巧,但他在作比的事物之間,要么是遠距離發生聯系,要么是近距離發生聯系,但在結果上都做到了新奇。《聽候召喚:趕路》里對作為男人第二性征的胡須有過這般的聯想:“你的/在火光洗濯下的胡須多美,如溪流圓石邊緣隨水紋微微擺動的薄薄苔絲綿軟而動情。……你柔柔的胡須可愛如嬰孩耳際柔柔的胎毛。”這兩個比喻,粗看全都來自實際物態的觀察,無非一則來自自然界,一則來自人類的幼年。可要是細辨起來,兩個聯想所形成的比喻卻分屬于不同的聯想類型。把胡須比作溪流圓石邊緣的苔絲,屬于相似聯想。相似聯想的原理是在兩種不同的事物之間因其一端的相似而展開,胡須與苔絲是絕不同類的事物,但它們在絲狀排列的形式上和綿軟柔順的質感上有著極為相似的一面。而把胡須比作嬰孩耳際柔柔的胎毛,則屬于相類聯想。相類聯想的原理是在同類事物之間展開,無論是胡須還是胎毛,它們都屬于人體上的毛發。通常情形下,同類事物之間形成比喻是違反以“不類為類”的比喻原理的,因故其修辭價值會大為貶值,就如同形容山羊的皮毛像綿羊一樣潔白柔亮,就屬于極其貧乏的比喻。昌耀這個看上去犯了比喻忌諱的句子,讓人玩味之后還是覺得新鮮,那是因為一般人不會把成年人的胡須和嬰孩的胎毛聯想起來,這不僅僅是它們之間隔著一段很長的光陰,更重要的一點是,人們不大容易關注到嬰兒毫不醒目的胎毛,尤其是男性作家,很少會用如此細膩、溫柔的母性目光去觀察,何況昌耀還把胎毛的范圍精確到嬰兒的耳際,似乎那里的胎毛比頭頂、腦顱后面的胎毛要更柔軟一些。
四
王國維先生在《屈子文學之精神》中專門論及南北方文學的優劣等差:“南人想象力之偉大豐富,勝于北人遠甚。彼等巧于比類,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則有若北溟之魚,語小則有若蝸角之國;語久則大椿冥靈,語短則蟪蛄朝菌;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陽,四子獨往:此種想象決不能于北方文學中發見之。……以我中國論,則南方之文化發達較后于北方,則南人之富于想象,亦自然之勢也。此南方文學中之詩歌的特質之優于北方文學者也。”這篇文章更大的一個價值和意義在于,靜安先生基于對中國文學史的觀察做出了一個重要的預言和卓越的判斷:“而大詩歌之出,必須俟北方人之感情,與南方人之想象合而為一,即必通南北之驛騎而后可。”驗之以文學史,能通南北之驛騎的詩人,古代以屈原為代表,當代則以昌耀為代表。
1980年,昌耀在《南曲》一詩里首次以文學的方式袒露青海之于他詩歌創作的巨大影響:“難道不是昆侖的雄風/雕琢了南方多彩的霜花,/才裝飾了少年人憧憬的窗鏡?”在此詩的結束部分,昌耀還有一句經典的表述:“我是一株化歸北土的金橘。”這句話的出處來自《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毫無疑問,昌耀在他的文學理念中是極為自覺和深刻地認同地理環境與某個地域的人文環境對作家性情、風格的塑造和影響。但是,長期以來由于昌耀的詩歌給世人展示出青海和西部雄奇博大的邊地風貌或“北人氣象”,以至于我們有所忽略昌耀原本作為沅江水哺育的湖湘才俊,在骨血里所秉承的“南人氣象”。
無論從何種視角觀察,一個跨越地理區隔和特定文化環境的作家,在他由原鄉寄身他鄉的生命羈旅當中,他本人必定會攜帶有關原鄉的氣息、經驗、記憶,以及沉積于心的諸多物象、無意受到的浸淫而融入他鄉。基于此,文學的形象、意象、格調、韻致、風骨、情感風貌等等,將會化育出比物種雜交還要豐富多變的精神果實。如同卡爾維諾在《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中所言:“我們可以這樣說,在文學想象力視覺部分形成的過程中,融匯了各種因素:對現實世界的直接觀察、幻象和夢境的變形、各種水平的文化傳播的比喻性世界和對感性經驗的抽象化、凝練化與內在化的過程,這對于思想的視覺化和文字的表述都具有頭等的重要意義。”攜帶并且傳播湖南或者更其廣大的南方文化基因,是我們觀照昌耀詩歌文化移植的一個重要經驗。
朱季海先生在《初照樓文集·楚辭長語》里解釋《河伯》里的“乘水車兮荷蓋”一語時,有一節關涉南北詞語雜交的訓詁:“河伯水車,僅見《楚辭》。蓋洞庭、云夢、大澤之鄉,其民狎習波濤,弄潮如驅車,故發為想象,形諸名言,曼妙如此,詩人有取焉爾。此北方之神,浸淫楚祠,流被歌詠,便宛然南風矣。沈復《浮生六記·浪游記快》:‘甲辰之春,余隨侍吾父于吳江何明府幕中……一日,天將晚矣,忽動歸興。有辦差小快船,雙櫓兩槳,于太湖飛棹疾馳,吳俗呼為出水轡頭。轉瞬已至吳門橋,即跨鶴騰空,無此神爽,抵家晚餐未熟也。甲辰乾隆四十九年,公元一七八四年,時三百二十一歲耳。今吳語猶謂絕塵而馳曰‘出轡頭,然不聞‘出水轡頭。斯言亦以車馬為隱喻,雖地有吳楚,時有古今,其為口俏(吳俗謂語雋為‘口俏)一也。”
朱先生說到的湖南地區百姓“狎習波濤,弄潮如驅車”的表述,我們在湘籍當代作家沈從文先生的文字里也屢屢見到船夫、水手等水鄉物事的描述。如同“河伯”一詞由北方輸入南方,“出轡頭”一詞則是由游牧民族把騎馬方式輸入南方。昌耀在他的詩篇里,尤其是在他初來乍到青海時,水鄉意象和南國風物被他頻頻植入青海的書寫。無獨有偶,清代大臣、湖南湘陰人左宗棠帶領一萬湖湘子弟收復新疆時,把散落在新疆、河西走廊戰場上的烈士遺骸暫存于甘肅蘭州市天水路南段的“義園”,其外形輪廓就是一條大船。這是這些南國義士們的鄉愁所系,是他們家鄉情結的自然投射。昌耀也是如此。在他所有的詩集或者詩選本里,置于首位的一首詩就叫《船,或工程腳手架》,“船房”“桅”“水手”這些在高原罕見的名物,被自然嫁接到青海。在青海黃河上渡河而過的,不是南方的船舶,而是青藏高原獨有的“羊皮筏”或“牛皮筏”。《水色朦朧的黃河晨渡》:“水手熟識水底的礁石”,“一眼就認出了河上搖棹扳舵的情人”;《冰河期》:“在白頭的日子我看見岸邊的水手削制槳葉了”;《山旅》:“正是以膀臂組合的連桿推動原始的風葉板,/日日夜夜高奏火的頌歌。像是扳槳的船工,/把全副身心全托付給船尾的舵手”;《隨筆》(審美):“我卻更鐘情于那一處鄉渡:/漫天飛雪、/幾聲篙櫓、/一盞風燈……(可參照杜甫《漫成一絕》:“江月去人只數尺,風燈照夜欲三更。”陳維崧《桂殿秋·淮河夜泊》:“船頭水笛吹晴碧,檣尾風燈飐夜紅。”);《風景湖》:“滑動著的原野。/幾株年青的船桅”;《劃呀,劃呀,父親們!》里的船夫。涉及南方物事的詩篇,在此聊舉數例:《秋之聲》:“旅次古城,望樓外燈火亮了萬頃珠貝”;《在敦煌名勝地聽駝鈴尋唐夢》:“——是誰們在那邊款款奏著/銅鑼鈸呢?那么典雅而幽遠,/像漁火盈盈……//……記起初臨沙山時與我偕行的東洋學者/曾一再駐足頻頻流盼于系在路口白楊樹下的/那兩峰身披紅袍的駱駝——美如江邊的船……”;《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個孩子之歌》:“說泥墻上仍舊嵌滿了我的手掌模印兒,/像一排排受難的貝殼,/浸透了苔絲。//說我的那些古貝殼使她如此/難過。”“牛伙里它的后尾總是翹得比誰的都高挺,/像一株傲岸的蒲葵……”;《騰格里沙漠的樹》:“銀白的月/把幻想的金桂樹/貼近/騰格里沙漠幻想的淡水湖。”《激流》:“海螺聲聲/是立在屋脊的黃河子民對東方太陽熱烈傳呼。”《獵戶》:“油煙騰起,照亮他腕上一具精巧的象牙手鐲。”《荒甸》:“等待著大熊星座像一株張燈結彩的藤蘿”;《良宵》:“這在山岳、濤聲和午夜鐘樓流動的夜”;《給我如水的絲竹》:“我渴,給我如水的絲竹之顫動,盲者!”《柴達木》:“我看見鋼鐵在蒼穹/盤作扶桑樹的虬枝。/濃縮的海水從隱身的鯨頭/噴起多少根泉突。”《幽界》:“山岳的人面鳥”,“一只鳳凰獨步”;《高大坂》:“一聲聲剝啄,是山魈之心悸。”《靈霄》:“新月傍落。山魈的野語。”《懸棺與隨想》:“昂起的低潮/把南國山水間古人懸棺喚起的思緒轉作喧囂的騷音”……
以上并不完全的示例,讓我們僅從詞語或意象層面感受到了“必通南北之驛騎”之后所能呈現出的局部風神意態,語言上的南方氣象。事實上,昌耀詩學的境界,絕不止于如此一端。昌耀從來不玩弄文字的積木,他從來都是以他的氣血,他胸中郁結的塊壘,彈奏他命運的鍵盤。他給當代詩歌的獨特貢獻,是在詩歌的整體氣息上熔鑄南北氣韻,將南人擅長的瑰麗想象與“化歸北土”后的曠悍深邃糅合在一起。正因為昌耀在詩歌骨相上具有“南人北相”的特征,他詩學的風神格調便出現了兼容并包的博雜性、繁復性,甚至在他的遲暮風格里頻頻出現復調性抒寫。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之后,昌耀就把自己變成了一個詩歌的夸父。他追趕的步幅,隨著生命時限所造成的強烈的迫促感、焦慮感,還有夾雜其間的頹喪感,讓昌耀奔逐著的詩探索,日益和他身后的詩壇、和他所處的時代拉開了距離。尤其是昌耀在遲暮之境開啟的玄奧詩旅,為后來的詩人和讀者留下了意義和價值尋索的巨大深壑。
五
《總集》和本書的最末一首詩《一十一支紅玫瑰》,盡管在思想性和審美表達上與昌耀諸多的重量級作品無法等量齊觀,但因其是詩人在彌留之際寫于病榻的絕筆,這首詩作至少體現出兩個方面的特殊意義:
一是它的時間形態。它屬于巴赫金所說的“危機的時刻”“邊沿的時間”,是“意識的最后瞬間”。在這個時刻,會表現出異常復雜精微的兩重性。比如此詩刻錄下昌耀處于毀滅性境遇時的臨終心理和臨終狀態:一會兒迷亂一會兒清醒;一會兒充滿對人世的戀戀不舍,一會兒又流露出棄世而去的斬截;一會兒苦苦掙扎,一會兒又乖順聽從……其情狀直通柴可夫斯基的《悲愴交響曲》。昌耀對“意識的最后瞬間”,對這種意識深層的“暗物質”,對即將跨入死亡門檻的人的精神活動,體現出一種超乎常人的敏感和特殊的洞察力。他先后以片斷的形式書寫過兩次“意識的最后瞬間”。在寫下此詩的兩年前,昌耀就在《語言》里銘刻下一個臨刑的少年殺人犯被軍警押載上死囚的刑車時發出的一句問語:“叔叔,我上哪一部車?”之后,再次書寫死刑前“意識的最后瞬間”,是在1999年創作的未完成的詩稿《20世紀行將結束》里。這個詩題視野宏大、調門隱含悲愴,好像是要給20世紀的一百年光陰劙刻一幀個性化的速寫,也好像有點卡爾維諾寫給未來千年文學的意味。不論怎樣,這是一件昌耀生前雄心勃勃的作品,意欲刷新他寫作紀錄的作品,我們僅從此詩文末標注的寫作時間從1988年開始寫作到1999年1月9日整理完畢,其間寫作的時間跨度竟長達11年之久!這可是昌耀全部作品里花費時間最長的一部作品。如此漫長的寫作,可以想見昌耀艱難運思的過程。我們可以從中揣摩到昌耀啟動他的“跨世紀工程”入手得多么早啊!他一生的后半程都在“趕路”,不單單是出于“怵他人之先我”的焦慮。就詩人的創作動機來看,這部作品當是他詩歌總譜里慮深懷遠的一聲“詠嘆調”,是他站在新舊世紀交替之際,經過變調的又一曲“登幽州臺歌”!只可惜殘編斷簡只留下輝煌殿堂的桁架、柱礎和窗欞。
在這部有著博大抒情韻腔和調式的“斷章”里,昌耀以文摘的形式(一則來自《文摘報》,一則來自《文學報》),分別在《殘編2:》和《殘編6:》,兩次寫到未提姓名但可一眼識別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瞿秋白就義前“意識的最后瞬間”。前一個題記側重于瞿秋白就義前的慷慨陳詞,話語帶有鮮明的布爾什維克意識:“繼而高唱《國際歌》,打破沉寂之空間。酒畢,徐步赴刑場,前后衛士護送,空間極為嚴肅。經過街衢之口,見一瞎眼乞丐,回首一顧,仍有所感也。”后一個題記側重于瞿秋白書寫絕命詩時表現出的詩騷性情:“此時軍法處長催他起程赴刑,秋白又揮筆疾書——‘方欲提筆錄出,而斃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半有句:‘眼底煙云過盡時,正我逍遙處。此非詞諺,乃獄中言志耳。”前后相繼的兩件作品,可以印證他對“意識的最后瞬間”這種人生極致體驗的念茲在茲,也是他吟唱出自己的“天鵝之歌”時,再次傳遞“終古之創痛”時的無盡玄愁和無盡喟嘆。
二是這首詩在詩行排列、詩句字數上給人留下過目難忘的對稱、均衡的形式美感。綜觀昌耀一生的詩作,早期的《月亮與少女》,便成就過“詩經體式”(四言句式)的整飭之美。昌耀對這種只有在古典詩詞里頻頻閃爍的、蘊含著漢語文字獨特文化根性的形式美感與節奏美感,一直保持著深切的感應和沉醉。《兇年逸稿》《給我如水的絲竹》《水手》《秋之聲》《建筑》《河床》《色的爆破》《招魂之舞》《懸棺》《冷色調的有小酒店的風景》《眩惑》《聽候召喚:趕路》《盤陀:未聞的故事》《極地民居》《在古原騎車旅行》《一片芳草》《這夜,額頭鋸痛》《拿撒勒人》《花朵受難》《意義空白》《薄曙:沉重之后的輕松》《意義的求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些作品中整飭、均衡、對稱的語句對偶雖說都體現在局部,但它們足夠傳遞出昌耀對古典詩歌氣韻、節奏、審美語境深度欣賞的強大信息。唯一和《玫瑰》形制極度相仿的是1994年寫下的《菊》。《玫瑰》以兩句為一節,共分為九節;《菊》則是四句為一節,共分為三節。稍加比對,《玫瑰》最長的句子字數超過《菊》。《菊》是詩人正常情況下的寫作,而《玫瑰》則是在極端境況下的寫作。在忍受病魔的極度創痛中寫下如此齊整的詩行,我們不能不為昌耀在詩歌上最后施展的“絕技”而驚嘆不已。在平靜狀態下寫出整齊的詩句相對容易,在大限將至的峻急時刻寫下如此整齊的詩句,則無異于他9年前寫過的那位以手掌在土地上劃行的關西大漢,每前行一步“像是匍伏波濤將溯流而上的船只艱難推進”。這一定是他在靈魂得到片刻寧靜時的傾心灌注,或者說是以他頃刻間獲取的“純粹美之模擬”和審美移情來鎮痛和減弱難忍的痛苦。即便是處在如此危重的當口,精敏、勇毅的昌耀偏要在此端端寫成9節?此中當蘊含著諸如極度的尊重、九九歸原、強力、長久等數字象征的隱秘信息。其整飭端莊,如他一生追求的“完美”,如一尊經過窯變的施釉大鼎。
六
1957年,昌耀寫了一首僅有8行的短詩《高車》。1984年年末,昌耀對這首27年前的舊作作了刪定,并加了一個題記(他自己稱為“序”):“是什么在天地河漢之間鼓動如翼手?……是高車。是青海的高車。我看重它們。但我之難于忘情它們,更在于它們本是英雄。而英雄是不可被遺忘的”。其中詩人創造了“翼手”這么一個陌生的詞語。在漢語語匯的構成里,以手作為后綴組成的詞語,比如“舵手”“水手”“旗手”“歌手”“棋手”等,都是指所從事的職業或者動作。那么“翼手”又是什么意思呢?除了“翅膀”這個“翼”字的常見義項,還有舊時軍隊編制分左中右三軍,左右兩軍叫做左右翼。還有一個偏僻的義項,是“十翼泛清波”里當“舟”這個意思。這幾個意思,都沒法與此詩的語境吻合。參照詩人其他的詩篇,我發現昌耀喜歡拿車輪這個帶著運動感、速度感的詞語,和“翼”字搭配在一起,比如《木輪車隊行進著》:“……這車隊/一扇扇高聳的車翼好像并未行進著?/這高聳的一扇扇車翼/好像只是座立在黃河岸頭的一扇扇戽水的圓盤?”“木輪車隊高聳的輪翼始終在行進著。”比如《雄風》:“我深信/只有在此無涯浩蕩方得舒展我愛情宏廓的輪翼。”比如《河床》:“我愛聽兀鷹長唳。他有少年的聲帶。他的目光有少女的/媚眼。他的翼輪雙展之舞可讓血流沸騰。”比如《感受白羊時的一刻》:“天路縱馳。翼輪闌干。夢影華滋。”《骷髏頭串珠項鏈》:“……插立在車翼的白布經幡像豎起的一只大鳥翎毛滿是塵垢。”如此看來,“翼手”是昌耀的一個擬人化了的曲喻,暗含有飛馳的運動感,有若屈原“乘回風兮載云旗”里那般車輪的速度與激情,是一種驅動運動的力量,一種充盈的生命力,一種如他所欣賞的“瞬刻可被動員起來的強大而健美的社會力量的運作力”,一種恢宏、盛大、厚重、莊嚴的演奏——“是以幾百、上千個體力勞動者同時運作爆發而得的體力作為動力,帶動特殊器械裝置為之鼓風,使氣流頻頻注入數百根、數千根金屬或木質管孔,發出來足以與其規模相稱的、令人心旌搖動的樂音。”總之,“翼手”是一種澎湃激情和生命強力的象征,是他的大詩歌觀在審美表現層面的最初呈現。
現在,我們回到《高車》的前兩節:
從地平線漸次隆起者
是青海的高車
從北斗星宮之側悄然軋過者
是青海的高車
昌耀鎖定西北大地以往常見的那種大轱轆車來書寫,但對其形狀之大并未作特寫處理,而是將其置入一個大視角、超長焦、大縱深的空間,并且不是將高車當作靜物來描寫,而是作為持續移動的意象來處理。讓人們費解的是,在大地上馳行的高車,怎么會跑到天上從北斗星宮之側悄然軋過呢?須知這不是詩人的幻想或產生的幻象,它是昌耀對視覺經驗里前景和后景相重疊后所形成的視覺錯覺的巧妙的詩性轉化,是昌耀對青藏高原極高的空氣透明度下清晰星象的敏銳洞察。這種視覺錯覺,一直被攝影家、畫家、電影攝影師們屢試不爽地運用于奇妙畫面的設計。擅長繪畫的作家阿城在《孩子王》里借王福的作文,就利用這一視覺錯覺寫出與昌耀詩句異曲同工的畫面:“早上出的白太陽,父親在山上走,走進白太陽里去。”后來昌耀寫下的“一百頭雄牛低懸的睪丸陰囊投影大地。/一百頭雄牛低懸的睪丸陰囊垂布天宇”,同樣采用的是宏廓的視角,但這一次垂布天宇的睪丸陰囊已不是詩人的視覺錯覺,而是詩人夸張性的主觀想象。
利用天地之間形成的夾角來成像造境,是昌耀書寫宏大境界的視覺和心理的雙重經驗。偏于視覺的,像《去格爾木之路》里這樣的描述:“鹽湖已被擠壓于天地之夾層。”(利用空間中物體大小的反襯效果)偏于心理的,像《巨靈》里這樣的描述:“我攀登愈高,發覺中途島離我愈近。/視平線遠了,而近海已畢現于陸棚。/宇宙之輝煌恒有與我共振的頻率。/能不感受到那一大搖撼?”
用天象作為詩歌意象,也是昌耀詩歌營造恢弘、崇高意境的重要途徑。其本質涉及昌耀詩學中極為醒目一個特點:廣闊、深邃的時空觀。王國維先生當年在《人間詞話》列舉“明月照積雪”“大江流日夜”“澄江凈如練”“山氣日夕佳”“落日照大旗”“中天懸明月”“大漠孤煙直”“黃河落日圓”等古典詩詞片段,批識道:“此等境界,可謂千古壯語。求之于詞,則納蘭容若塞上之作,如《長相思》之‘夜深千帳燈、《如夢令》之‘萬帳穹廬人醉,星影搖搖欲墜差近之。”靜安先生沒有明確點出邊塞或者游牧民族生活的疆域,往往因為遼遠開闊的地理環境會給人們視覺經驗上帶來一望無際的視覺感受。這種視覺感受隨后又會賦予人們心理感受上的博大與崇高。納蘭詞境的高曠,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實際上是唐代邊塞詩人開啟的博大詩境在清代迢遞的余緒,昌耀則是在當代新詩里一次更其遙遠的接續和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