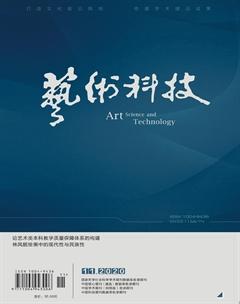媒介文化視野下短視頻文化繁榮的原因與危機
摘 要:隨著中國新冠疫情暴發,國內經濟受挫,文化產業受到極大打擊。而以UGC(用戶生成內容)生產模式為核心的短視頻卻逆流而上,其經濟營收在疫情期間不降反升,快手、抖音、美拍等短視頻APP成為用戶了解疫情、消磨時間、表達自我的主要平臺。當然,短視頻欣欣向榮的現狀之下還隱藏著巨大的危機,因而本文從媒介文化角度來分析短視頻得以興起、繁榮的背后因素,以及潛藏在短視頻繁榮陰影下短視頻傳播的技術陷阱和文化危機。
關鍵詞:媒介文化;短視頻;文化繁榮;原因;危機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0)11-00-04
2020年1月底,國內新冠疫情暴發,整個社會都被按下暫停鍵,全國人民的經濟受到巨大的影響。疫情令餐飲業、旅游業等行業受挫的同時,卻又對一批新興行業、互聯網行業產生積極的影響。無人經濟、新基建行業、短視頻行業等領域面臨新的機緣。以UGC(用戶生成內容)生產模式為核心的短視頻在互聯網科技發展的大環境下逐漸如魚得水,快手、抖音、美拍等短視頻APP成為用戶了解疫情、獲得樂趣、獲得認同、展現自我、表達自我的主要平臺。用戶既是使用者,也是生產者和服務者,實現了內容網絡、關系網絡以及服務網絡的三網融合。然而,新媒介技術和內容生產模式的興起,并不代表著烏托邦式新世界的出現,短視頻的繁榮之下還隱藏著巨大的危機。“媒介文化因媒介而生,又帶動文化而變,并且成為文化變遷的一種誘因。文化與媒介永遠是互為表里,合而為一的。沒有媒介作為依托,文化就失去鮮活。缺少文化作為內容,則媒介永遠是無靈魂的軀殼。”[1]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短視頻是媒介文化新時代的載體。本文就從媒介文化角度來分析短視頻得以興起繁榮的背后因素,以及潛藏在短視頻繁榮陰影下短視頻給受眾及社會帶來的不利影響和短視頻本身面臨的運營危機。
1 短視頻文化崛起的原因
從Web1.0到Web2.0,再到如今的Web3.0時代,不斷發展的網絡深入人們的日常生活。越來越多網民在網絡世界聚集,而網民的聚集使得媒介技術進一步發展,從傳統的文字報道到如今風靡的短視頻傳播,從傳者為主導的單向傳播模式到如今受者為王的雙向互動傳播模式,媒介延伸了人的感知。站在時代的拐點,以UGC(用戶生產內容)生產模式為核新的短視頻開始繁榮。
1.1 技術改變了媒介生態
隨著移動技術的發展和人工智能技術的出現,傳統媒介環境已經不能迎合現代信息社會瞬息萬變的現狀,受眾渴求更豐富的信息和更高的傳播效率。然而,傳統的媒介環境對新事物的接納是“細嚼慢咽”的方式,漸漸導致媒介環境與受眾之間的平衡瓦解。而與此同時,移動終端和互聯網的高速發展使得短視頻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不斷壯大,AI(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使得每一臺移動設備成為信息交互的終端,技術的進步和人們心態的轉化使得新的媒介環境漸漸形成。在新的媒介生態下,“智能+短視頻”模式改變了媒介經營模式,從傳統的用戶獲取升級為互動式的用戶經營。基于此,短視頻一舉成為“互聯網+”時代的“網紅”媒介產品之一。
1.2 快餐成為了文化選擇
生產力的繁榮使得人們對精神文化的需求日益增長,簡單的物質滿足已經不能給人們帶來幸福感,精神層次的滿足成為人們新的追求。由于生活方式的快節奏化,嚴肅枯燥的文化產品已經不能引人駐足,需要費時費力費腦的精英文化被“打入冷宮”。相反,給受眾提供娛樂、帶來消費的快餐文化成為主流。所謂快餐文化,就是指即時消費的文化,一切以“快”為準則,是快節奏生活的產物[2]。在快餐時代,由于越來越沉重的腦力負擔和碎片化的個人時間限制,好懂不費腦的快餐文化一舉擊敗精英文化成為社會選擇。短視頻作為新時代快餐文化的代表,以其自身強大的創造力和傳播性成為消費主義社會的“天選之子”。2017年,短視頻風靡于互聯網及移動客戶端,其中,抖音APP憑借技術流、生活向、自導自演等多種創意短視頻躋身國內受歡迎的短視頻平臺,甚至成為日本、美國等國在內最受歡迎的APP。
1.3 社交成為傳播渠道
人是社會的動物,人從與他人的社交中尋求認同。智能手機的普及和移動技術的發展,讓人與人之間的社交轉移到虛擬世界,手機移動端的流行改變了用戶獲取信息、社交溝通的渠道,并使得社交時代到來。隨著社交時代的到來以及各種自媒體的崛起,現代技術的發展和傳播權利下移,使得人們的自主意識和自我表達意識被激活。自媒體成為人們表達自我的渠道,甚至草根、布衣可以通過自媒體實現改變地位、跨越階級的目標,這使得人們對自媒體越發趨之若鶩。以自媒體平臺興起為標志,一個“人人都能發聲,傳播無處不在”的互聯網群體傳播模式興起。短視頻自由自主的制作周期、簡單便捷的制作方式、高效快速的傳播渠道,正好迎合了人們傳播的需求,因而短視頻被網友廣泛地接納和使用,并隨著用戶的激增而風靡起來。
1.4 短視頻成為吸引用戶的陷阱
算法是指通過一套相對完整且具有較強邏輯性的命令來描述解決問題的策略機制[3]。簡單來說,算法基于用戶的興趣偏好和個人特性,人工智能可以根絕不同用戶的需求提供個性化服務。以最近很火的短視頻APP抖音為例,抖音推薦機制主要是以大戶數據結合人工審核的機制來衡量一個短視頻作品是否可以上熱門。抖音是一個去中心化的算法平臺,任何一個用戶都有可能成為“網紅”,也許只是一個小視頻,用戶就可以收獲成千上萬的粉絲。只要短視頻內容受歡迎,用戶就會越來越火,抖音成為名副其實的“造星工廠”。這種算法推薦機制形成了一種互動傳播的效果。
短視頻的另一大技術陷阱是以VR(虛擬現實)技術為基礎的沉浸式傳播,這種VR技術可以給用戶游戲式的第一人稱體驗。通過刷視頻,用戶可以以第一視角觀看并體驗視頻內容,一不小心就會沉浸其中,這種方式給受眾的參與感極強[4]。抖音就通過其沉浸式使用界面,給予受眾強烈的場景帶入感,抖音對用戶的要求極低,用戶觀看視頻的場景和時間要求很低,幾乎沒有要求,只要拿起手機就可以觀看。而且由于視頻時長較短,視頻可自動播放,以及簡單的上下滑動切換視頻方式,用戶的注意力可以被瞬間捕獲。在此之后,抖音短視頻通過連續不斷的界面播放內容來制造“陷阱”,把用戶注意力牢牢把持在短視頻中。
2 短視頻傳播的文化危機
任何事物的出現都不是絕對正面的,短視頻也是如此。短視頻給用戶帶來表達新渠道的同時,也帶來了快餐文化傳播的文化危機,如泛娛樂化嚴重、生產內容同質化、出現信息遮蔽效應。
2.1 消費主義視角下的泛娛樂化嚴重
鮑德里亞認為:“在物品豐盛的時代,消費作為生產的起點和終點,成為刺激再生產欲望、拉動內需、促進社會發展的動力,成為支撐整個社會經濟運行的靈魂。”[5]隨著消費主義思潮的盛行,人們消費的范圍和消費的對象在不斷擴大,尤其是文化產業消費比重日益增長,逐利的資本自然不會放過文化產業背后蘊藏著的巨大經濟效益。消費主義導致的娛樂精神的泛濫成為短視頻的危機,短視頻領域泛娛樂化現象嚴重。正如美國學者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里提到:“一切公眾話語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并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泛娛樂化本質上是去中心化,在過度娛樂化的環境下,人們長期接觸毫無營養的碎片化信息。這些碎片化信息會對受眾的自我認知和認知方式產生影響,更有甚者會讓受眾陷入錯誤的文化認同,并對主流文化產生抵觸情緒。現在有很多短視頻傳播者為了獲得流量,故意做出一些夸張的動作,甚至在線編故事,以博取“觀眾老爺”的青睞。長期沉浸在這些短視頻包圍的氛圍中,用戶由于“涵化”效果的影響,對自身的認知不知不覺會向短視頻暗含的負面價值觀念靠攏,給社會和諧穩定埋下地雷。尤其是自身價值觀念還未成型的青少年用戶,更容易被短視頻里構建的世界影響。
2.2 群體傳播下同質化內容嚴重
“作為一種源自社會各階層的訴求表現方式,形成群體傳播的源泉更像消費主義思潮中‘欲望的一種延續,在得到越來越多人認同的同時,群體傳播這一媒介文化現象也變成了一種普適的,能夠代表社會各階層思想觀點、價值判斷和行為傾向的社會思潮。”[6]在各階級的訴求通過各種表現方式得到越來越多人認同后,群體傳播從一種文化現象轉變為一種社會思潮。也就是說,群體傳播思潮中裹挾的受到絕大多數人認可的個人意志,抑或是為數眾多而又相似的個人意志。在短視頻領域,群體傳播的力量體現在用戶的意志成為一只充滿力量的“無形的手”,這只手賦予青睞的短視頻內容巨大的流量和關注,使得視頻傳播者一舉跨越階級的桎梏,成為“網紅”甚至明星。其他傳播者為了復制這樣的成功,迅速模仿并病毒式傳播類似的視頻內容。很多傳播者為了迎合用戶,甚至將視頻內容的重點放在了搞笑、低俗、暴力等高度同質化的興趣點上,進而吸引大量關注。當出現一個現象級的短視頻時,出于對流量的追求,很多類似內容的視頻開始層出不窮。短視頻平臺為了商業利益,對這些同質化內容不管不顧,甚至推波助瀾,這樣的默許與縱容,使得同質化內容越來越多,短視頻的內容生產進入一個惡性循環。
2.3 算法推薦導致信息遮蔽效應
美國學者凱斯·桑斯坦曾提到,受眾進行信息選擇和接收時會受到個體差異和長久形成的思維固化的影響。受眾會依據自身的觀念而選擇自己感興趣的、與個人觀點相同或相似的信息,而對于相悖的觀點則會進行歪曲理解,更有甚者會對這些信息進行選擇性屏蔽。在短視頻領域,大數據算法會根據用戶的個人喜好推薦內容。然而,人工智能系統還存在這樣那樣的缺陷,固執且片面地給受眾推薦大量同質化內容,使得用戶長期主動或者被動地瀏覽相似內容。算法推薦導致的信息遮蔽效應影使得受眾看不到差異性信息,久而久之,用戶形成固化思維。在短視頻領域,算法推薦導致的信息遮蔽現象尤為明顯。比如,一個用戶喜歡小寵物,那么,有關寵物的視頻就會不停地推薦給這個用戶,使得該用戶打開平臺,推薦的視頻九成都是相似內容。大量同質化視頻被推薦給用戶,使得用戶的信息接收面變窄,思維方式、認知模式和價值觀持續固化。算法成為“過濾氣泡”,多樣化的信息在傳播的過程中被過濾掉,只剩下同質化內容。這不僅會導致信息傳播的多樣性受到阻礙,還會使用戶產生巨大的“知識溝”,使得個體越發孤獨,形成惡性循環。
3 結語
在新的媒介生態和互聯網群體傳播時代下,移動短視頻憑借強大的實力“井噴”崛起,它以技術陷阱抓住用戶心理,積累大量用戶群體。2020年1月底到3月底,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現還給短視頻一個難得的發展機遇期。人們“宅”在家里刷手機,短視頻行業營收實現與實體行業經濟下行相反的“逆增長”,天時地利人和。但是,在短視頻行業欣欣向榮帶來利好的同時,這背后還潛藏著文化危機——泛娛樂化、同質化內容、信息遮蔽……算法機制升級、未成年人模式推廣、違規懲治加強等一系列措施有待在短視頻領域施行推廣。雖然短視頻行業還有很多問題存在,但隨著5G技術的發展和人工智能技術的完善,在這個注意力為王的時代,短視頻有著廣闊的前景。因而,短視頻行業的長久繁榮更加需要各方來共同維護。
參考文獻:
[1] 楊俊倫.媒介文化及其對社會的影響[D].武漢大學,2004.
[2] 符國偉.“快餐文化”與現代閱讀方式之嬗變[J].圖書館界,2010(05):11-13.
[3] 趙辰瑋,劉韜,都海虹.算法視域下抖音短視頻平臺視頻推薦模式研究[J].出版廣角,2019(18):76-78.
[4] 劉國強,張朋輝.交互涵化與游戲范式:媒介文化批判視野下短視頻對兒童影響的雙重維度[J].渭南師范學院學報,2020,35(02):63-69.
[5] 黎春嫻.消費:一種社會結構的詮釋——兼讀讓·波德里亞的《消費社會》[J].北方論叢,2007(6):132-135.
[6] 隋巖.媒介文化研究的三個路徑[J].新聞大學,2015(04):76-85.
作者簡介:張盼盼(1996—),女,江蘇揚州人,揚州大學新聞與傳媒學院2019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媒體傳播。
指導老師:馮銳(1966—),男,甘肅正寧人,研究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揚州大學新聞與傳媒學院院長,揚州大學數字媒體應用研究所所長,主要從事網絡與新媒體傳播、新媒體社會責任等領域的研究工作,研究方向:社交媒體傳播與影響,信息化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