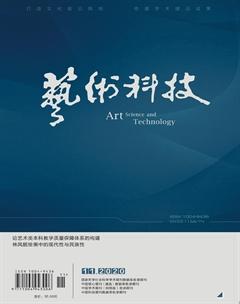鏡像形成階段下的程蝶衣的自我身份構建
摘 要:本文依據拉康鏡像理論的鏡像形成階段,開展對《霸王別姬》中程蝶衣性別認知從男到女的過程的分析。由于鏡像的永恒性,因此當幻象消失、鏡像破滅的時候,生命的存在也就沒有了意義。
關鍵詞:鏡像階段;《霸王別姬》;性別認同;自我身份構建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0)11-00-05
1993年在法國戛納國際電影節上,華語影片《霸王別姬》榮獲金棕櫚大獎。該影片成為首部獲此殊榮的中國影片,也是唯一一部同時獲得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大獎、美國金球獎的最佳外語片的華語電影,是華語電影難以超越的巔峰之作。
該電影的主線主要講述了程蝶衣與從小一起長大的梨園師兄段小樓一生的情感糾葛與愛恨情仇,電影隱喻出程蝶衣在藝術與生活、現實與人性、國家與個人的矛盾中不斷構建自我身份認知的過程。從一句“奴本是女嬌娥,又不是男兒郎”開始了程蝶衣鏡像形象下的自我構建。不斷堅定的自我信念與自我完善形成的泡沫,終將在多年之后段小樓的“奴本是男兒郎,又不是女嬌娥”的回憶下破裂,打破鏡像中的本我而回歸自我的程蝶衣走向了虞姬的結局。
1 女性性別認同的構建
拉康認為,人類對自身形象的構建最初起源于人們對形象的認知,具體開始于嬰兒面對鏡中形象產生的認同感。此認同表示的是鏡外主體趨向于整體性的自我形象構建的形成,同時趨向于自主性接受外部形象的構建以及同化。通過鏡子其實也就是外部環境以及他人對自己的評價和認識作為媒介,嬰兒尚未成熟的意識變得逐漸認同自我,逐漸變得完整,進而形成對自我的整體認知。出生時的嬰兒處于一個混沌整體感之中,嬰兒會覺得自身與母親甚至與周圍的環境沒有任何區別,嬰兒對于外部環境的感知是零散化的,既沒有整體意識也沒有主體意識。進入鏡像階段,嬰兒面對鏡子經歷了一個過程。當嬰兒被帶到鏡子前,嬰兒會感到好奇并不能完全分辨出自身的形象;進而嬰兒會通過身體的運動與形象的轉變區別出鏡子中自身的形象。最終嬰兒會形成整體對于自身形象的認知,分辨出鏡子中映射出的形象就是自己,并且為自己能看出自己而感到喜悅。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發現,鏡中嬰兒的形象讓嬰兒初步認知了自身的整體形象,并且形成了對自身整體形象的判斷,形成了主體概念:這就是我[1]。
如果把“鏡子階段”的鏡子僅僅理解為現實生活中真實的鏡子,那么便是我們的局限。人類在“鏡子”面前,鏡中之我就是一個“認”的主體,那么鏡中的映像就是本我在外在環境等一系列格式化的影響下形成的格式塔,而本我形象的構建是以外在環境以及他人評價的格式塔為依托,逐步認同和同化而形成的。對于內在的自我而言,自我的依托或承載體包括自我在內的影像都是自我的他者鏡像[2]。程蝶衣的藝術生涯以及自身的藝術認同就像是一個嬰兒被帶到鏡子前,這鏡子就是外界環境對程蝶衣的影響,從而形成了主體意識的過程。
1.1 “鏡中”的整體性認知——小豆子性別認知的轉變
根據拉康的鏡像階段(Mirror Stage),第一階段便是在“鏡中”呈現了一個自身的形象,也就是說他人環境不僅是過眼云煙,更重要的是接收到他人以及環境不論是強行還是暗示中反饋的信息后構建鏡中的自己[1]。
程蝶衣在“鏡中”形成了自身的整體性認知。但是,對于程蝶衣來說,這個過程是強行的、擰巴的。電影中的“鏡子”就是影響程蝶衣的外界環境以及他人的態度和評價,外部環境是零散的,沒有任何整體性。第一片碎片產生在小豆子(程蝶衣幼時)踏入戲班前后。該階段,小豆子就如同剛出世的嬰兒一般對這個自我認知的惶恐以及反抗:小豆子從小就是在妓院的女性環境下長大,并且在一個男扮女裝的教養方式下生活;為進入戲班,他的母親將其六指決然砍斷,“今兒個還只是破題,文章該在后頭那”,[3]該決斷就像是對小豆子男性自我認知的“閹割”。第二篇碎片產生在小豆子學戲的過程當中:小豆子對于自身男性性別認知以及對于女性性別的反感遭到了師傅的嚴厲責打,甚至是所謂的班規“打通堂”。以其糾正小豆子在“思凡”中的“我本是男兒郎,又不是女嬌娥”的堅持,師兄弟以及師傅這些外部環境的反饋在沖擊、鞭打、影響著程蝶衣對“鏡中”自身形象的整體形成。最后一片碎片的產生是在成角前夕:當小豆子逃出喜福成科班,引頸而望舞臺上絢麗華服、叱咤風云的霸王,小豆子對于成角的向往和獨立自主的意識堅定了回到科班的信念[4]。
至此,在一片片碎片的拼湊下,這些零散的感覺在鏡中強行形成了一個整體,但是這個整體并不是人的自然本體,而是在鏡中出現的整體,也就是在外部環境暗示以及影響下的自我形象的形成。“鏡子”以及“鏡子所形成的格式塔”在程蝶衣自我性別認同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且從蝶衣自身的本體之外發揮了自身并不能掌握的強大功能。正是這一差異,程蝶衣自身的性別認同和鏡子中形成的環境下的性別認同有著很大的距離,將程蝶衣原本脆弱的意識摧毀。但是,“鏡子”就是這樣映射出的碎片將程蝶衣本來的迷茫、意識上的零散組合成了“鏡中”的整體形象。在這一過程中,程蝶衣本身的自我男性性別的認同在鏡中之我的形象中被遮蔽了,因此程蝶衣也就會表現出自我與探索的迷茫感和無助感。作為人本來整體的替代物——整體性的鏡像出現了,就程蝶衣來說,這個整體形象的形成是在無盡的“暴力”和“暗示”下強行形成的。拉康將人的零散感到面對鏡像整體感的形成過程稱為一種類似于醫療外科式的整形(Orthopedics),從本質上講這個整體并不是本體,因此稱之為幻象(Fantasies)[1]。那么程蝶衣就是在無盡的暗示以及暴力下不合乎倫常的性別整體意識的形成,以及藝術追求的整體形象的形成。
1.2 認同“鏡中”的形象——小豆子性別的自我認同
其實根據零散感拼湊出的整體是社會環境下的幻象,并不是鏡外的本體。當程蝶衣觸摸鏡中的女性形象時,發現這一形象并不是真正存在的,并且本體對這個幻象是否認的,反而是因為映像的反射而存在的,因此程蝶衣也就形成了真實自我的性別認同與鏡中之我的性別認同的對立。這一對立的實質是鏡子得以存在,得以把人的形象轉化成鏡中的形象的一整套機制的對立[1]。程蝶衣在不斷擰巴的過程中用強大信念說服自己形成強大的自主意識,加之給予他最多愛護和照顧的師哥小石頭拿燒熱的煙袋鍋在小豆子嘴里一陣亂搞,強化了他作為主流意識形態下“對象”的特征,對自身強行獲得的認同感使得鏡中的整體形象與自我產生了同化效應。一方面,小豆子通過認同作為自己的客觀化的鏡像,也就是戲中的旦角形象,而獲得了主體意識。另一方面,“鏡像”中的女性性別認同是小豆子本身形象的異化,與主體本質有著相當大的距離和差異。但是,一旦小豆子認同了“鏡像”中形成的女性性別,本身的人的主體形象就會被鏡中所形成的形象同化。換言之,主體本就在鏡像中形成,形成之后又反過來作用于境外的本體[1]。也就是說,小豆子最終形象的形成是由于鏡中形象的反作用以及最終的自我認同。在這里,鏡外和鏡中自我產生了相互影響的辯證法,拉康稱之為“顛倒式對稱”的“格式塔方式”。正因為該階段的同化與異化,所以最終形成的主體是鏡像中的主體,因此主體是在“他者”與“自我”的相互糾纏、彼此辯證磨合過程中形成的產物[1]。
于是,在經歷了違背常理的自我形象的認定后,展現在鏡頭前的小豆子失魂地坐在太師椅上,儀態萬千地站起身來,行云流水般面帶微笑地唱“我們是女嬌娥,又不是男兒郎”。張公公府上發生的撲朔迷離的指向以及事情發生后小豆子不顧師傅和師兄的阻攔,撿回棄嬰的過程,已經表明了小豆子對“鏡中”強行形成的“女性身份”的心理性別產生了認同,男性身份徹底迷失,并且“鏡中”的女性心理性別的認同已經對“鏡外”的小豆子本體產生了同化現象[3]。這一新幻象的同化遮蔽了小豆子最初的性別認同,籠罩在他的自我性別認同上的是一層由強大信念支撐起的泡沫。這個信念產生自想要改變自己下三流的身份,產生于絢麗舞臺上成角的追求,因此這種信念可以強大到把女性的性別認同刻到骨子里,強大到作為一個旦角在舞臺上唱一輩子戲成為他畢生的信仰。
1.3 理想之我——程蝶衣的性別認同
在鏡外之我與鏡中之像的主體客體化,從主體到客體和從自我到同類的鏡像認同中,鏡像主體成為一種理想之我(Ideal I)。我(I),是主語,“我”也就是在一種關系中的主語,那么轉換角度,從關系一面來看境外之我和鏡中之我,“我”又成了賓語(Me),因此,理想之我同時也是一種被理想所關聯的我(Ideal Me)[1]。
霸王別姬這個故事講了唱戲和做人的道理:“既然老天不成全,那人就得自個兒成全自個兒”。在程蝶衣“人戲不分”的自我形象構建以及認同中,師兄段小樓就是楚霸王,而他程蝶衣就是虞姬。在舞臺上角兒們絢麗多彩、“雌雄不分”,在臺下扮演虞姬、楊貴妃時,又整天面對鏡子中帶著幾分嫵媚、幾分俏麗的女性裝扮,程蝶衣始終在自我本身的認同與鏡像的同化中游蕩,在虛幻中加強了對女性身份的自我認知,達到了“不瘋魔不成活”的境地[5]。“虞姬”的形象得到了社會的認同,程蝶衣在“幻象”的層面上對自身的鏡像認同,并且將鏡像內的虞姬幻化成了一個理想的自我,進而形成付諸行動的癡迷地追求。
在舞臺上數十年的旦角表演,傳遞著女性的柔軟與悲情;臺下為師哥勾臉描眉,沉浸在戲中與楚霸王的溫情;同時上演著與秋菊爭奪段小樓的激烈片段[6]……影片中虞姬裝扮的程蝶衣多次出現在化妝鏡中,導演巧妙地利用“鏡子”這個京劇演員必備的道具,將“虞姬”的鏡像同化為真正的“程蝶衣”[5]。因此,蝶衣一遍又一遍不自覺地在現實生活中模仿、表演出女性的性別特征,一遍遍強化鏡中之我對于本體的同化過程。這種同化不僅只是外在行為的表現,更是一種心理的深度暗示以及自我認定的行為方式。對于楚霸王段小樓來說,程蝶衣構建出的女性形象更加符合社會對于女性形象的認同:美麗柔弱、從一而終。程蝶衣的“癡”,段小樓的“迷”,使得段小樓對程蝶衣的感情藕斷絲連,曖昧不清。因此,在楚霸王與虞姬的幻象中,在程蝶衣與段小樓的幻象中,在兩層幻象的疊加下,程蝶衣徹底迷失了自己對于自我男性性別的認同,與此同時成功構建成女性角色與女性身份。
2 破鏡而出的不知所措
2.1 性別指認紊亂——菊仙的出現
只有在舞臺上,程蝶衣才能在虞姬與楚霸王的想象中,實現完整女性身份的認證。因此,程蝶衣對于“霸王別姬”有著不可言說的狂熱的追求,希望從一而終地與師哥唱一輩子戲。但是菊仙的出現打破了這個幻想,同時也使得程蝶衣的“鏡子”出現了裂痕。舞臺上“虞姬”的“楚霸王”突然變成了生活中“菊仙”的“段小樓”,程蝶衣女性身份的構建與同化失去了可以依靠的支柱。自我對于女性性別的深深認同使他拒絕,也使他忘記了回到男性認同的世界,他央求師哥“唱一輩子戲,差一年、一個月、一天、一個時辰都不是一輩子”,也就是在試圖挽救鏡像中構建的女性身份。但是,“假霸王”和“真虞姬”無法在現實生活中實現,因此沒有了“霸王”的程蝶衣陷入了茫然和不知所措。
2.2 重新審視——歷史的潮流
從清末的張公公,到民國的袁四爺,再到進入內戰混亂時期的國民黨高管,程蝶衣、段小樓和菊仙隨著潮流浮浮沉沉。“文革”時期剝奪了他存放幻象的舞臺和“虞姬”的服飾,甚至是“虞姬”的身份中斷了他的京劇生涯。太廟的批斗、段小樓的背叛、菊仙的上吊,加之之前袁四爺的審判,使得程蝶衣重新開始審視自我,陷入混淆不清無盡牽扯當中。
2.3 破鏡而出——走向無我的境界
10多年后,昔日“霸王”與“虞姬”著戲服重登舞臺,歷史與現實疊加。當段小樓回憶起兒時的“思凡”唱到“我本是男兒郎,又不是女嬌娥”,程蝶衣恍然大悟,他的男性身份得到了回歸,本就不是女嬌娥,這半生的執念、癡念只不過是鏡花水月,一場虛空。竟不知這從一而終的堅持是為了什么,一聲癡笑過后,劍起人落。
鏡像身份的構建隨著程蝶衣的自刎結束了。段小樓撕心裂肺地喊了聲“蝶衣”后,又平靜地像是遇見一位久未謀面的老熟人一樣叫了聲“小豆子”。“虞姬”之死,完結了半生的身份確認;程蝶衣之死,實現了女性性別認同的終結,同時實現了小豆子的“涅槃重生”,悲劇結束。正如拉康所說:“現實世界產生愿望客體。在這個客體作為一個現實因素尚不能接近以前,就已經存在對它的需要了;當這種需要得到滿足時,愿望也就消失了,生命本身也和它一起消失了。”[7]
“鏡像永恒存在,因為鏡像是自我構建和自我感知的基礎。但正是由于鏡像的永恒性,一旦自我存在失去了意義,那么生命也就沒有了意義。有即是無,無即是有,打破了鏡像也就沒有了存在。如果不能從意識形態上消除對自我的羈絆,達到‘本來無一物的境界,就只有從物質形態上消除自我的存在,達到‘無我的境界,為生命畫上句號。”[7]
參考文獻:
[1] 王平原.拉康“鏡像階段”理論探析[J].德州學院學報,2017,33(05):29-32.
[2] 劉文.拉康的鏡像理論與自我的建構[J].學術交流,2006(07):24-27.
[3] 呂娟娟.從《霸王別姬》看程蝶衣藝術形象分析[J].電影評介,2015(17):72-74.
[4] 張睿潔.試論電影《霸王別姬》中程蝶衣的身份認同與主體欲望[J].視聽,2020(04):73-74.
[5] 黎子微.從鏡像認同看程蝶衣一生的夢魘[J].電影文學,2012(12):98-99.
[6] 郭培筠.暴力·迷戀·背叛——影片《霸王別姬》的文化內蘊闡釋[J].內蒙古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02):76-80.
[7] 賀志濤,任永進.鏡像即存在——從《霸王別姬》程蝶衣之死看身份確認[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7(S1):277+290.
作者簡介:王齊(1999—),女,山東日照人,南京林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金融工程專業本科在讀,研究方向:金融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