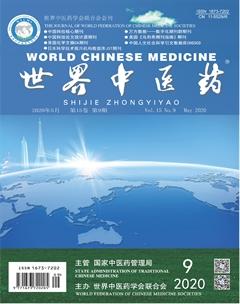朱克儉教授辨治肝癌經驗探析
胡琦 朱定耀 黃上
摘要 從對朱克儉教授肝癌學術思想的剖析、臨證經驗的總結及典型病案分析3個方面梳理朱教授治療肝癌的經驗特色。總結朱教授治療肝癌立足于濕熱瘀毒結聚、肝脾氣血兩傷的關鍵病機,治療以解毒抗癌、消瘀散結、疏肝理脾為大法,以資臨床借鑒。
關鍵詞 肝癌;中醫藥;名醫經驗;朱克儉;解毒抗癌;病機;臨證經驗;學術思想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Professor ZHU Kejian′s experience in treating liver cancer from 3 aspects:the analysis of the academic thoughts of liver cancer, the summary of clinical experience and the analysis of typical medical records.It is concluded that Professor ZHU Kejian′s treatment of liver cancer is based on the accumulation of damp,heat, toxin, and the injury of liver, spleen, qi and blood.The treatment is the method of detoxifying and anticancer, dispersing the stagnated liver-energy and regulating spleen, which can be used for clinical references.
Keywords Liver cance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amous doctor experience; ZHU Kejian; Detoxification and anticancer; Pathogenesis; Clinical experience; Academic thought
有“癌中之王”之稱的肝癌位居我國十大惡性腫瘤之列,嚴重威脅人類生命健康。肝癌起病隱匿,病情進展迅速,死亡率極高,自然生存期短[1]。近年來研究[2-4]顯示中醫藥防治肝癌已成為肝癌綜合治療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朱克儉教授為著名中醫學家歐陽锜及湖湘歐陽氏雜病流派傳承人,湖南省首批跨世紀中醫學科學術與技術帶頭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在其30余年的臨床工作中累積了豐富經驗,擅長運用中醫藥和中西醫結合方法診治肝癌。我有幸跟隨朱克儉老師學習,受益匪淺,茲將其治療肝癌經驗特色總結于下。
1 學術思想
1.1 病因病機 在中醫學文獻中,雖無肝癌的病名,但根據其主要癥狀和體征,屬中醫“肝積”“臌脹”“癖黃”“肝壅”“癥瘕”“黃疸”等范疇。據《醫宗必讀·積聚》指出“積之成也,正氣不足,而后邪氣踞之”,說明正氣虛弱,邪氣乘襲,蘊結于肝,形成痞塊,乃致肝癌;《血證論》日:“瘀血在經絡臟腑之間則結為癥瘕”;《諸病源候論·積聚病諸候》曰:“人之積聚癥瘕,皆由飲食不節,臟腑虛弱而生,久則成形”;《圣濟總錄》曰:“積氣在腹中……牢固推之不移者,癥也……”;《靈樞·百病始生》言:“若內傷于憂怒則氣上逆,氣上逆則六輸不通,凝血蘊裹而不散,津液澀滲,著而不去,則積皆成矣”。就其發生發展的原因,歸結為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內因即是臟腑氣血虛損,加之七情內傷,情志抑郁;脾虛濕聚,痰濕凝結;外因則為外感六淫乘虛入侵體內,邪凝毒結,使氣、血、濕、熱、瘀、毒互結,蘊結于肝,漸成癥積。
朱老師在傳承湖湘歐陽氏雜病流派學術經驗基礎上,經過30余年自身臨床反復實踐、思考和總結,認為肝癌的發生、發展和轉移的主要病因病機為疫毒感染,遷延失治,嗜食醇酒厚味內生濕熱蘊毒等,以致癌毒久羈,損及肝脾,濕熱瘀毒結聚,氣血漸傷,瘀毒流注,其關鍵為濕熱瘀毒結聚,肝脾氣血兩傷。
2.2 治療原則 中醫對肝癌治療的認識歷史悠久,經各代醫家的不斷完善豐富,傳承留下了寶貴的經驗總結。如《黃帝內經》《圣濟總錄》《張氏醫通》《金匱要略》等,在黃疸、膨脹、癥瘕、積聚等篇中,都對肝癌癥狀、病理和處理措施做了詳細的總結;金代張子和指出“積聚陳荃于中,留結寒熱于內,必用下之”;《圣濟總錄》云:“癥瘕癖積者……使氣血流通,則病可愈”;《醫學正傳》曰:“大凡腹中有塊,不問瘕瘕積聚,俱為惡候”。近年來肝癌的治療,臨床多采用辨證分型治療法則,常見的有扶正攻毒、滋陰養血、清熱解毒、健脾理氣、活血祛瘀等[5-10];臨床也可見健脾、清熱、祛瘀數法并用辨證施治者[11]。
朱老師認為,癌毒與濕熱瘀結是肝癌發生、發展以及復發轉移的關鍵病機,治療過程中應始終以解毒抗癌、消瘀散結為立法組方之重點。而“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以及肝之疏泄、脾之健運又是保持氣血運行流暢,瘀毒可否羈留的重要環節,疏肝理脾之擇藥用方亦不可忽略。
2 臨證經驗
朱老師結合肝癌發現晚、發展快、治療難、預后差的特點,認為治療上應采取綜合治療,選擇最適合患者之法。如早期有手術指征者可行手術切除;轉移擴散無法手術但正氣尚存者,可行介入、放療等控制局部腫瘤。但無論何種治療,中醫辨證論治應始終貫穿其中。
2.1 專病專方,辨病、辨證與辨證相結合 朱老師對于肝癌的治療注重辨病、辨證與辨證3者的結合。辨病治療,即探究疾病的本質并施行針對性治療。如同是抗腫瘤,針對肝癌,多用鱉甲、半邊蓮、臭牡丹、龍葵等藥;肺癌多用魚腥草、桔梗、仙鶴草等藥;腸癌則多用藤梨根、敗醬草、白花蛇舌草等藥。辨證治療即通過分析、綜合,明確疾病發展過程中某一階段,包括疾病部位、原因、性質,揭示疾病的本質,再確定相應的治法,最終延緩、控制、治愈疾病。如肝癌術后元氣損傷,氣血陰陽俱虛,證屬氣陰虧損為主者,應以益氣養陰、調補臟腑為主。對癥治療即采取有效手段,緩解患者目前最感痛苦或者可能危及患者生命的突出癥狀。如通過中醫藥緩解肝癌晚期或者術后出現的黃疸、腹水、疼痛、睡眠等全身癥狀。朱老師強調要根據疾病發生發展的不同階段和患者的實際情況合理選擇,以解毒抗癌為主,結合辨證論治;或辨證論治為主,結合解毒抗癌;或對癥為主,及時緩解患者心理恐懼或者生理痛苦。故明白病、證、癥之間的內在聯系,做到辨病、辨證與辨證相結合,才能有效提高治療肝癌的療效。
2.2 臨床運用 目前,肝癌尚沒有統一的辨證分型標準,朱老師根據多年臨床經驗,查閱大量文獻記載,總結出瘀毒互結為肝癌的主要證型。綜觀朱老師治療肝癌的遣方用藥,發現其多從疏肝柔肝、化瘀解毒、消瘤散結3個層次著手,再隨癥加減,自擬解毒消癌方用于肝癌防治。解毒消癌方藥物基本組成:柴胡12 g、郁金12 g、白芍15 g、女貞子15 g、黃芪30 g、白術12 g、薏苡仁20 g、半邊蓮15 g、鱉甲15 g、臭牡丹20 g、龍葵15 g、浙貝母12 g、夏枯草15 g、石見穿15 g、陳皮12 g、甘草5 g。方中柴胡、郁金、白芍、女貞子、黃芪、白術等藥益氣養陰、行氣解郁、疏肝柔肝;薏苡仁、半邊蓮、鱉甲、臭牡丹、龍葵等均具解毒抗癌之療效;浙貝母、夏枯草、石見穿等藥消瘤散結作用明顯;陳皮、甘草同用,則起和胃護胃、調和諸藥之效。
隨癥加減:痛甚者加絲瓜絡、延胡索、蒲黃;肝郁甚者重用白芍、郁金;失眠、夜寐不安者加夜交藤、合歡皮養血安神;食欲不振者加雞內金、山楂;皮膚瘙癢者加地膚子、白鮮皮;預防骨轉移者加蜈蚣、全蝎;腹水甚者加大腹皮、茯苓;大便稀溏者改白術為炒白術等。
2.3 注意事項
朱老師在多年臨證過程中發現堅持服用中藥3至5年的肝癌患者,不僅可以幫助機體調節陰陽平衡,有效改善黃疸、腹水、疼痛、睡眠等全身癥狀,使患者生命質量提高,生存期明顯延長,而且還能在一定程度上預防復發和轉移。臨證過程中應注意以下事項。
2.3.1 祛邪與扶正相結合 惡性腫瘤的病因病機有本虛標實和本實標虛兩類截然相反的認識[12],朱老師傾向于后者。在肝癌的治療過程中將祛邪與扶正相結合,以解毒抗癌、消瘀散結、調補臟腑為總原則。在堅持總體原則的情況下,依據疾病所處的不同時期、階段,側重點也不一樣。如術后階段,正氣受損,氣血津液耗傷,故治療應以扶正為主,補益氣血,清解余毒;又如介入或其他治療階段,患者常出現口干口苦、食欲不振、惡心嘔吐、大便不調、皮膚瘙癢、失眠、脫發等多種不適反應,在此階段,應堅持扶正祛邪兼顧對癥施治,以提高患者生命質量為治療目的。再者,若處于病情穩定無特殊不適的階段,則以解毒抗癌為主,可適當增加消瘤散結藥物的數量和用量,同時兼以扶正。
2.3.2 慎用活血化瘀藥 中醫學認為,肝癌是因痰瘀、寒滯、瘤毒積滯于人體組織內的腫塊,故治療可選用活血化瘀藥,以行活血化瘀、行氣補血、攻毒散結、活血止痛之效。縱觀以往科學研究[13-14],活血化瘀藥具有抗腫瘤及其復發轉移的作用。但20世紀80年代初,李學湯等[15]首次報道了與之截然相反的結論,即丹參、赤芍、紅花等可以促進惡性腫瘤的轉移。基于活血化瘀藥對腫瘤轉移的雙重作用和多年的臨證經驗,朱老師認為肝癌是具有出血傾向的腫瘤,且原發腫瘤的部位在腹腔,故應慎用該類藥以免促進其復發和轉移。
2.3.3 注重預防與調護 肝癌最大的特點是發展快、治療難和極易復發轉移,《黃帝內經》曰:“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也說明治未病的重要性。朱老師認為,可從“未病先防”“已病早治”和“病重防變”3個方面著手防治肝癌。“未病先防”的關鍵在于學習和踐行中醫傳統和現代養生理念,保持良好的心理和生理健康狀態,從根本上防治肝癌的發生,其中最重要的是“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勞作”以及“恬淡虛無,精神內守”;“已病早治”是中醫藥介入癌前病變的治療,如慢性乙肝合并肝硬化的患者,可盡早服用中藥,防止疾病發展到肝癌的階段;“病重防變”既包括早中期術后患者采用中醫藥病證結合治療預防復發和轉移,也包括中晚期患者采用中醫藥辨證治療改善生命質量和延長生存期等。
3 病案舉隅
某,男,56歲,2016年7月8日初診。患者于2016年6月因腹部疼痛于當地醫院就診,診斷為原發性肝癌,拒行手術和其他治療。既往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病史。就診時訴腹部疼痛脹滿,稍食即吐,全身乏力,夜寐不安,納差,舌暗淡,苔白厚,脈沉弦。辨證為肝郁脾虛、瘀毒互結證。治宜疏肝柔肝、化瘀解毒、消瘤散結。處方:柴胡12 g、郁金12 g、白芍15 g、女貞子15 g、黃芪30 g、白術12 g、薏苡仁20 g、靈芝10 g、半邊蓮15 g、鱉甲15 g、臭牡丹20 g、龍葵15 g、浙貝母12 g、夏枯草15 g、石見穿15 g、陳皮12 g、甘草5 g。14劑,水煎服,每日1劑,分2次服。同時服用院內自制中成藥肝喜片(湖南中醫藥大學附屬中西醫結合醫院院內制劑,批號: 湘藥制字Z20080761),10片/次, 口服,3次/d。肝喜片的藥物組成主要為:明黨參10 g、黃茂20 g、白術10 g、茯苓10 g、柴胡10 g、香附10 g、蚤休9 g、陳皮10 g、醋鱉甲(先煎)15 g、桃仁10 g、丹參15 g、生牡礪( 先煎)30 g、半枝蓮30 g、白花蛇舌草30 g、甘草5 g。2016年7月12日復診,患者自覺乏力減輕,腹脹等癥狀明顯改善,舌紅,苔白,脈沉弦。守原方,去靈芝,黃芪減為20 g,加山慈菇15 g、白花蛇舌草15 g、夜交藤15 g、合歡皮15 g。21劑,水煎服,每日1劑,分2次服。此后患者堅持門診復診用藥,未行特殊西醫治療,至今病情穩定,生活正常(注:服藥時間是自2016年7月8日初診至撰寫此文時)。
按語:患者原發性肝癌,晚期肝硬化且常年乙肝病史,素體虛弱加之癌毒侵犯,瘀毒互結,故首診治以疏肝柔肝、化瘀解毒、消瘤散結。方中柴胡、郁金、白芍、女貞子、黃芪、白術、靈芝等藥益氣養陰、行氣解郁、疏肝柔肝;薏苡仁、半邊蓮、鱉甲、臭牡丹、龍葵等均具解毒抗癌之療效;浙貝母、夏枯草、石見穿等消瘤散結作用明顯。陳皮、甘草同用,起和胃護胃、調和諸藥之效。全方扶正與祛邪并用,方投14劑,患者癥狀減輕,原方治療有效,故二診仍用此方,考慮患者精神好轉,正氣較之前恢復,故減少益氣養陰藥味,加山慈菇、白花蛇舌草等加強化瘀解毒、消瘤散結之功效。另加夜交藤、合歡皮等改善睡眠質量。
參考文獻
[1]林麗珠,肖志偉,黃學武,等.原發性肝癌中西醫結合診療實踐回眸[J].中醫腫瘤學雜志,2020,2(1):5-9.
[2]吳萬垠.腫瘤靶向藥物治療時代中醫藥定位與發展[J].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2018,38(8):908-910.
[3]徐菲,曾楊麗,李娟,等.中藥復方防治肝癌作用機制研究進展[J].中國實驗方劑學雜志,2019,25(24):196-204.
[4]魏亞威,葉之華,高翔,等.肝癌中醫藥防治三級監測平臺的設計與實現[J].中國衛生信息管理雜志,2019,16(1):60-63.
[5]劉蓮,張紅霞,崔書彥,等.原發性肝癌中醫辨證與外周血免疫抑制細胞表達異常關系[J].中醫學報,2019,34(10):2236-2240.
[6]周小舟,馮文杏,孫新鋒,等.原發性肝癌中醫宏觀辨證傳承及微觀辨證學創新與發展[J].湖南中醫藥大學學報,2018,38(8):845-848.
[7]李冉,袁成民.原發性肝癌中醫研究進展[J].山東中醫藥大學學報,2018,42(3):276-279.
[8]劉建麗,李藝,王亮開,等.105例原發性肝癌患者中醫證候分布規律研究[J].新中醫,2019,51(6):23-25.
[9]周順.原發性肝癌中醫辨證分型與臨床指標的相關性研究[D].石家莊:河北中醫學院,2019.
[10]呂樹垚,王立森.原發性肝癌的中醫診療[J].世界最新醫學信息文摘,2019,19(16):225-226.
[11]杜小艷.潘敏求治療原發性肝癌經驗[J].湖南中醫雜志,2014,30(11):23-25.
[12]池志恒.中醫對惡性腫瘤病因病機認識的歷史演進[D].南京:南京中醫藥大學,2018.
[13]方漢欽,魏開建.魏開建對腫瘤血瘀證的認識及治療經驗[J].中醫藥臨床雜志,2018,30(2):247-249.
[14]羅琴琴,魯葉云,王立芳,等.基于血瘀證探討活血化瘀法在惡性腫瘤治療中的應用[J].中醫雜志,2017,58(8):654-656.
[15]李學湯,王永泉,傅乃武.幾種活血化瘀藥物對小鼠肝癌細胞形成肺轉移影響的初步實驗觀察[J].中醫雜志,1980,21(8):75-77.
(2019-04-25收稿 責任編輯:芮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