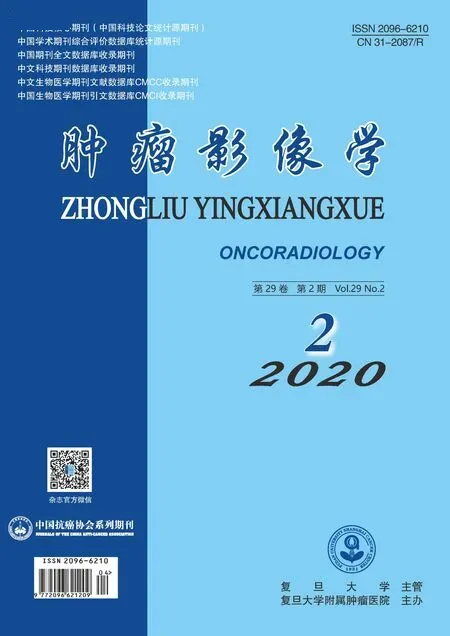動態增強磁共振成像定量參數早期預測局部進展期乳腺癌新輔助化療效果的價值
孫海馨,張仁知,周純武,蔣 濤
1.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朝陽醫院放射科,北京 100020;
2. 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醫學影像科,北京 100021
局部進展期乳腺癌(locally advanced breast cancer,LABC)包含Ⅲ期患者,原發腫瘤T0-3期,同側鎖骨上、下區或內乳淋巴結轉移(N2或N3),腫瘤侵犯胸壁或皮膚(T4期),無論淋巴結有無轉移。在某些情況下,LABC的定義擴大到臨床ⅡB期,如原發性腫瘤≥5 cm而無淋巴結轉移(T3N0期)[1]。新輔助化療(neoadjuvant chemotherapy,NAC)是LABC的標準治療方式,不僅可以縮小腫瘤體積、降低臨床分期、增加手術機會、提高保乳率,而且可以抑制微轉移灶、評估化療效果、了解耐藥情況。以蒽環類和紫杉類藥物為基礎的方案是LABC的主要NAC方案,以蒽環類藥物為基礎的方案加入紫杉類藥物能提高病理學完全緩解(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pCR)率和保乳率,并延長患者的生存時間[1]。研究表明,約80%的患者可以通過NAC達到臨床緩解,30%的患者可以達到臨床完全緩解,13%的患者可以達到pCR,但仍有部分患者既不能達到臨床完全緩解也不能達到pCR[2]。因此,早期檢測NAC療效對于明確治療方案非常重要。
定量動態增強磁共振成像(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DCEMRI)通過藥代動力學模型,計算出容量轉移常數(Ktrans)、速率常數(Kep)和血管外細胞外間隙容積比(Ve)這3個參數,可以反映腫瘤血流灌注、微血管滲透性等血流動力學信息,對于病變定性診斷及NAC療效評估具有更大價值。既往研究基本認為化療2個周期后的DCE-MRI定量參數能夠預測療效[3-7],而化療1個周期后DCEMRI定量參數對于療效預測結果并不一致[8-10]。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究DCE-MRI定量參數在NAC的1個周期后預測LABC化療效果方面的價值。
1 資料和方法
1.1 臨床資料
入組標準:① 病理學活組織檢查證實為乳腺癌;② 首次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檢查前未進行過乳腺癌手術及系統性化療的患者;③ 進行規范性乳腺癌NAC;④ 化療前1個月內及化療1個周期后(通常為2周或3周后)均進行乳腺DCE-MRI檢查。排除標準:① 圖像偽影太重,影響評估;② 僅進行1次乳腺DCE-MRI檢查;③ 化療結束后未進行手術治療,沒有取得術后病理學檢查結果。最終納入患者共28例。
1.2 檢查方法
MRI掃描采用美國GE公司的Discovery MR750 3.0T超導磁共振設備,使用8通道乳腺專用相控陣線圈作為接收線圈。掃描時患者采用俯臥位,雙側乳腺自然懸垂于乳腺線圈內。
在定位掃描后,分別行脂肪抑制T2WI、單b值擴散加權成像(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DWI)及DCE-MRI掃描,以上序列均采用橫軸位掃描,最后行延遲矢狀位增強掃描。DCE-MRI掃描采用Vibrant技術行橫軸位掃描,共掃描39期(1期增強前蒙片和38期增強掃描),掃描參數:重復時間(repetition time,TR)/回波時間(echo time,TE)為3.8/2.1 ms,翻轉角9o,視野( field of view,FOV)為32 cm×32 cm,矩陣為256×256,激發次數(number of excitation,NEX)為1,層厚4 mm,無間隔掃描,每期掃描時間為10 s。增強掃描對比劑使用釓噴替酸葡甲胺(Gd-DTPA),劑量為0.1 mmol/kg,經肘靜脈以2.0 mL/s的速度團注,之后注射20 mL 0.9%的NaCl溶液沖管。囑患者檢查前6 h空腹,檢查過程中禁止運動或咳嗽。
1.3 圖像分析
所有數據均使用GenIQ軟件及GE AW4.6工作站3D Synchro View軟件進行分析。由兩位診斷經驗豐富的醫師繪制感興趣區(region of interest,ROI),ROI均放置在病灶的最大層面,盡量避開明顯的壞死、出血和囊變區。在動態增強早期病變強化較顯著時手動勾畫ROI,測量DCE-MRI相關定量參數,包括Ktrans、Kep和Ve,重復測量3次取其平均值并記錄。
1.4 病理學檢查
由具有10年以上工作經驗的病理科醫師,在不知患者信息的情況下,采用盲法對組織標本切片進行閱片,NAC后的病理學評價采用Miller&Payne分級系統[11],具體標準如下:1級,腫瘤細胞數量無變化;2級,腫瘤細胞減少比例≤30%;3級,腫瘤細胞明顯減少,比例介于30%~90%;4級,腫瘤細胞減少比例≥90%,僅少數殘余的癌細胞散在分布;5級,所有切片均無浸潤癌殘存,可見殘存的導管原位癌(ductal carcinoma in situ,DCIS)。將1~3級歸為組織學非顯著反應組(non-major histological response,NMHR),4和5級歸為組織學顯著反應組(major histological response,MHR)。
1.5 統計學處理
使用SPSS 22.0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學分析。采用Wilcoxon signed-ranks檢驗比較化療前后DCE-MRI定量參數的差異。采用Mann-Whitney U檢驗及獨立樣本t檢驗來比較組織學顯著反應組和組織學非顯著反應組組間化療前及化療1個周期后DCE-MRI定量參數的差異。利用MedCalc軟件進行受試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線的繪制,利用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curve,AUC)來判斷不同參數預測化療療效的準確性(AUC=0.5,無診斷準確性;0.5<AUC≤0.7,較差的診斷準確性;0.7<AUC≤0.9,中等程度的診斷準確性;AUC>0.9,優秀的診斷準確性)。根據Youden指數確定各參數的最佳診斷閾值,并計算相應的診斷靈敏度、特異度。
2 結 果
2.1 患者的基本情況
40例接受NAC的乳腺癌患者完成了治療前和(或)治療中的MRI檢查。其中,12例患者因不滿足入組條件被排除(3例患者圖像偽影較重,影響分析;5例患者未進行化療1個周期后乳腺MRI檢查;2例患者未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朝陽醫院進行手術治療,具體術后病理學檢查結果不詳;2例患者治療過程中出現遠處轉移,最終失去手術機會)。最終入組患者28例,同時完成了化療前和化療1個周期后的乳腺MRI檢查,化療結束后在進行手術治療。患者的基本情況見表1。

表1 患者的基本情況
2.2 NAC前后DCE-MRI定量參數變化
NAC前后DCE-MRI定量參數比較見表2,化療前Ktrans值為0.28/min,化療1個周期后為(0.21±0.12)/min,化療前Kep值為0.79/min,化療1個周期后為(0.56±0.22)/min,化療1個周期后Ktrans、Kep均較化療前下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均<0.05),提示NAC前后病灶血流灌注狀態變化顯著。Ve值化療前后大致相仿,差異不明顯。
2.3 NAC前及化療1個周期DCE-MRI定量參數組間比較
MHR組與NMHR組組間NAC前及化療1個周期后DCE-MRI定量參數比較見表3及圖1~2。NAC前MHR組Ktrans值、Kep值、Ve值均比MHR組參數值要高,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化療1個周期后MHR組Ktrans值為(0.14±0.04)/min,NMHR組Ktrans值為(0.24±0.13)/min,兩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35),而Kep、Ve值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表2 NAC前后DCE-MRI定量參數比較

表3 MHR組與NMHR組間NAC前及化療1個周期后DCE-MRI定量參數比較

圖1 MHR組NAC前后DCE-MRI定量參數圖
2.4 化療前DCE-MRI定量參數預測療效效能
化療前DCE-MRI定量參數預測NAC療效的預測效能參見表4及圖3。結果表明,NAC前DCE-MRI定量參數的預測效能均較差,其中以Ve值預測效能最大(AUC=0.716),閾值為0.344,靈敏度為66.67%,特異度為78.95%。

圖2 NMHR組NAC前后定量DCE-MRI參數圖

表4 化療前DCE-MRI定量參數預測NAC療效的預測效能

圖3 NAC前DCE-MRI定量參數預測組織學顯著反應的ROC曲線
2.5 化療1個周期后DCE-MRI定量參數預測療效效能
化療1個周期后D C E-M R I定量參數預測N A C療效的效能見表5及圖4,顯示Ktrans、Kep預測效能均較N A C前提高,以Ktrans預測效能最好(AUC=0.749),閾值為0.202/min,靈敏度為100.00%,特異度為63.16%。Kep及Ve值的預測效能較低,AUC分別為0.667、0.632。

表5 化療1個周期后DCE-MRI定量參數預測NAC療效的預測效能

圖4 NAC 1個周期后DCE-MRI定量參數預測組織學顯著反應的ROC曲線
3 討 論
DCE-MRI定量參數包括:Ktrans,反映局部血容量、血流量和血管通透性;Kep,反映局部血流量和血管通透性;Ve,與細胞密度和微血管密度相關[12]。有報道認為Ktrans、Ve與微血管密度密切相關[13]。本研究中化療1個周期后Ktrans、Kep較化療前明顯降低,主要與化療過程中血管密度和功能變化有關。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在乳腺癌組織中是一種促進腫瘤血管新生和組織通透性的強效刺激物[14],是維持血管微環境和高比例新生血管所必需的。腫瘤組織內部有大量新生血管,這種血管并不成熟,缺乏內皮細胞或者平滑肌細胞,因此血管通透性較高。Wang等[15]認為,血清VEGF能夠區分三陰性乳腺癌的pCR組與非pCR組,pCR組化療后VEGF明顯下降,而非pCR組化療后VEGF水平變化不大。化療過程中,腫瘤細胞壞死導致組織內VEGF因子產量減低,因而不成熟血管內皮細胞凋亡,新生血管減少,因此化療后Ktrans、Kep減低。
既往研究多認為化療2個周期后的DCE-MRI定量參數或其變化值能夠預測化療效果,而對于化療1個周期后DCE-MRI定量參數的預測效能觀點則不盡相同[3-7]。Padhani等[8]認為化療2個周期后的Ktrans的變化值可以預測療效,而化療1個周期后DCE-MRI定量參數均不能預測療效。Cho等[10]也認為化療1個周期后DCE-MRI定量參數均不能預測療效。Li等[9]分析了28例患者化療1個周期后的Kep值能夠區分pCR組和非pCR組。Li等[16]也得到相似結論,化療1個周期后Kep值的預測效能最高。本研究認為,化療1個周期后的Ktrans值在組織學顯著反應組和組織學非顯著反應組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ROC曲線顯示預測療效的AUC為0.749,能夠早期預測療效。但Kep值、Ve值預測療效的能力不佳。目前各個研究結果并不一致,分析原因可能是掃描機器不同、掃描序列設置的時間分辨率及期別不同、化療方案不一致、實驗分組標準不一致等所致。筆者認為隨著MRI新技術的發展和成熟,化療1個周期后的DCE-MRI定量參數的預測價值會逐步提高,為臨床應用帶來更大幫助。
本研究探討了化療1個周期后的DCE-MRI定量參數早期預測乳腺癌化療效果的價值,研究發現Ktrans值預測效能最高,是最佳指標,Kep值、Ve值具有補充價值。本研究的創新之處:① 乳腺癌NAC療效評估時間點提前為1個周期后;② 本研究為前瞻性收集患者,MRI掃描采用3.0T超導設備,均在同一機器,掃描序列和各項掃描參數一致性很高,共掃描39期,無間隔掃描,每期10 s,得到的DCE-MRI定量參數可信度較高。但本次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樣本量較少,得到的閾值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次,部分患者為非腫塊樣病變,在軸位多期動態增強圖像勾畫ROI有一定難度,但我們勾畫ROI遵循病變最大截面、避開囊變壞死區的規則;最后,樣本中pCR患者較少,可能對組間差異分析有一定影響。后續應進一步擴大樣本量,使得此次探究結果能夠得到進一步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