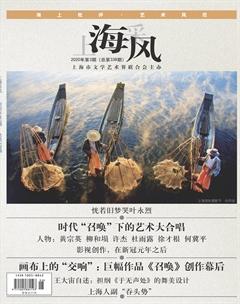“故事大王”續寫故事傳奇
馬信芳
今年年初,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牽動著幾億國人的心,也牽動著上海人的心。被國家文化部命名“全國故事之鄉”的上海浦東川沙鎮同被震動。為這場疫情防控的攻堅戰,很多醫院的醫護人員紛紛報名參加醫療隊支援武漢。天使逆行的英雄壯舉,深深激勵著老夏。夜深人靜,他輾轉不能入眠。一個歌頌白衣天使請纓去武漢的故事在他腦海里活了起來。他干脆起身,扭亮臺燈,拿出筆記本,寫了起來。他筆下的人物金慧英,上有老下有小,且她的女兒還未滿周歲。醫院領導就她實際情況,遲遲沒有批準她上武漢的請求。疫情是命令,防控是責任,救人成為第一等重要的事,金慧英鐵了心三次請纓上武漢。關鍵時刻,金慧英丈夫挺身而出,包攬后方一切事務,送自己媳婦上前線。夏友梅足足花了三個晚上,從構思到人物設計,到情節安排,新故事《倔姑娘三請纓》終于脫稿。
鎮上故事員儲鳳珍聞訊,馬上要走了故事稿,連夜講演排練并錄了音。第二天,又請人制作成視頻。
夏友梅發揮專長,盡綿薄之力的精神同樣鼓舞了川沙其他故事員,顧正權等作者紛紛行動起來。《病床前的團圓飯》《雪中送炭》《夜尋失蹤者》等一個個故事文本送到老夏的手中。夏友梅不顧休息,一一修改。兩天后,反映抗疫的七篇故事通過鎮上微信平臺,以文本、音頻和視頻形式向村民和小區居民傳送。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夏友梅正是借助故事這個平臺與百姓群眾連在了一起。
醉心于民間故事
上海是新故事的發源地和發祥地。故事作為百姓喜愛的文學和文藝樣式,新中國誕生以來獲得了飛躍發展,這是在群眾文化活動中廣大故事工作者努力的結果。上海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項目——川沙民間故事傳承人夏友梅就是其中一位。五十多年來,他在這塊樂土上辛勤耕耘,已搜集整理和發表故事作品三百余萬字。特別是退休后,更為培養故事接班人盡心竭力,數以千計的故事員脫穎而出。
夏友梅,出生于浦東一個貧困家庭,從小喜歡聽母親講故事。《牛郎織女》《孟姜女》《梁山伯與祝英臺》《白蛇傳》等,母親講得有聲有色,小友梅聽得津津有味,常常睡夢中笑出了聲。懷著對民間文學的癡情,當他在農村務農的時候,就不忘搜集整理流傳于民間的故事、諺語和歇后語。6000多則(條)的手抄記錄稿正是他青年時代的酷愛。
上天眷顧這位醉心于民間文學的青年,1979年,當夏友梅調入川沙縣文化館工作時,讓他擔任的是故事專職干部。真是如魚得水,他將寫故事、講故事、抓故事,三位集一體,在川沙這片熱土上,開始了他的故事生涯。就這樣,五十年如一日,他不僅將故事視為愛好,更將它當作事業。他從一般干部,直升至館長,從小故事員,成為故事大王。
1998年,夏友梅的母親身患絕癥。臨終前幾天,母親意味深長地對站在床前的兒子說:“友梅,今朝我可能要走了,你是故事大王,給娘講個故事,送送娘走好嗎?”夏友梅瞪大眼睛,看著娘,這是母親對他故事事業的極大鼓勵,言下之意,就是娘歸天也要以故事為伴。夏友梅熱淚盈眶,握著母親的手,“從前,有個孩子叫……”夏友梅慢慢講起了母親從小給自己講的《孝子》故事,講著講著,母親露出欣慰的笑容。面對彌留之際的母親,夏友梅知道,是娘、是家人、是同道們的支持,才有了今日的他。當晚,他下了決心,誓把故事當作自己的終身事業。
潛心于故事創作
夏友梅知道,要使故事成為老百姓喜歡的作品,創作是關鍵。他也知道,自己并非是天生的故事家,要想成功必須努力。他為自己立了座右銘:“笨鳥先飛,勤能補拙。”為寫好故事,他常常挑燈夜戰。稿紙寫了一疊又一疊,作品改了一稿又一稿。有時,睡夢中想到一個情節,他會半夜起床,開燈鋪紙揮筆,甚至寫到天亮。
故事來源于生活,故事又是民情和民風的寫照,及時和藝術地再現現實生活,是故事“輕騎”的特點。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的春風吹綠了浦東大地,川沙鎮上出現了首家個體戶水果店。借著印度電影《大篷車》的放映,一個名為“大篷車”的水果店應運而生。時任記者的我曾與青年報記者黃漢民同到川沙采訪,給我們帶路的夏友梅敏銳地感到這是故事創作的新題材。翌日,他馬上展開更深入的調查,在積累了大量素材后,運用中國民間故事“三疊式”的結構,寫成了《“大篷車”招親》。這個開先河的作品發表后,多家故事刊物引來了一系列反映改革開放的作品。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夏友梅的目光投向市場經濟的更深層面。他創作的故事《吳經理三戰“大篷車”》《戇阿福三鬧“大篷車”》,發表后社會反響更為強烈。跨入新世紀后,他緊隨時代的步伐,以更高的高度、更新的角度來反映生活。《女財神》《特效藥方》《被跟蹤的大夫》《飛來的人民幣》等故事以反腐倡廉、頌揚人民公仆、提倡社會正氣為主題,受到讀者的歡迎。故事活動家、評論家任嘉禾先生稱贊他的故事,是“浦東開發開放真實面貌的一面鏡子,一部運用文學筆觸,從普通老百姓的視角觀察的‘歷史,從而使廣大讀者分享浦東改革開放的偉大成果和學習浦東改革開放的創業精神。”
五十多年來,夏友梅堅持故事創作,先后在《新民晚報》《上海老年報》《東方城鄉報》《故事會》《上海故事》等報紙雜志上發表故事作品近百篇(則),結集出版了《夏友梅故事集》《夏友梅戲曲故事評論集》《夏友梅故事藝術集》。
精心于故事演講
故事貴在口口相傳,演講常常是好故事的第二創作,專家稱之為:“講講寫寫,寫寫講講”。
1983年,夏友梅參加《故事會》雜志舉辦的每月一次的故事講座,從郊區到市區乘車要一個多小時。整整一年,他風雨無阻,從不缺課。有一次刮十級臺風,他第一個走進課堂,雖渾身濕透,內心卻因為故事的神奇召喚而熱情洋溢,早已忘卻了風雨的侵襲。一年的學習,對夏友梅的故事創作和演講產生了重大影響,年終被《故事會》評為優秀學員。
夏友梅講故事,講究一個情字。一是動情,他感情充沛,善于刻畫人物,許多故事被他講得催人淚下。二是重情節,專家總結講故事的“新、奇、巧、趣、謎”等演講技巧,他應用之妙,存乎一心。他還從滬劇、越劇、評彈、浦東說書等藝術中擷取養料來豐富自己的表演。
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這是論戲。但老夏說,講故事也一樣,也得下苦功。有人說他,排演起來像真的一樣。一次,夏友梅關門練講《救火英雄》。他大聲呼叫“救火”,急切之聲溢于言表,屋外鄰居信以為真,紛紛攜盆帶桶把他家團團圍住。
夏友梅常將身邊熟悉的人與事創編成故事來講,《神奇姑娘“蒸活人”》《養子秘方》等,被他講得活靈活現。有聽眾竟與現實等同起來,把他當作是醫術高超的“神醫”,特邀他看病,車費食費住宿費實行三包。有個患有不育癥的婦女,為了她家庭的幸福,含淚懇求老夏獻出秘方。急得老夏連連聲明,這是文藝作品。
夏友梅曾在農村小學擔任過語文老師,有個勤學的學生讓他念念不忘,他以學生為原型創作新故事《作弊的三好學生》,懸念迭起,蘊含了深深的人間真情,在校園演講后引起強烈的反響。故事在《故事會》發表后,被評為全國優秀作品一等獎,并于1993年榮獲文化部群星獎“金獎”。
優秀的故事感染人,如花香引蝶。精彩的演講有聲有色,如磁鐵吸針。復旦大學、上海大學文學院、華東化工學院(現華東理工大學)等高校學院曾邀他講課。上海大學文學院、《上海故事》編輯部、上海市文化局等單位聯合舉辦“夏友梅故事藝術討論會”,對其作品和講演給予極高的評價。是故事給了群文工作的高地,是故事活動造就了故事大王的誕生。1991年,夏友梅被文化部評為全國文化系統先進工作者。1992年,他被授予上海市勞動模范的稱號。1993年,文化部人事司編著出版《文化群英錄——首批全國文化系統先進工作者小傳》一書,以“故事大王”為題介紹夏友梅,自此故事大王聲名鵲起。夏友梅還獲“開發浦東杰出人才貢獻獎”,上海民間文藝家協會與上海故事家協會等單位頒發的“改革開放40周年上海故事發展突出貢獻獎”。
用心于故事培育
2004年,夏友梅從川沙文化館館長崗位上退了下來。退休生活將如何安排?這時有人建議:老夏,退休了,你也可歇夏(趁夏日休息)了。夏友梅嫣然一笑:“大家稱我的故事是一碗‘炒青菜,一碗‘咸菜湯。油水不足但味道還可以,這正合老百姓的口味。我的故事還沒講完,焉能歇歇?”
一直癡迷于故事的夏友梅依然“蠢蠢欲動”,現在他有充足時間了,一個弘揚浦東特色文化、將故事做成品牌的想法在他的腦海里慢慢成形。
僅一年的籌備,在川沙新鎮政府與新區文廣局的支持下,“夏友梅故事藝術工作室”正式掛牌。這是他退休后開始的更有激情的“創業”,沒有人召喚,他卻以工作室為新的陣地。老伴衛鳳新說:“我家老夏沒退休,家仍然只是他的旅店。”
為故事費時費力,夏友梅決不吝嗇。民間文學要傳承,故事也要后繼有人。不久,“上海夏友梅故事藝術學校”宣告成立。以藝校為基地,他又創辦起“開心果故事團”,這是個旨在培養少兒學習講故事、寫故事的踐行計劃,“傳承紅色基因”巡回宣講、故事進校園等活動,深受歡迎。一分耕耘一分收獲,十多年的辛勤付出,藝校已先后培養小故事員3000余名,故事指導老師近百名。故事隊獲得了上海市故事創作演講比賽八連冠的優秀成績,而組織單位和老師更是獲得華東六省一市廉政故事大賽優秀組織獎、第九屆第十屆全國少兒故事大王邀請賽全國優秀組織獎的殊榮。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74歲的夏友梅仍不滿足,他立足川沙故事之鄉,放眼長三角地區,為川沙故事走出上海,走向全國繼續努力。一場又一場大規模、高級別的故事邀請賽在川沙舉行,外省市一個個故事在這里得到交流,而一本本精彩故事集——《花香彩蝶飛》《熱土報春花》《藝苑花枝俏》《花香飄萬里》《時代的浪花》等作品集已展翅舞動飛向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