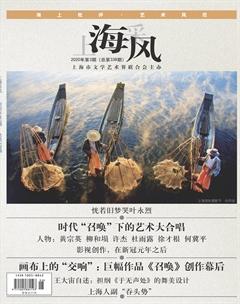畫家汪家芳:沉下心來繪制不負時代的精品力作
施平

2020年4月至5月,中華藝術宮的“召喚——上海市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美術、攝影主題展”上,有件寬5米、高3.2米的巨幅山水畫《巍巍中國情》,因其震撼力和感染力俱佳而特別醒目。創作者以洗練精致的筆墨,突顯疫情防控阻擊戰中滬鄂兩地緊密聯手,積極營造堅不可摧的精神力量,講好疫情防控中的中國故事。
畫作引起了許多觀賞者駐足,細瞧品評交流。站在觀賞者的角度,這幅作品以傳統山水畫固有筆墨技法,來演繹當代主題性創作,讓人們獲得跨越時空的感動,這樣的創作理念新意迭出,用藝術驅散陰霾,喚起對生命的敬畏,具有現實意義。
速寫特殊時期平民英雄,畫家應有主觀意識與行為擔當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后,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國家一級美術師、上海市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上海中國畫院畫師汪家芳,內心一直想著做些為社會提振正能量的事情。宅居畫室的日子,汪家芳的所有喜怒哀樂都隨武漢紀事而起伏。隨之而起的“靈魂拷問”在他心頭反復縈繞:作為手握畫筆的藝術家,能為當下的社會做點什么?如何體現社會責任與命運擔當?面對疫情,畫家既不能像臨床醫生那樣在第一線拯救病人,也沒有能力參與疫苗的創新研發,那就以自己的所長,開動腦筋,拓展思維,用熟悉的畫筆傾注胸中塊壘,謳歌那些值得濃墨重彩描繪的人與事物,銘記中華民族共擔風雨共沐陽光的大愛與大義。
農歷新年初二開始,汪家芳外出觀察街景,實地尋找創作素材。在地鐵站入口,他看到了工作人員為每一位乘客認真測量體溫的實況。在市井街坊,他看到街頭風雨無阻騎車送餐的外賣小哥。尤其是在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探訪門診與病區的身臨其境之后,他心頭很不平靜。他意識到,作為一名關注社會、有責任心的畫家,應該有義務用自己特長,速寫并記錄當下可貴的場景,用筆墨謳歌那些特殊時期為社會作出自己貢獻的平凡人物。
接下來的許多天時間,汪家芳埋頭揮毫,連續創作了20多幅《疫情下的平民英雄》水墨寫生小品。內容聚焦那些支撐起民眾信心、城市平穩的平凡人,如醫護人員、公安干警、快遞小哥、出租司機、環衛工人、菜場售貨員等形象。寫生畫稿經報刊與網絡公開發表后,引起許多良好反響,稱贊畫家具有敏銳的社會洞察力,細微之處彰顯社會正能量,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這是一股隱秘的、不起眼的力量在作出默默貢獻。”回想起那段時期重點創作的人物速寫,汪家芳記憶猶新且感慨不已。
疫情下,因為有這些普通而平凡的人在努力工作,保障了城市基本運轉,保障了民眾正常生活,可以這樣認為,他們就是這座城市的平民英雄。“我以自己繪畫所長謳歌他們,表達心中的贊揚與敬畏。記錄是藝術工作者的使命。藝術介入人類所經歷的災難,意義就在于記錄苦痛,也在于激勵人心、凝聚共識。它因創造者的飽含深情,而觸發觀眾的心靈共鳴。”
兩座城市同舟共濟,彰顯強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筑同心力量
隨著國內疫情逐漸得到有效控制,汪家芳“抗疫”繪畫專題創作的思路更加開闊。他想到,在20多幅《疫情下的平民英雄》水墨寫生基礎上,發揮自己更為擅長的山水畫題材進行創作,著力塑造生動感人的藝術形象,演繹“武漢加油”與“中國加油”的抗疫主題。
在武漢抗擊疫情的艱難時刻,一聲聲“武漢加油”從四面八方傳來。道不遠人,人無異域。面對疫情在湖北多點爆發,上海等國內多城市及時向有困難地區盡力提供幫助,派遣精兵強將醫療隊與物質趕赴當地,積極貢獻醫治經驗與解決方案。
汪家芳耳濡目染,強烈感受到黨中央與各級政府采取最全面、最嚴格、最徹底的防控舉措,不僅對本國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負責,也體現對全球公共衛生事業盡責的胸懷與擔當。
深感于此,他的心潮逐浪高,萌發出構思創作大尺幅作品,映現以上海與武漢為聚焦點,在黨中央部署下全國一盤棋,傾力支援武漢抗疫的真實與動人的場面。他將這幅畫命名為《巍巍中國情》。
2020年3月15日,是汪家芳繪制中國畫《巍巍中國情》開筆落墨的日子。之前10多天,面對鋪平于畫板的巨大宣紙,他久久沉思。巍巍長城、黃鶴樓、 布達拉宮、泰山南天門、武漢長江大橋、武漢金銀潭醫院,以及上海東方明珠、浦東上海中心、外白渡橋、華山醫院等標志性地標,還包括川流不息的海陸空物流輸送鏈等一連串創作元素,不斷在腦海中交替盤旋。腹稿由粗略布局到輪廓成形,一遍遍打磨修正與完善,胸中塊壘也隨之積攢與厚實。由此,心頭意念如同開閘洪流那樣,隨著畫筆揮灑彩墨而盡情宣泄,所有思緒通過畫稿上的點線面與色彩而延伸,演繹成了中華民族攜手大愛的壯麗畫面。
10多天連續奮戰之后,《巍巍中國情》創作完稿。該畫以“患難見真情,人間有大愛”為創作主旨,彰顯上海與武漢兩座英雄城市的人民,共飲一江水,同舟共濟、共克時艱,協力防控疫情的可歌場景,映現強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筑同心力量的創作初衷。
畫面中央偏右,千年屹立的黃鶴樓占據重要位置,意味著武漢城市標志性建筑的精神力量所在,象征中華民族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團結一心,匯聚起戰勝疫情的強大合力。在色彩與筆墨處理上,相比畫稿其他區域,采取工筆與寫意合一方式,突顯“武漢加油”“中國加油”強大的中國力量。
畫稿右側偏下,武漢長江大橋、武漢鐘樓、武漢市金銀潭醫院、武漢協和醫院等地標性建筑,相鄰矗立,與畫稿左面部分的上海東方明珠、浦東上海中心、黃浦江畔外灘鐘樓、外白渡橋,以及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上海市瑞金醫院、華山醫院等遙相呼應,象征著武漢有難,上海舉全市力量,傾全力出手相助,不僅派遣精兵強將,醫護人員逆行而動,趕赴現場實地治病救人,而且通過海陸空運輸鏈,相贈大批量的醫療物資和抗疫用品的真實場面。
其間,對于武漢協和醫院建筑物體的具象描繪,畫家作了特別手段處理。外觀上,采取低沉的黑色暈墨為主,樓層相隔之間的白色頗顯垂滴狀態,擬人化顯現疫情帶給人們的病痛與傷感。旁側部位,還以簡筆寫生方式,寥寥勾勒雷神山醫院、火神山醫院拔地而起,日夜兼程,熱火朝天加快建設的真實場面。
畫幅上方中央部位,則是萬里長城的標志性建筑烽火臺及攀登階梯,寓意中華民族的脊梁與風骨。畫幅左上方,布置著大面積連綿起伏的山脈,以及布達拉宮建筑和皚皚雪白的積雪,有著疫情當前,愛心和支持無遠弗屆,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的深層意味。
把握主題繪畫三個關系,探索藝術個性化表達形式
中國畫《巍巍中國情》完成了,汪家芳心中對于主題性繪畫創作的激情,意猶未盡。尤其是繪制巨大尺幅,他情有獨鐘,感觸頗深。
近幾年,他先后應邀創作繪制了《上海》《山高水長》《南大蝶變》《海天松濤圖》《春風又綠江南岸》(與人合作)等10多件大尺幅畫稿,每幅畫的面積幾乎都超15平方米以上。
如何把握主題性繪畫創作方向,怎樣以傳統山水畫筆法演繹當代風尚,汪家芳以不間斷的筆墨實踐,逐漸感悟出了個人心得。他認為,主題性繪畫創作應把握好三個關系,即形式創意中的思想性,大制作中的精致性,以及時代特征中的藝術個性。只有將這些要素合理且有序兼顧到了,主旨內容設置下的個性化表達形式,才能映現新時代美術應有的特點。
以中國畫《巍巍中國情》為例。畫面借鑒電影蒙太奇創作手法以及中國山水畫寫意筆法,既呈現時空交錯與地域之間的穿插,又營造塊面切割與彩墨暈染的美感,實現眾多景觀交相輝映的特殊效果。由此,畫稿突顯出武漢與上海兩地心手相應、共克時艱,凝聚成一股堅不可摧力量的創作主旨。
整幅畫雖然沒有一個人物出現,但千萬個中國人隱于其中,是他們構筑了巍巍中國。其間,特別敷設了濃重的筆墨,意在突顯有溫度、有信念的地標性城市輪廓,以及長江之水從西到東奔流向海的雄偉氣魄,擬人化地象征著中國民族挺起脊梁,積聚起巨大凝聚力。
頗具深意的是,《巍巍中國情》畫面中兩座鐘樓格外醒目。一座是上海的外灘鐘樓,另一座是武漢的江漢關鐘樓,遙相呼應,似乎告示著2020年間,這兩座不同城市的不同尋常,更有提醒人們警鐘長鳴的深刻意味。
汪家芳用畫筆,更是用深厚而獨到的情感,突顯了謳歌抗疫英雄,致敬最美逆行者的創作主旨。畫幅中,超越一個城市與一個國家的范疇,展現人類的命運與共理念,更是屬于他心中的殷切表達。
2018年6月,汪家芳受有關方面委托,獨立創作了體現上海城市歷史、文化、經濟、人文為主題內容的巨幅中國畫《上海》(寬7.5米、高5.4米,已陳列于西郊迎賓館貴賓廳),是迄今為止上海地區個人創作的單幅最大尺寸的中國畫之一。
畫面濃縮性地展示了江南文化、紅色文化和海派文化的意象,映現“這里是上海”的時代強音,突顯城市建設與發展而呈現的人文溫度、歷史厚度、建設速度和發展高度,展示作為中國“改革發展排頭兵、創新發展先行者”的偉岸氣魄。
畫作甫一亮相,即讓上海人驚嘆:這不就是我平常生活、喜聞樂見的上海場景嗎?很多蒞臨上海的外賓也頻頻點頭:這就是我眼中的上海。
《上海》之所以獲得廣泛認同,就在于它接地氣。不僅抓住了紅色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三種文化融合的典型特征,也在于它在描繪上海過去、展現上海未來的同時,更捕捉到了上海當下的脈動。
通過繪畫石庫門的特有形式,畫的是上海的日子、上海的煙火氣,來傳遞與突顯創作者所處時代的最強音,展示上海的城市風采,響亮“說”出上海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故事,“說”出上海改革開放、包容與創新的獨特個性。
對于如何以中國山水畫為表現形式的美術創作方式創作主題性繪畫,汪家芳思考良久。最近幾年,這種想法逐漸成為他常態化了的創作取向,他時常通過閱讀古典文獻、國內外寫生與實地采風等機會,強化意念,豐滿理想,以積累素材、勾勒畫稿等方式,付諸創新實踐。
唐宋之后,文人士大夫常將山水畫視作向內尋求安寧的方式。汪家芳嘗試打破此規矩。他認為,凡屬經典之作,描述的總是“此時此刻”,傳遞的總是創作者所處時代的最強音。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便是“此時此刻”。
繪畫是一種靜止的藝術,而“此時此刻”是不好抓的“活魚”。如何求得“此時此刻”的心想事成?汪家芳以實踐告之。他說:“熱愛生活就不會太難。繪畫技巧固然重要,但創作者感情比技巧更為重要。”他期望筆下的丹青作品,既有歷史的寬度與歷史的厚重,他也盼望那些內容有勾連、意境相統一,筆法有傳承、思想有崇高感的恢宏畫面,能夠藝術性地展現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追求。
不負韶華用畫筆述說愛國情懷
2020年5月,汪家芳精心繪制的百幅中國畫《話說徐霞客游記》,由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這項歷盡艱辛的創作,獲得2019年第一期上海市重大文藝創作項目選題孵化研發資助。
回首一百幅畫成稿過程,汪家芳不由得浮想聯翩、感慨系之。同樣題材畫一百幅畫?這不是為難自己?何況還要翻山越嶺實地考察、野外寫生。面對眾多好友不解,汪家芳說出了心里話。“捧讀《徐霞客游記》,他的求知精神、審美意識、實踐毅力,以及終其一生‘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誓言,深深打動我。徐霞客行走天涯,是以其獨特的個性,展現人類特有的求知精神,求真求是,為躬親體驗山河勝景而不懈游歷。這種對外在世界的純粹好奇,對祖國大美河山的敬畏,對未知疆域的真實記錄,講求親身體驗的求知精神,是人類有別于其他物種的特性,也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基本動因。徐霞客對祖國美好景觀的熱愛,以及他勇于擔當的精神,值得我學習,更值得我思考。”
2019年3月起,汪家芳開始了難以忘懷的長期野外寫生創作。全身心投入數量多且題材大的美術創作,既是長時期漸進式文化考量與深思使然,又是他久存心間的向往,有種積蓄力量之后,躍躍欲試,想要參與馬拉松長跑的渴望。在限定的時間段內完成百幅游記繪畫,對他來說最大的難度在于,思想意識等在內的所有表達,難以盡善盡美地周全。因為,繪畫是一種直觀的東西,所有內容都需要平面鋪展開來,一覽無余。
于是他背起畫架,手攜速寫本,沿著徐霞客當年行進足跡,跋山涉水,且行且記,留下了諸多創作心語。“藝術創作必須有實地采風寫生作支撐,走出畫室,去尋找自然萬物間屬于自己符號的藝術精神與語言。其時,空山寂寞,滿目荒寒,靜默遠山,那重山疊兀生發著我筆底的無限遐思,而氣勢雄偉的山川,又使我生發宋畫神韻與時代精神契合之聯想。”
采風途中,汪家芳時常會被千奇百怪的峰巒地貌而吸引,忍不住大聲贊嘆。時常,又會被神秘而遠古的曠野景致所震撼,止不住流連忘返的步履。累積而成的上千幅速寫畫稿,提升了他對徐霞客人文精神的再認識。
他感悟到,自然之美才是大美,即便一座古亭,一面石壁,一川碧流,抑或漁舟泊巖腳而息之景,山川薄霧層林隱寺之貌,也有其幽深的禪意,也有桃花源記般的仙境。行走之路,就是發現之路,眼有多高,手就自然有多高。只有用心用情細致體察所得,才有發現的收獲可得,才能夯實中國畫傳承與創新的基石。將寫生稿轉換成中國畫的過程,就是將采集于名山大川的氣息與感受,直抒胸臆地表達出來的過程,必須全身心投入,去完成這樣的“二度創作”。
“一頂巴拿馬草帽,一身簡易的硬漢行裝,永遠在大自然中行進,永遠在筆墨硯畫稿中行走。”這是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毛時安,對汪家芳重走徐霞客探索之路,實地學習徐霞客開拓創新精神的描述。
筆墨當隨時代,實踐提升作品精氣神
沿著徐霞客走過的路實地寫生,汪家芳笑言自己“厚重”了些許。以一百幅畫的方式致敬徐霞客,需要畫家超常的精力、專注力與意志力。“我希冀用我的所有努力,將視角聚焦于傳統經典名著題材,用中國畫形式表達民族經典,為建立民族的文化自信推波助瀾。”由此,對畢加索“藝術本身不變,而是人的思想在變”之說,有了更深理解。畫家尋求創新之路,關鍵在于更新與突破自我理念。
他在創作感言中寫道,寫生屬于畫家的一種生活狀態,靈泉之中本有幽秀并集的氣息。寫生之時不僅為眼前的靈山麗水所觸動,也常常被充滿神秘而鮮活的氣息所觸動而心生贊嘆,思緒翩翩。雖然我們生活在瞬息萬變的當代,但自然山水仍舊保持著原本的地質風貌,萬峰對峙,煙云萬象,不為塵世所動。尤其是登高遠眺之時,面對滿目煙云和青山綠水,創作激情油然而生。目睹云霞峰巒的變化莫測,就會感覺到自然界造化之功的神奇。
畫家是依仗眼睛與雙手表達思想的行動者,繪畫全過程,有很高的技術含量,且極富創造性。很多的想法,只有在宣紙上,通過線條與色彩的無窮變現,通過筆端一起一收剎那間的頓挫與使轉,才能得以盡情宣泄,從而用作品的形式實踐并實現了心中的創新理念。
真正在藝術上有追求的畫家,應當既有在畫齋中傳神臨摹古人優秀之作本領,又有出遠門寫生描繪大自然雄偉景色之特長,所謂“兩手硬”。傳承中學習古人,寫生時師法自然。古人的優秀傳統該盡善盡美地承繼,眼前生動的自然美景更應當傾情演繹。寫生山水,朝夕之景不同,四時之景也不同,移步換景,就是一幅全新的畫面。大自然千變萬化的山山水水,賦予畫家無窮的創作激情,敬畏自然,謳歌美景,創作道路大有可為。
“關注自己所處的時代精神,這是畫家必須做好的功課。”新中國成立以來產生重大影響力的美術作品,如董希文《開國大典》,石魯《轉戰南北》,陳逸飛、魏景山《占領總統府》,羅中立《父親》等,“直至今日,只要你站到畫前,那個時代的氣息依然會撲面而來,你依然會被濃郁的歷史感和使命感所震撼,真實感受到畫筆記錄下的宏大敘事。”
歷史上留存的名作,都是集時代大成者。藝術家如總是囿于傳統題材,追求的目標是畫得和古人一模一樣,那百年之后的人們,如何從我們作品中獲取這個時代特有信息呢?
“畫家需要終身學習,拓展眼界提升認知,用實踐提振自我精氣神。”繪畫作為終其一生事業,就必須在守住寂寞中砥礪前行。畫者獨步,敢于棄人所取、取人所棄,且取之執著,方有“坐殘明月”的享受和“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收獲快樂。
頗具探索意義的是,汪家芳百幅中國畫《話說徐霞客游記》,書法線條張力感韻味十足。他試圖將新的認知與純熟技法融合其間,展現新面貌。筆觸間傳承中有創新,既顯現宋畫雄強剛勁之手法,也有元畫典雅秀潤之意味,他探索的是如何將眾多前賢筆墨語言在畫面上合理貫穿,以現代人的審美視角,營造筆墨當隨時代的氛圍。 譬如為包括墨痕在內的色澤應用引入新元素,作品“五墨必備”,加之丙烯等顏料擇量參與,宣紙效果呈現出特有的亮麗,而線條、塊面、色彩營造的多維空間在通透性上,也有了改觀。
“百幅中國畫《話說徐霞客游記》創作,除了注重繪畫技法,更重要的是關注中國文化傳承。不負韶華,用手中畫筆述說愛國主義情懷,是當代美術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與擔當。”汪家芳有感而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