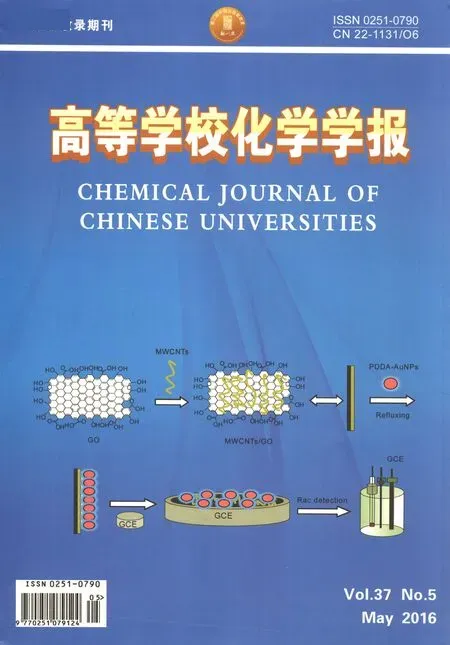β-硝基苯乙烯衍生物與丙烯酰胺及N-溴代丁二酰亞胺的區域專一性氨溴加成反應
杜曼飛, 侯 丹, 惠文萍, 陳戰國
(陜西省大分子科學重點實驗室, 陜西師范大學化學化工學院, 西安 710119)
?
β-硝基苯乙烯衍生物與丙烯酰胺及N-溴代丁二酰亞胺的區域專一性氨溴加成反應
杜曼飛, 侯丹, 惠文萍, 陳戰國
(陜西省大分子科學重點實驗室, 陜西師范大學化學化工學院, 西安 710119)
摘要以β-硝基苯乙烯衍生物為底物, 丙烯酰胺和N-溴代丁二酰亞胺(NBS)為氮源和鹵素源, 建立了碳-碳雙鍵上的選擇性氨溴加成反應新體系. 以二氯甲烷為溶劑, 在沒有惰性氣體保護及乙醇鈉促進下, β-硝基苯乙烯衍生物與丙烯酰胺和NBS于室溫反應即可高收率地獲得α-氨基-β,β-二溴加成產物, 最高收率達83%; 以甲醇為溶劑, 在無水碳酸鈉作用下, β-甲基-β-硝基苯乙烯衍生物也可高收率地獲得相應的鄰位氨溴加成產物, 最高收率達97%. 共考察了25種不同結構β-硝基苯乙烯衍生物的氨溴加成反應, 結果表明, 該反應具有廣泛的適應性. 采用核磁共振波譜及質譜表征了產物的結構, 并提出了可能的反應機理.
關鍵詞氨溴加成反應; β-硝基苯乙烯; 區域專一性; 丙烯酰胺; N-溴代丁二酰亞胺
烯烴的氨鹵加成反應是一類在碳-碳雙鍵上同時引入氨基和鹵原子而形成具有鄰位氨基鹵素雙官能團的重要反應[1]. 在一定條件下, 鄰位氨基鹵素可以發生分子內親核取代反應形成氮雜環丙烷, 再由氮雜環丙烷的開環-閉環反應構建一系列的雜環化合物; 由于鹵素是一個容易離去的基團, 可與其它親核試劑發生分子間的親核取代反應, 形成新的雙官能化合物(如氨基醇、 內酰胺及α,β-脫氫氨基酸衍生物[2]等); 鄰位氨基鹵素在一定條件下還可形成氨基烯, 進而發生Diels-Alder反應. 因此, 烯烴的氨鹵化反應在有機合成[3]、 藥物分子設計及天然產物結構改造[4]等方面有重要的應用.
β-硝基苯乙烯是進行氨鹵加成反應最有用的底物之一[5], 其加成產物中的硝基易被還原成氨基, 從而形成鄰位二氨基化合物[6], 該類化合物在化學和生物學上有廣闊的應用前景. 多數已報道的β-硝基苯乙烯的氨鹵化反應均需在氮氣保護下進行[7], 且所用氮源/鹵素源(如N,N-二氯對甲苯磺酰胺[8])的獲取比較困難. 近年來, 本課題組[9~14]對烯烴的氨鹵加成反應進行了深入研究, 發現多種新的氮源/鹵素源, 建立了多種氨鹵加成反應新方法. 在此基礎上, 本文研究了β-硝基苯乙烯衍生物的氨鹵加成反應, 建立了乙醇鈉和碳酸鈉促進下, 丙烯酰胺和NBS作為氮源和鹵素源的β-硝基苯乙烯衍生物的氨溴加成新方法. 以丙烯酰胺作為氮源, 可以在產物中引入一個丙烯酰氨基活性官能團. 由于丙烯酰氨基活性官能團能參與多種反應, 如可與其它試劑形成具有生物活性的聚合物[15], 在過渡金屬催化下, 聚合物繼續與芳香族腈類發生還原偶合反應, 形成吡咯烷酮衍生物[16]. 因此, 丙烯酰氨基的引入有望擴大氨鹵加成反應的應用范圍.
1實驗部分
1.1試劑與儀器
實驗所用試劑均為分析純, 使用前未經純化處理; 丙烯酰胺和N-溴代丁二酰亞胺(NBS)購自國藥集團化學試劑有限公司.
AVANCE600/300MHz超導傅里葉數字化核磁共振儀(瑞士Bruker公司);GCMS-Qp2010UItra型質譜儀(日本島津公司);BS224S型電子天平(德國賽多利斯集團);RE-52AA型旋轉蒸發器(上海亞榮生化儀器廠);XT5A型顯微熔點測定儀(北京市科儀電光儀器廠).
1.2實驗過程
1.2.1底物的合成參照文獻[17]方法合成β-硝基苯乙烯類化合物(1a~25a, 見Scheme1), 產物的熔點列于表1.

1a: R1=H, R2=H; 2a: R1=4-CH3, R2=H; 3a: R1=4-OCH3, R2=H; 4a: R1=3,4-(OCH3)2, R2=H; 5a: R1=3,5-(OCH3)2, R2=H; 6a: R1=2-Br-4,5-(OCH3)2, R2=H; 7a: R1=4-F, R2=H; 8a: R1=4-Cl, R2=H; 9a: R1=4-Br, R2=H; 10a: R1=3,4-Cl2, R2=H; 11a: R1=4-NO2, R2=H; 12a: R1=2-NO2, R2=H; 13a: R1=3-CHCHCHCH-4, R2=H; 14a: R1=H, R2=CH3; 15a: R1=4-CH3, R2=CH3; 16a: R1=4-OCH3, R2=CH3; 17a: R1=3,4-(OCH3)2, R2=CH3; 18a: R1=3,5-(OCH3)2, R2=CH3; 19a: R1=3,4,5-(OCH3)3, R2=CH3; 20a: R1=2-Br-4,5-(OCH3)2, R2=CH3; 21a: R1=4-F, R2=CH3; 22a: R1=4-Cl, R2=CH3; 23a: R1=4-Br, R2=CH3; 24a: R1=4-NO2, R2=CH3; 25a: R1=2-NO2, R2=CH3. Scheme 1 Synthesis route of β-nitrostyrene derivativesTable 1 Melting points of β-nitrostyrene derivatives 1a—25a

Compd.m.p.(Ref.)/℃Compd.m.p.(Ref.)/℃1a57.1—58.5(58[18])14a65.7—66.8(65—66[28])2a100.1—102.1(102—102.5[19])15a54.0—54.4(55[29])3a84.4—86.0(85.5—87.5[20])16a47.6—49(48[30])4a143.6—144.217a71.5—72.05a133.6—135.1(133.5—134.5[21])18a87.0—87.4(87—88[31])6a98—99(98—99[22])19a94.0—94.8(95[32])7a101—103(101—102.5[23])20a96.4—97.3(96—97[22])8a114.3—115.4(113—114[24])21a64.0—65.1(66[33])9a149.3—150.6(151—153[25])22a86—89(86—87[34])10a56.2—57.823a92.6—93.8(93—95[33])11a123.1—124.3(124.5—126[20])24a113.8—114.1(114—115[35])12a105.4—105.8(106—107[26])25a73.5—74.8(74[36])13a120—122(121—122[27])
化合物4a, 10a和17a均未見文獻報道. 化合物4a,1HNMR(CDCl3, 600MHz), δ: 7.90(d, J=13.6Hz, 1H,CH), 7.47(d, J=13.6Hz, 1H,CH), 7.11(d, J=8.3Hz, 1H,ArH), 6.94(d, J=1.9Hz, 1H,ArH), 6.85(d, J=8.3Hz, 1H,ArH), 3.88(s, 3H,OCH3), 3.86(s, 3H,OCH3);13CNMR(CDCl3, 151MHz), δ: 152.8, 149.6, 139.3, 135.2, 124.6, 122.8, 111.4, 110.3, 56.11, 56.03, 14.20;HRMS(C10H11NNaO4計算值), m/z: 232.0582(232.0586)[M+Na]+. 化合物10a,1HNMR(CDCl3, 600MHz), δ: 7.91(d, J=13.7Hz, 1H,CH), 7.65(d, J=2.0Hz, 1H,CH), 7.56(d, J=10.3Hz, 1H,ArH), 7.54(d, J=4.9Hz, 1H,ArH), 7.39(dd, J=8.3, 2.0Hz, 1H,ArH);13CNMR(CDCl3, 151MHz), δ: 138.3, 136.4, 133.9, 131.5, 130.6, 130.0, 127.9;HRMS(C8H5Cl2NNaO4計算值), m/z: 239.9588(239.9595)[M+Na]+. 化合物17a,1HNMR(CDCl3, 600MHz), δ: 8.00(s, 1H,ArH), 7.02(d, J=8.3Hz, 1H,CH), 6.92~6.84(m, 2H,ArH), 3.87(s, 3H,OCH3), 3.85(s, 3H,OCH3), 2.43(s, 3H,CH3);13CNMR(CDCl3, 151MHz), δ: 171.1, 150.8, 149.1, 145.9, 133.8, 125.0, 124.0, 113.1, 111.3, 111.2, 77.24, 77.03, 76.82, 60.38, 56.00, 56.00, 21.03, 14.18;HRMS(C11H13NNaO4計算值), m/z: 246.0737(246.0742)[M+Na]+. 化合物4a, 10a和17a的磁共振譜圖見圖S1~圖S3(見本文支持信息), 質譜圖見圖S4~圖S6(見本文支持信息).
1.2.2氨溴加成反應氨溴加成反應路線如Scheme2所示.

1b, 14b: R1=H; 2b, 15b: R1=4-CH3; 3b, 16b: R1=4-OCH3; 4b, 17b: R1=3,4-(OCH3)2; 5b, 18b: R1=3,5-(OCH3)2; 6b, 20b: R1=2-Br-4,5-(OCH3)2; 7b, 21b: R1=4-F; 8b, 22b: R1=4-Cl; 9b, 23b: R1=4-Br; 10b: R1=3,4-Cl2; 11b, 24b: R1=4-NO2; 12b, 25b: R1=2-NO2; 13b: R1=3-CHCHCHCH-4; 19b: R1=3,4,5-(OCH3)3. Scheme 2 Aminobromination of β-nitrostyrene derivatives with acrylamide and NBS
化合物1b~13b的合成: 以化合物1b的合成為例, 向25mL燒瓶中依次加入化合物1a(1.0mmol)、 丙烯酰胺(2.0mmol)、NBS(2.0mmol)、 乙醇鈉(1.1mmol)和10mL二氯甲烷, 室溫下攪拌, 用薄層色譜(TLC)跟蹤反應. 反應完成后, 向反應液中加入25mL乙酸乙酯稀釋, 稀釋液依次用飽和食鹽水(10mL×3)和蒸餾水(10mL×3)洗滌, 有機相用無水硫酸鈉干燥, 過濾除去干燥劑, 減壓濃縮. 粗產物經柱色譜[V(石油醚)∶V(乙酸乙酯)=2∶1]分離純化后真空干燥. 化合物2b~13b的合成方法與化合物1b相同.
化合物14b~25b的合成與化合物1b~13b的合成類似, 使用14a~25a各1.0mmol, 丙烯酰胺2.0mmol,NBS2.0mmol, 促進劑為Na2CO3(1.1mmol), 溶劑為甲醇(10mL).
化合物1b~25b的表征結果見表2和表3, 核磁共振譜圖見圖S7~圖S31(見本文支持信息), 質譜圖見圖S32~圖S56(見本文支持信息).

Table 2 Appearance, yields, melting points and HRMS data for compounds 1b—25b
*Yieldafterpurificationbycolumnchromatography.

Table 3 1H NMR and 13C NMR data for compounds 1b—25b*
Continued

Compd.1HNMR(CDCl3),δ13CNMR(CDCl3),δ16b7.19(d,J=8.7Hz,2H,ArH),6.84(d,J=8.8Hz,2H,ArH),6.36(dd,J=17.0,1.2Hz,1H,CH),6.23(dd,J=17.0,10.3Hz,1H,CH),5.80(d,J=9.7Hz,1H,CH),5.74(dd,J=10.3,1.2Hz,1H,CH),3.78(s,3H,CH3),2.24(s,3H,CH3)164.6,160.2,130.2,129.8,129.4,128.1,126.0,114.4,114.1,96.7,60.11,55.29,29.417b7.74(d,J=9.4Hz,1H,NH),6.88(d,J=8.0Hz,1H,ArH),6.83(s,1H,ArH),6.76(d,J=8.2Hz,1H,ArH),6.31(d,J=17.1Hz,1H,CH),6.25(t,J=13.4Hz,1H,CH),5.89(d,J=9.5Hz,1H,CH),5.66(d,J=8.7Hz,1H,CH),3.80(s,3H,OCH3),3.77(s,3H,OCH3),2.25(s,3H,CH3)165.0,149.7,149.0,130.1,128.2,126.5,121.0,111.8,111.2,96.9,60.40,55.98,55.81,28.8718b7.51(d,J=8.7Hz,1H,ArH),6.72(dd,J=7.5,5.8Hz,1H,ArH),6.51(dd,J=5.8,3.0Hz,1H,ArH),6.45(d,J=2.6Hz,1H,CH),6.38(dt,J=17.1,3.7Hz,1H,CH),6.26(t,J=6.5Hz,1H,CH),5.75(dd,J=10.1,1.4Hz,1H,CH),3.86(s,3H,OCH3),3.74(s,3H,OCH3),2.27(s,3H,CH3)164.5,160.4,157.2,136.1,129.9,128.3,105.8,103.8,100.2,93.82,59.33,56.43,55.58,28.2419b6.46(s,2H,ArH),6.39(dd,J=17.0,1.1Hz,1H,CH),6.26(dd,J=17.0,10.3Hz,1H,CH),5.78(dd,J=10.3,1.1Hz,1H,CH),5.72(d,J=9.6Hz,1H,CH),3.82(s,9H,3OCH3),2.25(s,3H,CH3)164.6,153.5,138.9,130.1,129.4,128.3,105.4,95.68,60.93,60.82,56.28,29.7120b7.04(t,J=17.9Hz,2H,ArH),6.56(s,1H,CH),6.43—6.38(m,1H,CH),6.29—6.26(m,1H,CH),5.77(d,J=10.3Hz,1H,CH),3.86(s,3H,OCH3),3.78(s,3H,OCH3),2.27(s,3H,CH3)164.5,150.1,149.3,129.9,128.4,125.8,116.2,116.0,115.7,109.6,94.06,60.40,59.44,21.0421b7.27(dd,J=6.0,2.7Hz,2H,ArH),7.02(t,J=8.6Hz,2H,ArH),6.37(dd,J=17.0,1.1Hz,1H,CH),6.23(dd,J=17.0,10.3Hz,1H,CH),5.85(d,J=9.6Hz,1H,CH),5.76(dd,J=10.3,1.1Hz,1H,CH),2.25(s,3H,CH3)164.7,163.9,130.5,130.1,130.1,129.9,128.5,116.1,116.0,96.41,59.98,29.4122b7.31(d,J=8.5Hz,2H,ArH),7.22(d,J=8.5Hz,2H,ArH),6.37(dd,J=17.0,1.1Hz,1H,CH),6.23(dd,J=17.0,10.3Hz,1H,CH),5.83(d,J=9.6Hz,1H,CH),5.76(dd,J=10.3,1.1Hz,1H,CH),2.25(s,3H,CH3)164.7,135.5,132.7,130.0,129.9,129.6,129.2,128.9,128.5,96.17,60.06,29.3923b7.47(d,J=8.5Hz,2H,ArH),7.16(d,J=8.5Hz,2H,ArH),6.37(dd,J=17.0,1.0Hz,1H,CH),6.23(dd,J=17.0,10.3Hz,1H,CH),5.81(d,J=9.6Hz,1H,CH),5.77(dd,J=10.3,1.0Hz,1H,CH),2.25(s,3H,CH3)164.7,133.2,132.2,131.9,130.2,129.9,129.9,128.5,123.7,96.03,60.13,29.4424b8.21(d,J=7.0Hz,3H,ArH,NH),7.49(d,J=8.7Hz,2H,ArH),6.39(d,J=16.3Hz,1H,CH),6.2(dd,J=17.0,10.3Hz,1H,CH),5.92(d,J=9.3Hz,1H,CH),5.82(d,J=10.4Hz,1H,CH),2.30(s,3H,CH3)171.6,165.3,148.2,141.7,130.0,129.9,129.5,129.0,123.7,96.59,59.95,21.0425b7.99(dd,J=20.3,8.1Hz,1H,ArH),7.72(d,J=53.7Hz,1H,ArH),7.63—7.50(m,2H,ArH),7.01(dd,J=31.6,8.0Hz,1H,CH),6.79—6.66(m,1H,CH),6.34(dd,J=27.1,16.6Hz,1H,CH),5.75(dd,J=17.5,9.7Hz,1H,CH),2.27(d,J=6.2Hz,3H,CH3)164.7,149.9,133.9,133.4,130.2,129.6,128.0,125.6,125.4,102.3,54.90,29.98
*Compounds1b, 8b, 9b, 11band18b:1HNMR(300MHz),13CNMR(75MHz);compounds2b—7b, 10b, 12b—17band19b—25b:1HNMR(600MHz),13CNMR(151MHz).
2結果與討論
2.1促進劑、 溶劑和反應溫度的影響
β-硝基苯乙烯屬于缺電子烯烴, 在加成反應中應該表現出Michael反應的特征, 堿是必要的促進劑. 首先選用β-硝基苯乙烯1a作為反應模板, 以丙烯酰胺和NBS作為氮源和溴源, 二氯甲烷作為溶劑, 室溫下對常見堿的促進作用進行了考察, 結果見表4. 由表4可知, 當促進劑用量為硝基苯乙烯的110%(摩爾分數)時(表4中Entries1~10),CH3CH2ONa對該反應有較好的促進作用(表4中Entry10, 收率為83%);K3PO4,K2CO3,Na2CO3,NaOH和KOH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但都不及CH3CH2ONa; 乙二胺和三乙胺等有機堿(表4中Entries8和9)不是該反應的有效促進劑. 進一步篩選CH3CH2ONa的用量(表4中Entries11~14)發現, 其用量為110%(摩爾分數)時收率最高, 增加或減少堿的用量, 收率都會下降. 對比實驗結果表明, 不加堿(表4中Entry15), 該反應只能得到痕量產物, 說明堿在反應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加熱回流時(表4中Entry23), 反應的收率未明顯提高. 通過對常用溶劑的篩選發現, 二氯甲烷是該反應的有效溶劑(表4中Entries16~22). 以中等活性β-甲基-β-硝基苯乙烯(14b)為底物模板, 丙烯酰胺和NBS作為氮源和溴源, 在CH2Cl2溶劑中反應24h的結果列于表4. 可見, 當促進劑用量為硝基苯乙烯的110%(摩爾分數)時(表4中Entries24~33),Na2CO3對該反應有較好的促進作用(表4中Entry26, 收率24%);K3PO4,NaOH,KOH,CH3ONa和CH3CH2ONa等無機堿也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但效果都不及Na2CO3; 乙二胺和三乙胺等有機堿(表4

Table 4 Effects of catalyst and temperature as well as solvent to the aninobronation of β-nitrostyrenea
a.Reactionconditionforformula(1)inScheme2: β-nitrostyrene(1.0mmol),acrylamide(2.0mmol),NBS(2.0mmol),catalyst,solvent(10mL), 25 ℃;forformula(2)inScheme2: β-methyl-β-nitrostyrene(1.0mmol),acrylamide(2.0mmol),NBS(2.0mmol),catalyst,solvent(10mL), 25 ℃; b.isolatedyieldaftercolumnchromatographicpurification; c.NR:noreaction.
中Entries32和33)不是該反應的有效促進劑. 在此基礎上對常用的溶劑也進行了篩選(表4中Entries34~40), 發現甲醇是該反應的最有效溶劑(表4中Entry40, 產率93%). 在確定甲醇為溶劑后, 進一步篩選Na2CO3的用量(表4中Entries40~43)發現,Na2CO3用量為110%(摩爾分數)時收率最高. 對比實驗結果表明, 不加堿(表4中Entry44), 該反應僅能得到痕量產物, 說明堿在反應中起到重要作用. 當加熱回流24h后, 反應變得相當復雜. 控制回流時間為2h, 僅得到了27%的目標產物(表4中Entry45), 說明提高反應溫度不利于該反應的進行.
上述實驗結果表明, 反應的優化條件為: (1)CH3CH2ONa(摩爾分數110%), n[β-硝基苯乙烯衍生物(1a~13a)]∶n(丙烯酰胺)∶n(NBS)=1∶2∶2, 溶劑為CH2Cl2, 室溫下攪拌反應; (2)Na2CO3(摩爾分數110%), n[β-甲基-β-硝基苯乙烯衍生物(14a~25a)]∶n(丙烯酰胺)∶n(NBS)=1∶2∶2, 溶劑CH3OH, 室溫下攪拌反應.
2.2底物結構對反應的影響
為了探索該反應的普適性, 在優化條件下對各種β-硝基苯乙烯衍生物的氨溴加成反應進行了考察, 結果列于表5. 可見, 各種硝基苯乙烯衍生物均能順利地進行氨溴加成反應, 但因結構不同而表現出不同的反應活性.

Table 5 Aminobromination of β-nitrostyren derivatives with acrylamide and NBS promoted by basea
a.RractionequationsarethesameasScheme2.Reactionconditionsforthesynthesesofcompounds1b—13b: β-nitrostyrenderivation(1.0mmol),acrylamide(2.0mmol),NBS(2.0mmol),CH3CH2ONa(110%,molarfraction),CH2Cl2(10mL), 24h, 25 ℃;reactionconditionsforthesynthesesofcompounds14b—25b: β-methyl-β-nitrostyrenederivation(1.0mmol),acrylamide(2.0mmol),NBS(2.0mmol),Na2CO3(110%,molarfraction),CH3OH(10mL), 24h, 25 ℃; b.isolatedyieldaftercolumnchromatographicpurification.
2.2.1反應活性與苯環上取代基的關系從反應收率看, 苯環上有供電子基團的β-硝基苯乙烯衍生物的反應收率相對較低(表5中Entries2~6, 40%~52%); 而對于苯環上有吸電子基的β-硝基苯乙烯衍生物, 其反應收率相對較高(表5中Entries7~12, 收率56%~81%); 1-萘型的硝基烯得到中等收率(表5中Entry13, 收率58%). 以上結果表明, 對于β-硝基苯乙烯衍生物, 碳-碳雙鍵上電子密度越小, 反應的活性越高; 同時底物的空間位阻越大, 反應的活性越低. 對于β-甲基-β-硝基苯乙烯衍生物(14a~25a), 在優化條件下, 反應活性的規律與β-硝基苯乙烯衍生物活性的規律相似. 當苯環上有給電子基團時, 其氨溴加成反應活性降低, 相應的收率也隨之降低(表5中Entries15~20, 收率19%~45%). 當苯環上有吸電子基團時, 其反應活性增強, 反應收率也相應提高(表5中Entries21~25, 收率52%~97%). 當苯環上有多個取代基時, 特別是在苯環的3,5-位有強的給電子基時, 電子效應和位阻效應的疊加導致反應收率進一步下降(表5中Entries18和19). 以上結果表明, 無論是β-硝基苯乙烯衍生物還是β-甲基-β-硝基苯乙烯衍生物, 其氨溴加成反應的活性不僅取決于底物的空間位阻效應, 還取決于底物雙鍵上的電子效應. 雙鍵上的電子密度越低, 其反應活性越高; 反之, 雙鍵上的電子密度越高, 其反應活性越低. 此結果表明, 該氨溴加成反應可能是一個親核加成反應.

Fig.1 Crystal structure of 1-acrylamido-2,2-dibromo-1-(4-methylphenyl) nitroethane(2b)
2.2.2反映的區域選擇性從2類反應的結果看, 所有產物中氨基均加在與苯環相連的碳原子上, 而溴原子則加在與硝基相連的碳原子上, 表現出區域專一性. 為了進一步確證反應的區域選擇性, 對其中1個加成產物進行了單晶結構分析. 1-(4-甲苯基)-1-丙烯酰胺-2,2-二溴-2-硝基乙烷(2b,CCDCNo.1432487)的單晶結構分析結果表明, 氨基加在與苯環相連的碳原子上, 而溴原子加在與硝基相連的碳原子上, 而且該碳原子完全溴化(見圖1). 其它產物的結構以1HNMR和13CNMR波譜中的化學位移和氫的偶合常數得以確證, 說明堿催化能高度控制該反應的區域選擇性.
2.2.3鹵素源的普適性為了考察該反應對鹵素源的普適性, 將實驗所用鹵素源NBS換為N-氯代丁二酰亞胺(NCS), 以丙烯酰胺為氮源, β-硝基苯乙烯為底物, 在相同的實驗條件下制得1-苯基-1-丙烯酰氨基-2,2-二氯-2-硝基乙烷白色固體作為對照,m.p. 168.5~168.7 ℃,HRMS(C11H10Cl2NaN2O3計算值), m/z: 310.9955(310.9966)[M+Na]+, 質譜圖見圖S57(見本文支持信息), 說明鹵素源NBS和NCS均適合該反應(見Scheme3).

Scheme 3 Aminochlorination of β-nitrostyrene with acryl amide and NCS

Scheme 4 Possible mechanism of the aminobromination reaction
2.3反應機理
根據實驗結果提出了與文獻[37]相似的反應機理, 如Scheme4所示. 首先, 丙烯酰胺和N-溴代丁二酰亞胺之間發生質子和溴的交換反應, 建立一個4組分共存的平衡體系(混合物的1HNMR圖譜見圖S58, 見本文支持信息), 生成重要的中間體N-溴代丙烯酰胺(A), 在堿(B=CH3CH2O-或NaOCOO-)的作用下, 中間體A失去質子, 產生一個氮負離子B,B作為親核試劑與β-硝基苯乙烯發生加成反應, 生成中間體C, 接著發生分子內溴正離子的遷移, 得到中間體D. 當β-硝基苯乙烯結構中R=H時, 中間體D發生氫遷移得到中間體E,E與A作用得到產物P1(即產物1b~13b), 同時A被轉變成氮負離子F,F再與另一分子A作用得到氮負離子B,B參加下一次循環. 當β-硝基苯乙烯衍生物結構中R為甲基時, 中間體D與A作用生成產物P2(即產物14b~25b)和中間體B,B再參與下一次循環.
3結論
以丙烯酰胺和N-溴代丁二酰亞胺為氮源/溴源, 分別以二氯甲烷和甲醇作溶劑, 在不同促進劑CH3CH2ONa和Na2CO3的存在下, 建立了2類不同的β-硝基苯乙烯衍生物的氨溴加成反應新體系. 該反應具有條件溫和、 操作簡單、 可接受的收率及區域選擇性高等特點. 該反應以不飽和酰胺作為氮源, 在產物中引入了1個丙烯酰氨基活性官能團. 由于該活性官能團能參與多種反應, 如可與其它試劑形成具有生物活性的聚合物, 在過渡金屬催化下, 聚合物繼續與芳香族腈類發生還原偶合反應, 形成吡咯烷酮衍生物. 因此, 丙烯酰氨基的引入有望擴大氨鹵加成反應的應用范圍. 通過大量不同結構的氨溴加成反應活性的比較, 證明該類缺電子烯烴的氨溴加成反應是一個親核加成反應. 在實驗基礎上, 提出了可能的反應機理.
支持信息見http://www.cjcu.jlu.edu.cn/CN/10.7503/cjcu20150883.
參考文獻
[1]KempJ.E.G.,FlemingM.I., Comprehensive Organic Synthesis,Pergamon,Oxford, 1991, 471—513
[2]ChenD.J.,GuoL.,LiuJ.Y.,KirtaneS.,CannonJ.F.,LiG., Org. Lett., 2005, 7(5), 921—924
[3]YeungY.Y.,GaoX.R.,CoreyE.J., J. Am. Chem. Soc., 2006, 128(30), 9644—9645
[4]BaerH.H.,RankW., Can. J. Chem., 1974, 52(12), 2257—2267
[5]LiuY.L.,LiuD.E.,DuM.F.,CaoC.X.,ChenZ.G., Chem. J. Chinese Universities, 2015, 36(6), 1117—1125(劉亞麗, 劉德娥, 杜曼飛, 曹晨茜, 陳戰國. 高等學校化學學報, 2015, 36(6), 1117—1125)
[6]NishimuraT., Bull. Chem. Soc. Jpn., 1954, 27, 617—619
[7]ZhiS.J.,SunH.,LinC.,ZhangG.Q.,LiG.,PanY., Science China: Chemistry, 2010, 53(1), 140—146
[8]LucetD.,ToupetL.,LeG.T.,MioskowskiC., J. Org. Chem., 1997, 62(9), 2682—2683
[9]ChenZ.G.,ZhaoP.F.,WangY., Eur. J. Org. Chem., 2011, 5887—5893
[10]ChenZ.G.,HuJ.L.,XiaW.,WangD.,LiY.N., Chem. J. Chinese Universities, 2013, 34(5), 1151—1159(陳戰國, 胡均利, 夏偉, 王丹, 李亞男. 高等學校化學學報, 2013, 34(5), 1151—1159)
[11]ChenZ.G.,XiaW.,WenH.,WangD.,LiY.N.,HuJ.L., Chem. Res. Chinese Universities, 2013, 24(9), 699—705
[12]ChenZ.G.,LiY.N.,ZhouJ.M.,WangD.,GeM., Chem. Res. Chinese Universities, 2014, 30(2), 266—271
[13]ChenZ.G.,LiuD.E.,LiW.L.,LiuY.L., Chem. J. Chinese Universities, 2014, 35(11), 2360—2365(陳戰國, 劉德娥, 李文麗, 劉亞麗. 高等學校化學學報, 2014, 35(11), 2360—2365)
[14]ChenZ.G.,LiuY.L.,HuJ.L.,LiuD.E., Chem. Res. Chinese Universities, 2015, 3(11), 65—70
[15]BauerJ.,RappA.,StanislawskiB.,CapitoF., Copolymers for Protein Precipitation,MerckPatentGmbH,Germany,PCTInt.Appl.,WO2014094957A1, 2014-06-26
[16]WongY.C.,ParthasarathyK.,ChengC.H., J. Am. Chem. Soc., 2009, 131(51), 18252—18253
[17]FryszkowskaA.,FisherK.,GardinerJ.M.,StephensG.M., J. Org. Chem., 2008, 73(11), 4295—4298
[18]MilhazesN.,CalheirosR.,MarquesM.P.M.,GarridoJ.,CordeiroM.N.D.S.,RodriguesC.,QuinteiraS.,NovaisC.,PeixeL.B.F., Bioorg. Med. Chem., 2006, 14(12), 4078—4088
[19]WangW.,WangJ.,LiH., Angew. Chem. Int. Ed., 2005, 44(9), 1369—1371
[20]OheT.,UemuraS., Bull. Chem. Soc. Jpn., 2003, 76(7), 1423—1431
[21]LloydH.A.,KielarE.A.,HighetR.J.,UyeoS.,FalesH.M.,WildmanW.C., J. Org. Chem., 1962, 27, 373—377
[22]WangY., Study on the Aminobromination of β-Nitrostyrene Derivatives with Acetamide and NBS,ShaanxiNormalUniversity,Xi’an, 2010(王蕓. β-硝基苯乙烯與乙酰胺/N-溴代丁二酰亞胺的氨溴加成反應研究, 西安: 陜西師范大學, 2010)
[23]SandharR.K.,SharmaJ.R.,ManraoM.R., J. Ind. Chem. Soc., 2006, 83(3), 263—265
[24]CampbellN.,AndersonW.,GilmoreJ., J. Chem. Soc., 1940, 446—451
[25]OheT.,UemuraS., Bull. Chem. Soc. Jpn., 2003, 76(7), 1423—1431
[26]CorbettJ.F.,HoltP.F.,HughesA.N., J. Chem. Soc., 1960, 3643—3645
[27]KoremuraM.,OkuH.,ShonoT.,NakanishiT., Takamine Kenkyusho Nenpo, 1961, 13, 216—221
[28]MilhazesN.,CalheirosR.,MarquesM.P.M.,GarridoJ.,CordeiroM.N.D.S.,RodriguesC.,QuinteiraS.,NovaisC.,PeixeL.,BorgesF., Bioorg. Med. Chem., 2006, 14(12), 4078—4088
[29]WorrallD.E., J. Am. Chem. Soc., 1938, 60, 2841—2844
[30]MilhazesN.,BorgesF.,CalheirosR.,MarquesM.P.M., Analyst, 2004, 129(11), 1106—1117
[31]MathisC.A.,ShulginA.T.,SargentT. Ⅲ., Journal of Labelled Compounds and Radiopharmaceuticals, 1986, 23(2), 115—125
[32]PradhanP.K.,DeyS.,JaisankarP.,GiriV.S., Syn. Comm., 2005, 35(7), 913—922
[33]AgafonovN.E.,SedishevI.P.,DudinA.V.,KutinA.A.,StashinaG.A.,ZhulinV.M., Izvestiya Akademii Nauk SSSR, Seriya Khimicheskaya, 1991, (2), 426—433
[34]NguyenB.,ChernousK.,EndlarD.,OdellB.,PiacentiM.,BrownJ.M.,DorofeevA.S.,BurasovA.V., Angew. Chem. Int. Ed., 2007, 46(40), 7655—7658
[35]YangJ.K.,ZhengM.,LuoS.P.,LiZ.B., Acta C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E: Structure Reports Online, 2010, 66(7),o1781
[36]NiwasS.,KumarS.,BhaduriA.P., Synthesis, 1983, (12), 1027—1028
[37]ChenZ.G.,ZhouJ.M.,WangY.,LiW.L., Acta Chim Sinica, 2011, 69(23), 2851—2858(陳戰國, 周繼梅, 王蕓, 李文麗. 化學學報, 2011, 69(23), 2851—2858)
(Ed.:P,H,W,K)
?Supportedbythe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No.20572066),the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ShaanxiProvince,China(No.2009JM2001)andtheInnovationFoundationofPostgraduateCultivationofShaanxiNormalUniversity,China(No.2008CXB009).
doi:10.7503/cjcu20150883
收稿日期:2015-11-19. 網絡出版日期: 2016-04-20.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批準號: 20572066)、 陜西省自然科學基金(批準號: 2009JM2011)和陜西師范大學研究生創新基金(批準號: 2008CXB009)資助.
中圖分類號O626.3
文獻標志碼A
RegiospecificAminobrominationofβ-NitrostyreneDerivativeswithAcrylamideandN-Bromobutanimide?
DUManfei,HOUDan,HUIWenping,CHENZhanguo*
(Key Laboratory for Macromolecular Science of Shaanxi Province, School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A new protocol for the high regioselective aminobromination of β-nitrostyrene derivatives with acrylamide and N-Bromobutanimide(NBS) as nitrogen/bromine sources was developed. β-Nitrostyrene derivatives reacted with acrylamide and NBS promoted by CH3CH2ONa at room temperature(without the protection of an inert gaseous atmosphere) in CH2Cl2, offered vicinal haloamine products in good yields(up to 83%). For the β-methyl-β-nitrostyrene, the good yields(up to 98%) were also achieved in CH3OH promoted by Na2CO3. Although the strong electron-donating substituents(e.g., OCH3) on the 4-position of benzene ring could deactivated the reaction activity of β-nitrostyrenederi-vetives, the vicinal haloamines were also afforded as the sole addition product. Whereas strong electron-withdrawing substituents(e.g., NO2) could activated reaction activity remarkably and the vicinal haloamines were afforded as the sole addition product, too. The result revealed that the addition reaction has a nucleophilic addition feature. The aminobromination of 25 examples of β-nitrostyrenes were investigated and the structure of all products were confirmed by the corresponding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NMR) spectra and high resolution mass spectrometer(HRMS). A possible mechanism involving a nucleophilic conjugate addition was proposed.
KeywordsAminobromination; β-Nitrostyrene; Regiospecific; Acrylamide; N-Bromobutanimide
聯系人簡介: 陳戰國, 男, 博士, 副教授, 主要從事有機合成及天然產物結構改造方面的研究.E-mail:chzhg@snn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