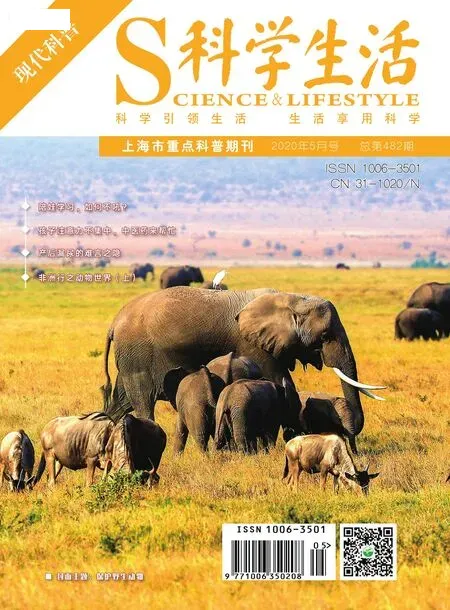由“與子同袍”說起……
文/馮憲編輯/丙丁
2020年春節期間,中央電視廣播總臺綜合頻道播出了《中國詩詞大會》第五季,節目內容豐富、知識點多,很吸引人,觀看后會讓人得到意外的收獲與啟發。筆者在其中一場的現場答題環節看到了“與子同袍”這一詩句,由此引發了立足本專業,審視、探究其中蘊含的中華傳統服飾文化的興趣。該詩句源于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詩經》,所收錄的作品大多描寫了西周至春秋中期的社會生活和人文情感。“與子同袍”的詩句出自其中的《秦風·無衣》,全詩如下: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據考證,這是一首誕生于先秦時期的詩歌,距今已有2 700余年了。是由當時亦農亦兵的先民創作的,表現的是戰士們聽從號令,團結一心,共赴沙場,保衛家鄉的一種剛烈、堅定的決心,屬于一種出征和戰前動員的詩歌。此首詩歌的誕生地為西周晚期、東周初期秦襄公時期的秦地(今陜西中部和甘肅東南部),當時該地區的華夏先民與西北方的少數民族西戎、北狄為鄰,邊疆經常會受到少數民族的騷擾和進犯,所以軍事管轄者在當地實行了民兵制度,即青壯男丁平時無事時在家耕田種地,一旦邊疆發生戰事,便集合起來,穿上同色、同款的作戰服裝,拿起武器,跟隨統帥開赴戰場御敵,捍衛家鄉安全。
其實,這首詩除了表現出保衛家鄉壯士們濃烈的愛國主義情感之外,還展現出中華服飾文化的源遠流長,生動描繪了我國古代的衣著文明。在這首短短三行、60余字的詩里面,與服裝品種及穿著有關的關鍵字竟多達五個,這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中的作品大都來自民間,創作內容與日常生活及身邊環境息息相關的特色。本文所要深究的正是這方面的內容。

▲“衣”字的演進
衣——此詩中出現的“衣”特指那種顏色相近、款式相同,識別效果突出的作戰專用服裝,或者可以說是類似于現代的軍裝。因為集合部隊作戰,首先要有利于指揮者進行統一調動和管理,士兵之間也要能夠相互呼應、協同。另外,裝束還需要明顯有別于對手,以便在兩軍對壘、搏殺時能夠分得清敵我,防止出現誤傷。據考證,漢字“衣”最早出現于商朝的甲骨文、金文中,距今已有3 500多年的歷史了。在古代,作名詞使用的“衣”一般是指上身穿著的服裝,后來又成為服裝的總稱,并引申為覆蓋在或包在物體表面的東西,如“地衣”“腸衣”等。在古代,“衣”還作動詞用,表示包裹、覆蓋,乃至“穿”的意思。如在《論語》中,孔子稱贊自己的學生子路時就說“衣敝缊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意思是說(子路)穿破舊的麻綿外衣,與穿名貴皮草的人站在一起并不感到羞恥與低下。到了現代,人們一般把上身穿著的服裝叫做“上衣”。

▲古今之“袍”
袍——對于人類社會而言,“袍”這種服裝出現很早,是起初最簡約的一種外穿類服裝形式,無論中西,皆是如此。此詩中出現的“袍”特指一種不貼身穿著的直腰身、窄袖口結構,穿脫方便,且能覆蓋全身的服裝。“袍”通常能夠起到御寒保暖、護體和身份辨別的作用,由此可以推測,當時邊疆的戰事大約是發生在深秋或初冬,否則士兵們不會加穿袍子這種服裝。后來,隨著社會進化和生產手段的多樣性,“袍”的變化也豐富起來。我國古代至近代,“袍”曾有過龍袍、官袍和民袍之分。所謂龍袍特指皇帝穿著的服裝,用名貴絲綢作面料,其特征是盤領(圓形領口)、右衽(由左向右系扣)、寬袖寬擺,并以明黃色為主色調,因袍上繡有龍的紋樣而得名,又稱龍袞、袞服、黃袍,清代的龍袍還配有“水腳”,即在袍的下擺等部位繡有水紋山石的圖案,隱喻山河統一。所謂官袍是指朝廷任命的文武官員公干或上朝時所穿的服裝,通常用絲綢做面料,外形也為寬袖寬擺,并以一定顏色或刺繡圖案表明官位等級的大小。比如唐朝武則天主政時,曾規定文官的官袍繡上不同種類的禽,武官的官袍繡上不同種類的獸,以示區別。所謂民袍是指民間人士普遍穿著的外衣,它外形為窄袖窄擺,用料平常,以麻、棉布居多,顏色單一,且縫制簡單,不加任何額外修飾。一些延續到近現代的“袍”類服裝款式,如長衫、旗袍等都還保留有“袍”的這種“一體化”的基本元素。古代的“袍”有單、夾和長短之分,單袍在春夏季穿,夾(棉)袍在秋冬季穿著,長的“袍”下擺及至鞋面,多為官員、文人和商賈之人穿著;短的“袍”則下擺剛過膝蓋,多為農人、販夫、走卒穿著。故此詩提到的“袍”應該是一種短“袍”,必須利于士兵在作戰時作跨越或奔跑等大幅度動作。

▲上衣下裳(明代)
澤——此詩中出現的“澤”是指貼身穿著的一種衣物,也叫做里衣、汗衣、褻衣,現在一般叫做內衣。在古代漢語里,“澤”字有光滑、柔潤之解,故用此字命名貼身穿著的服裝十分貼切,因為這種服裝穿著的親膚感和舒適感十分明顯,且具有吸汗排濕功能,由此看得出先人們很早就注重穿衣的“內外有別”。他們通常把細密、柔軟、輕薄、透濕透氣的材料用作貼身穿著服裝的縫制,減少粗糙不適感,提高透氣排濕的舒適功效,并賦予一個形象化的字——“澤”。現如今,盡管很久以來人們已經不再把內衣稱之為“澤”,許多年輕人也未必知道“澤”在古代有內衣的這一層含義,但是,這種穿衣方式得到了延續,“澤”所體現的親膚、舒適的內涵始終有所傳承。比如現在人們不會把細帆布、厚卡其等粗糙感強的布料用作貼身服裝,而喜歡貼身穿著那些感覺柔軟、細膩的內衣,多采用全棉、真絲或羊毛羊絨材料,施以針織技術加工而成,富有一定伸展力。
裳—— 此詩中出現的“裳”字 讀作cháng(音同“常”),而“裳”字與“衣”連用時,則讀作shāng(音同“商”),“衣裳”一詞現一般作為服裝的統稱。詩中的“裳”字做“下衣”解,相傳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黃帝時期就有“上衣下裳”的說法。最初的“裳”分有前后兩個部分,按照拼縫布料的塊數為“前三后四”,前后布料通過腰帶拼攏后會在兩側交接處形成重疊部分,以便在不影響下肢活動的同時,能夠起到遮蔽與保護下體的作用。到了漢代,才開始把前后兩片連起來形成筒狀,類似現在的“裙”。當時“裳”的穿著是不分性別的,“裳”便視同于“裙”。自兩千三百多年前戰國時期,趙國的趙武靈王趙雍吸收域外少數民族服飾優點,倡導“胡服騎射”之后,褲子(最初名為“袴”)這種利于騎馬時下身穿著的服裝款式便開始在中原地區出現,豐富了“下衣”的形式。起初,“袴”僅限于軍隊中士兵的使用,而民間使用多為“绔”——一種兩個褲腿狀物分開、當中無合襠部位,靠系帶縛于腰間的護腿用品,也叫“脛衣”和“裈”——一種合襠的、無褲腿或短褲腿的護體用品,且延續了許多朝代。到了近代,與“裳”同義的“裙”便逐漸變成對女子“下衣”的一種稱謂了。

▲穿袍披甲的秦兵馬俑

▲與子同袍,抗擊“疫”魔
甲——此詩中出現的“甲”便是護甲的意思,系指一種士兵在戰場上穿著的、具有保護自身安全的特殊防護服裝。當時受材料來源和生產手段的制約,士兵身上所穿的“甲”,多半是由藤條或牛皮制作的,主用來抵擋刀、劍、斧、戟、箭等冷兵器的打擊。另外,此處的“甲”還應該包括盾牌,因為盾牌也是一種有效的近體防身物品,且通常持刀作戰的士兵都是一手拿刀,一手持盾,能夠做到進退自如、攻守兼備。現在看來,那個時候的“甲”可以算作是當今各類防彈衣的“鼻祖”了。
通過閱讀一首古詩,回溯一下中華民族服飾的歷史源頭,并做出一些專題梳理和歸納,有一定現實意義。因為當今在談及服飾時尚文化時,民族文化的問題不容忽視,深入探究這些古代服裝形式,能夠幫助我們加深理解中華民族“衣冠大國”“衣被天下”這些詞語背后的歷史根基所在。
在當下抗擊“疫”情的重要時刻,“與子同袍”也成為了最為壯烈、激昂的動員令,表達了身穿統一防護服裝的廣大醫護工作者,像古代保衛家國的將士們一樣,義無反顧、舍生忘死地奔赴救死扶傷第一線,與“疫”魔進行抗爭,爭取挽救更多患者生命的錚錚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