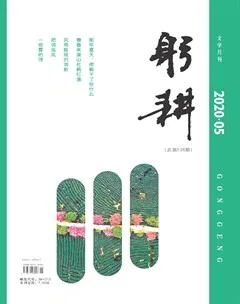山路彎彎,鄉情繾綣
楊麗琴
山不高路卻遠,偏遠的小山村是他的老家。
娘家有一句俗話:“女兒家一不嫁山里,二不嫁圩上。”但自從和他相識以來,從沒想過,那個隔山隔水的地方與我有多大瓜葛,我們的“人財物”都遠離了那里,也有自己的一片小天地。父母在,逢年過節,禮節,孝順,盡為人子之責;父母去,三間磚瓦老屋,破舊,倒塌,漸漸消失于歲月的風霜里,我們以及我們的后代,也將離那座小山村,愈行愈遠。但是,最近發生的一件事,讓我明白:不管走多遠,我們與那個小山村,從來沒有走遠,依舊是拉拉扯扯、藕斷絲連的……
一日,已經逐漸淡忘那座小山村的我,忽然接到娘家親戚電話,說老家要拆遷了,要我送相關證明材料去,可享受福利分房待遇。問及原因:祖居戶,母親尚在。對于此事,純屬于意外之外的意外,我早已遠離了娘家,作為女人,生我養我的地方,成了遙遠的符號。可這祖居二字,只輕輕一聲呼喚,就輕而易舉將我牽了回去,且義無反顧。
祖居,猶世居,世代居住。古時侯,那些遠離家鄉,在外經商為官的仕途名人,老了,病了,要“告老還鄉”“告病還鄉”。《世說新語·識鑒》記載:“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莼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棄官回鄉歸隱。明朝翰林院東閣大學士于慎行,到了晚年告病還鄉,居住在云翠山下洪范池邊的于家村。每天讀書著書,著名的《谷山筆麈》一書,就是那時完成的。
閑時讀書,更有懷鄉詩詞躍然紙上。薛道衡《人日思歸》詩:“人歸落雁后,思發在花前”;柳宗元的《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若為化得身千億,散上峰頭望故鄉”;還有南唐后主李煜《子夜歌》詩:“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虞美人》詩:“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現代著名詩人余光中《鄉愁》里:“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
古人今人,心里想的,夜里夢的,兼及筆下的故園家國,故鄉都是一份戀戀不舍的情懷,是寧靜安詳的樂土,是生命旅途的魂夢之地。
從記事時起,每年春節一過,村子里的壯年男子就背起行囊,遠離親人,外出做手藝活,他們背井離鄉,足跡遍布祖國的大江南北,留下來耕植這片土地的,清一色是老人和女人。90年代初,村子里年輕的女人們也加入了城市打工的行列,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的土地很多已經撂荒,因為土地上一年到頭再怎么打捏,也只能圖個溫飽。陸續有去異鄉學習就此安了家的;有女兒直接嫁到外地的;也有兒子在城市買房定居的。村子里的人不再依靠著土地上的收成生活。曾經興旺繁盛的山村,漸漸繁華不再。
我時常想,過去的生產力那么低下,村里人都能在家鄉安居樂業,不舍得離家。也印證了那句俗話:“美不美家鄉水,親不親故鄉人。”可現在呢?為什么一個個不辭辛苦,走得那么理所當然,那么義無反顧呢?難道,經濟的追求真有那么大的魔力?人們對于生活更高更美的要求只有在異地他鄉才能實現?
從古到今,詩人筆下寫的,書生口里念的,依舊是割舍不斷的鄉愁。可如今,怎么會是另一種境況?鄉親們對于生我養我的故鄉,說舍就舍,毫無一絲一毫的留戀。這是社會的進步,還是人們思想觀念的衰退?古老的鄉愁,代代相傳到今天,難道真的會成為人們永遠的回憶?
18歲的年齡,沖動又莽撞,要強的我隨著人流也涌進了城市的大海。臨走時,沒有不舍,只有決絕,我不想讓那個叫淚水的東西流下來,打濕了好不容易積攢起來的勇氣。走出村子,走到村頭的老槐樹下,我回轉身,閉上眼睛,雙手緊緊按著狂亂跳動的胸口,默默地許了一個童話般的夢想。那時,我始終感覺自己是城市的“異鄉客”。每次回家時,踏著柔軟的泥土,聞著鄉土的氣息,吃著父母從這片土地收獲的飯菜,左鄰右舍那樸實的鄉音鄉情,心里總會涌起莫名的溫馨和親切。我如一尾魚,盡管游出了千里萬里,但是,時不時地我選擇了洄游,回到了這里。
后來,在城里成了家,養育兒女,在這里生活、交友、娛樂;從一家人蝸居在單位十幾平方的宿舍,換成幾十平方的寬敞明亮的套間。行走于喧囂的城市街頭,融入多彩多姿的城市生活,漸漸地熟悉了環境,并自許為城市的一分子。城里當作了“家”,而老家,那個生我養我的地方好似成了驛站,每次都是來去匆匆,即使住上一晚,偶爾停一停腳 ,心里還是記掛著城里的家。夢里只覺身是客,哪晌可曾貪歡?山風吹得人不寐,只把故鄉做他鄉。
記得兒子小時候,一次我們去山里的老家,吃過飯后,因兒子有飯后睡覺的習慣,就一直哼哼著要回家。一旁的婆婆聽見了,笑著說,“這里就是你的家啊!我來鋪床給你睡。”兒子卻不知忌諱地說:“這不是我家,我家在城里。”
臨時辦事處設置在村后一處廢棄的公房里,院里院外,停滿了各種車輛。辦事的人,你來我往,川流不息。我靜靜地待在一旁,面前的這些似曾相識的面孔,光鮮也好,滄桑也罷,很多已經還原不出舊時的模樣。歲月的刻刀,不偏不倚地在每個人的身上臉上,刻下深深淺淺的印記。無論老少,無論男女,無論貴賤。
信步走出院子,踏上村后的田間小路,我將曾經走過的土地,走了一遍又一遍。猛然間我發覺:歲月可以催老我們的容顏,卻無法磨滅土地的情懷,那是扎進土地的根的情懷,也是骨子里無法磨滅的依戀。走遍了大江南北,長城內外,驀然回首,我的根還在這里。不管你回不回來,它,都在這里等你,念你。那一刻,我淚眼滂沱。我才知道,什么是根,什么是脈。什么是影,什么是心。
現代化的進程中,我的祖居之地,一步步走過來,早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是,土地還是那片土地,莊稼還是那片莊稼。土地上,可以種麥子,也可以種花生;可以長稻谷,也可以長蔬菜;可以蓋鄉間民房,也可以建城鎮化的高樓;可以從事農業,也可以從事工業。這片土地,一味任憑人們來安置,從來都是不聲不響,任勞任怨,敞開了心扉,任人們予取予求。一如沉默的智者,只管靜觀,不參與評論。永遠做著根的事業,執行根的使命。
都說:“父母在,人生尚有來處,父母去,人生只剩歸途。”這片土地養育了我們,是不求我們回報的父母。拆遷了,土地沒了,這一條條鄉路都不存在了,我們還有歸途嗎?
拆遷安置項目里有一項非常人性化和有溫度的規定:房子拆遷了,土地征用了,但在我們這幾個村子的后面圈了一片地,用作墓地,每家每戶都可分得一塊。我想起:小山村前的山坡上,拱起一片一片的墓地,那是一個一個宗族的。墓地的墳頭都朝西南向,墳尾東北方,上一輩墳尾對著下一輩的墳頭,下一輩的墳尾挨著上一輩的墳頭,這樣一個抵著一個,叫“抵腳后跟。”意為后繼有人。其實,不管我承不承認,心里有沒有它,這里是他的根,也是我最后的歸宿之地。
有人說:“回鄉的路是艱難的,我們回不去了。” 我想:我們都是這方土地上長出來的,和地里的草木莊稼一樣。只要我們的祖先在,我們的根就在,回鄉的路就不會坎坷艱難,更不會遙遠。
如今,多少城市里的人,紛紛告別城里的蝸居,返回鄉下生活。這,到底是人們的觀念在進步,還是一種形勢的逼迫?想當年,我們歷經千辛萬苦,在那個本來不屬于自己的城市安下了屬于自己的家。如今,我們在城市里住得安生了,卻又紛紛想著逃離那個光怪陸離的所謂家園,這又當如何解釋呢?難道,僅僅“鄉愁”兩個字,真的有那么大的魔力嗎?
我想不通。想不通的事,不想了。隨它去吧。在我們這一輩子,且隨它去。好在鄉村還在,鄉路還在。
鄉路,多么美好與溫馨。讓我們的心胸更豁達寬廣,歸途,可以歸家園之途,也可以歸家國之途!
故鄉雖然好,他鄉情亦濃。宋代詞人蘇軾《定風波》詞:“此心安處是吾鄉。”情如此,勢如此,還需要那么糾結嗎?
鄉路也好,歸途也罷,只要還有凝望的方向,回歸的目光就不會迷離,回歸的腳步就不會遲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