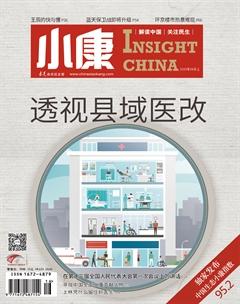王辰:既挺身而立,又俯下去
郭玲

“特別高興在近年最大的一輪圓月映照下站在這里,受到大家熱烈歡迎。”說話的是王辰——中國工程院副院長、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院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他的笑容中流露出些許疲憊。
這一天是2020年4月7日,這一年中最大的一輪“超級月亮”如約登場,為月光下的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增添了一份月圓人圓的美好。19點17分,載著中日友好醫院160余位國家援鄂醫療隊員的飛機抵達機場,首都機場以民航界最高禮儀“過水門”的方式迎接白衣戰士們回家,王辰就在這支隊伍當中。
此時,距離他奔赴武漢前線援鄂,已經66天。
迷霧下的決斷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場人類面對病毒的戰爭,疫情暴發后,來自全國各地的大量優秀醫護人員迅速集結、馳援武漢。2月1日,大年初八,王辰跟隨中日友好醫院援鄂醫療隊前往武漢,其身處武漢的66天,正是這場戰爭中最艱苦的時段。
果敢決斷,敢說真話,是戰士王辰在這場戰爭中給人們留下的印象。
2月5日晚上,央視主持人白巖松在《新聞1+1》中和王辰連線。當時,全國人民都在期待疫情拐點的到來,而王辰的回答卻異常清醒。“首先我們現在對疫情的底數不甚清楚,如果不甚清楚,在判斷上的根據是不足的。現在在外頭有多少沒有隔離的病人?這種社區和家庭的傳染還是有相當的嚴重性的。在這種情況下,這個拐點不是人為能夠預期的。”
王辰的回答得到了網友們的點贊,有人評價“久違的力量正在刺破疫情的迷霧”。
面對不清楚底數的疫情和超負荷運轉的醫院,王辰提出開建“方艙醫院”,實現“應收盡收,應收早收”。有人擔心會發生交叉感染,王辰扛下所有壓力,提出不僅要建“方艙醫院”,還要快速建。
在人類抗擊傳染病歷史上,“方艙醫院”尚無先例,但后來的事實證明,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這場戰爭中,“方艙醫院”成為了重要武器。
其實,這并不是王辰第一次“打仗”。2003年“非典”來襲,王辰臨危受命,擔任了北京防治“非典”專家組組長。憑借多年的經驗,王辰意識到“這個病,很危險”,他立刻決定建立隔離病房,帶領同事用了48小時,在朝陽婦幼保健院搭起了高標準的“非典隔離病房”,而這個病房,為后續隔離病房的搭建提供了參考,發揮了極大的作用。那一次的反應,和這次建立“方艙醫院”一樣快。
能夠一次次做出決斷性和前瞻性的判斷,背后依靠的是實力。王辰是國內首屈一指的呼吸病學與危重癥醫學專家,與鐘南山院士齊名。2008年,人民衛生出版社發行了一本研究生教材,名為《呼吸內科學》。封面上主編一欄只有兩個名字:鐘南山、王辰。2018年,復旦公布中國醫院排行榜,其中呼吸科全國排名第一的是鐘南山所在的醫院,緊跟其后的第二名便是王辰所領導的中日友好醫院。有人說,“兩位業界泰斗,醫術高,醫德更是高山仰止,更難得的是,他們都敢說真話。”
王辰說真話,源自底氣,也源自一以貫之的習慣,他深知“做學問,要用心、嚴謹、領會”。王辰出生在山東高校大院,父母都是教師。從小生長在學術氛圍濃厚的環境中,讓他對“做學問”這件事耳濡目染。在他的記憶中,凌晨兩三點起夜時,經常發現父母還在臺燈下備課,讓他意識到,讀書、做學問是絲毫不能怠慢的事。上小學時,他有一次求教鄰居、蒙古史學家賈敬顏先生一個詞語的含義,賈先生翻遍自家書堆和圖書館都沒找到確切答案,他找到王辰,給了一個他的“假說”,但卻強調,“這只是我的猜想,并未找到嚴格根據,以后若找到,一定再告訴你。”從此,王辰知道,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不是什么都可以隨便說說。
3月10日,武漢所有“方艙醫院”休艙。在很多專家撤離武漢時,王辰卻選擇了堅守,并投身到救治一線。武漢中心醫院染病的易凡、胡衛峰兩位醫生在命懸一線的時刻,王辰又一次站了出來,提出“更換ECMO導管”的治療方案,讓治療向著好的方向發展。“我們大夫,特別是懂ECMO的大夫,知道中間有多大的風險、多大的困難……這不是件容易事,必須要有擔當,王辰院士就很有擔當,他說,咬咬牙,再難我們也要換導管。”兩位醫生的同事、武漢中心醫院醫生楊軍輝非常佩服王辰的擔當。
“4+4”改革,要快還是慢?
北京市東城區東單,繁華鬧市中有一隅古老的綠瓦青墻矗立其間,它就是已經走過一個世紀的中國現代醫學搖籃——北京協和醫學院。
“協和的每個角落都有深厚的歷史沉淀,閃爍著精神光芒。”王辰如此形容自己心中的這座“中國宮殿里的西方醫學殿堂”:一號樓是協和醫學院的靈魂和精神依附地,泰戈爾曾在此慶祝生日,孫中山先生的靈柩曾在這里停放;二號樓是協和的解剖樓,曾是步達生研究北京猿人頭蓋骨的地方;三號樓是協和的生化樓,吳憲先生的蛋白質變性學說在這里醞釀產生;四號樓是協和的生理和藥理樓,林可勝、陳克恢昔日就在這里工作……
2018年1月,任職中日友好醫院院長的王辰,正式調職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擔任校長、黨委常委,成為這座醫學殿堂新的掌舵人。
很多師生對于這位新校長的認識,是從那一年的兩場典禮開始的。
2018年8月30日,北京協和醫學院的開學典禮在秋雨中如期舉行,整整一個多小時,王辰全程筆直挺立,西服被淋得泛水光,頭發被淋濕貼在一起,師生們一起站在雨中,完成了這次特殊的開學典禮。
“我很心疼你們淋雨,但是我更在意的是你們所應該持有的精神……今天,協和的老師和同學們迎雨而立,這是協和百年精神的寫照,全體師生,要以這種精神投身事業,完成學業。”王辰雨中的致辭,帶給師生們深思與感動,亦如一個月前他在畢業典禮上的那段話:“今天是一個炎熱的日子,已經入伏了,大家穿著厚重的學位服,很多同學把帽子摘下來了,當做扇子。但我所希望的協和學生,應當是哪怕下著瓢潑大雨,也是要穿著學位服挺身而立的人。炎熱和大雨就是現實的條件,而你們穿著學位服挺身而立,就是你們作為知識分子的信仰和你們所崇仰的精神體現。”
挺身而立,這就是王辰心中協和精神的象征。經歷了兩次典禮,老師們評價道:感覺協和的精神又回來了。
王辰帶給協和的,不僅僅是精神的回歸,更有教育的突破。2018年7月,北京協和醫學院正式對外發布招生簡章,開啟“4+4”學制臨床醫學教育,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
1917年以來,北京協和醫學院一直采用八年制教育模式,即一名高中畢業生步入大學之后,要先進行醫預科的學習,再經過醫學專業系統學習,前后經過8年的學習,最終被授予醫學博士專業學位。而“4+4”教育模式,是指任何本科專業背景的學生,滿足一定的醫預科基本條件之后,都可以報考醫學院。
“從天下大學招生”,上任伊始,王辰就開始了他的突破,他要真正把醫學的精英教育轉化成為現實,“協和是精英教育里更精英的教育。健康和生命是人類的終極利益,醫生照護的是這個終極利益,因此容不得這批人素養不高,容不得這批人不夠聰明、不夠智慧,容不得這批人品德不夠高尚”。
那段時間,王辰帶著團隊奔走在教育部、衛健委等部門,就是為了盡快落實“4+4”的改革。有人勸他說,可以再等等,沒有必要剛一上任就干這件事。王辰的回答卻是,協和一定要為天下先,開風氣先。“為什么要這么快?我感覺到不能再拖了,因為國際上的醫學教育,已經遠遠地走在前面了。”
作為師者,王辰對于醫學院的教育有著深深的思考。他主張協和學生的產出不在畢業時,而在未來,對于他們的培養方式是檀木式,檀木長得很慢,但木質很堅實,未來是成材的。
愛其所愛,懼其所懼
有時治愈,常常幫助,總是安慰,這是長眠在紐約東北部的撒拉納克湖畔的特魯多醫生的墓志銘,曾經被無數的醫者所引用與推崇。王辰對此有過類似的闡釋,“自古以來,都說醫生看病有三個法寶,這三個法寶是什么呢?第一個是語言,第二個是藥物,第三個是刀械,包括手術刀和器械。”在他看來,醫生擔負著維護健康與生命的職責,對醫生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其科學與人文素養都必須能夠滿足對人進行身心照護的要求。
“醫患關系是人間最美好的關系。”王辰多次表達過這樣的觀點,也曾在自己的從醫生涯中有過深刻的體會。1988年,在他還是住院總醫師的時候,到急診室去會診一個十幾歲的年輕民工。當時,患者發燒、休克,CT檢查發現是心影后肺炎所引起的感染中毒性休克,這樣嚴重休克的病人必須收到搶救室里進行重癥監護治療,但是民工的老板已經跑掉了,沒人交押金。盡管知道可能面臨的問題,王辰還是決定簽字、收住院。經過監護治療,病人一天比一天好,到了第七天的時候,病人跑了。“我簽的字,就意味著700塊錢由我來承擔。當時獎金我記得才幾十塊錢,但沒辦法,慢慢還唄,畢竟活了一條命最重要。”
王辰沒有想到,十天后,醫院來了一個河南農村的老漢,正是那個年輕人的父親,老人變賣了家里很多東西,帶來1000元錢,還道歉說“孩子不懂事,大夫給治好病還跑了”。當時王辰心里非常感動,他覺得這世界上自有公道人心,“醫生真不必想那么多功利的東西,只要你心存善念,會得到社會的理解和回報。醫患關系到什么時候都是最值得珍惜的,應當充滿著善良互動的關系”。
醫生最重要的素質是有悲憫之心,有悲憫心、有同情心、有同理心的人才能夠做醫生。這是王辰對醫生素質的理解,也是對自己的要求。
“對醫生來講,既對品德有很高尚的要求,又要很具體于現實,膿、血液、糞便,這些常人看起來不屑、不愿意接觸的東西,醫生都要接觸。所以醫生既在情智上、在思想上必須是一個很高尚的人,同時又能夠俯下身去,接觸一切苦難和面對一切的骯臟、一切的腐朽、一切的痛苦。”在王辰的職業生涯中,他始終堅持到臨床去。不管是被任命為中日友好醫院院長,還是履新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院校長,他的這一習慣從未改變。
王辰曾經和朋友探討過,“喜怒憂思悲恐驚”,人類最本元的情感是什么?他覺得,只有愛和怕才是最本元的情感,其他情感都源于愛和怕,善良也是源于愛和怕。“人生要真正愛其所愛,如親人、事業、民族、國家;懼其所懼,要對違法、貪婪、不健康生活方式深存戒懼之心。作為醫生和護士,更要知道生活中、執業中何為所愛所懼,還要將這兩種最本元的情感傳遞給患者,讓患者能夠愛之所愛,懼之所懼,趨利避害,維護好身心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