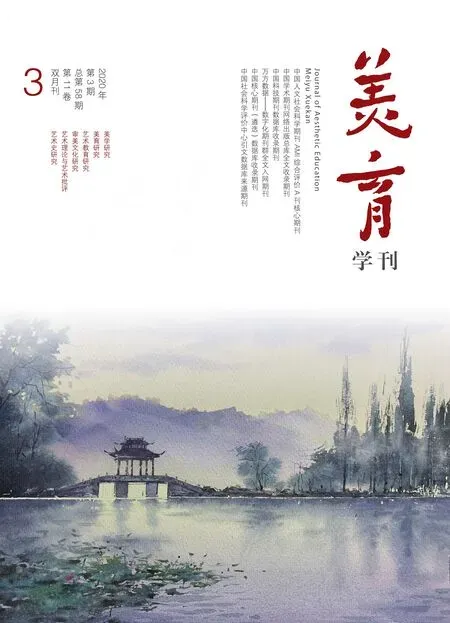從田野到課堂
——甘青藏區民藝田野考察方法與教學研究
王 東
(甘肅民族師范學院美術系,甘肅 合作 747000)
田野考察是人類學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始于19世紀末,至今已有100多年歷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學習田野工作的方法,對于民間工藝田野考察的整體規劃和實踐有一定的參考和實踐指導意義,對明確民間工藝田野考察的對象、目的和意義很有幫助。田野考察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在不同學科研究背景之下采用的方法會有不同,對考察對象的考察重點也有所不同。
對于民間工藝相關的田野考察,不同學科研究視角會產生不同的研究成果。實際上,田野考察在對我國的民間工藝的研究中并非是從現在才開始的,甚至可以上溯到春秋戰國時期成書的《考工記》和明代宋應星所著《天工開物》,后者就是作者在趕考沿途見聞的考察記錄。我國現代學科背景下的田野考察,早在20世紀初就已經應用于民俗文化、傳統工藝的調查研究工作,視角多從文化人類學和美術學學科背景考察居多。關于民間工藝的概念描述也從工藝美術、實用美術到藝術設計幾經變化,仍有歧義。這里采用“民藝”來描述所探討的民間工藝類型,民藝學的發展就是建立在田野工作基礎之上的。前人經驗積累為我們討論田野考察研究方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一、民藝田野考察的對象與法則
“民藝”一詞,源于日本。近代日本在面臨現代化的轉型中,隨著歐美文化的傳入,從歐洲傳入的機械工業生產把日本的傳統工藝產業不斷趕到角落中,使其走上從沒落到絕嗣之路。被稱為日本“民藝之父”的柳宗悅(1889—1964),在1925年討論日本的民俗工藝時,率先創造并使用了“民俗工藝”的簡稱“民藝”這一新詞。[1]在柳宗悅的論述中,把“民藝”所研究對象的特征主要概括為:民眾的工藝(手工藝);實用的工藝;無名工匠所為;作為實用品,生產在長期的生活經驗中,不斷得到發展創造;由于就地取材,因而地方的風土特色濃郁;手工制作完成,可大量生產,較為廉價;富有功能性健康的美。民藝學便是以此為內容中心來論述美的學問。
民藝學視角下對傳統民間工藝田野考察的方法,在文化人類學、美術學或民俗學視角下的田野考察基礎上,突出類民藝學考察的特點。首先,考察對象是以民藝作品——“物”為主體;其次,理念中包含有民生和民主的思想和價值取向;另外,注重反思傳統工藝在當下現實的意義,通過從文化和經濟兩個維度考察工藝對人和社會的影響,在傳統中尋求符合時代的新工藝傳統。
柳宗悅對于民藝的理念,成為此后民藝學理論的基礎,繼而發起了一直延續至今對日本設計影響深遠的民藝運動。柳宗悅于1916年曾到朝鮮和中國進行過為期兩個月的考察之旅,他對民藝的研究和理論經過其子柳宗理的發展和實踐,影響很大。臺灣在20世紀70年代同樣涌現了大批的民藝研究學者,民藝學者受日本民藝運動影響做出的應對,其中最為我們熟知的就是《漢聲》雜志的創辦人黃永松。
《漢聲》1971年創刊時是以英文版ECHOMagazine面貌出現,1978年中文版創刊。早先ECHO工作宗旨在于“東西交流”,是空間橫向坐標,到了中文版創刊,則以“銜接古今”的時間縱坐標為主,致力于銜接傳統與現代。1988年后更為漢聲民俗田野工作拓展了無比遼闊的空間。[2]漢聲雜志社策劃出版的《戲出年畫》《剪花娘子庫淑蘭》《侗族服飾藝術探秘》《華縣皮影》《蠟染》《夾纈》《黃河十四走》等多部關于海峽兩岸民間工藝文化的精品出版物,為我們對傳統民間工藝文化的研究、保存、繼承、傳播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也為我們對民藝的研究積累了豐富的可借鑒學習的經驗。
我們在進行甘青藏區民間工藝的田野考察時,借鑒了漢聲團隊訂定的“體、用、造、化”田野工作“考工法則”,即包括四法、十六則,共二十字的“考工四法十六則”口訣。“體”指調查主題對象的外觀形態積累,四項細則包括“形制、材質、色彩、紋飾”。“用”指調查主題對象的功能,四項細則包括“使用之人、地點、事件、用法”。“造”指調查主題對象和生產過程,四項細則包括“材料、工具、工序、要訣”。“化”指調查主題對象的文化淵源和流傳背景,四項細則包括“歷史、地理、人、演變”。[2]漢聲之所以在傳統文化田野考察中碩果累累,和他們嚴謹的治學態度和田野考察的工作方法密不可分。
二、民藝田野考察的內容與方法——以青海湟中敲銅工藝田野考察為例
我們對于甘青藏區的工藝考察,起初采用傳統文化人類學“實地觀察”“深度訪談”的田野工作方法,收集了牛羊毛編織、木雕、泥塑等數種甘南藏區手工藝的圖片資料和訪談記錄。但在做后期資料梳理時發現,我們的調研基本是一種浮光掠影、純粹審美、甚至是獵奇式的民俗文化及民間技藝報道,缺少一以貫之的田野調查的核心學科理念和有效的調研工作方法論,使得調研結果不能繼續深入并為研究和教學實踐提供有意義的指導。
在對青海省湟中縣的敲銅工藝進行調研時,我們參考了漢聲團隊的“考工法則”,開始嘗試更細密、更有效的方式來進行民間工藝的調查和記錄。對調研內容和目的進行了民藝學和設計學方向的明確,以“物”為考察核心,由“物”及“人”、由“物”及“道”的總體思路,采用了更細致的田野工作方法:第一,直接觀察;第二,深度訪談;第三,器物考量;第四,影像采集;第五,文脈溯源;第六,造物美學;第七,現狀反思。具體考察內容如下:
(一)直接觀察:現狀與環境
直接觀察敲銅工藝存在的自然和社會環境,直觀感受從業人員的生存現狀。通過直接觀察我們看到一個直觀的環境印象:藏族同胞對銅制品有著特殊的喜好,在藏區我們可以見到一些經營民族用品的店鋪,里面有各種新舊銅制物件,有佛像、法器等宗教圣物和用品,有奶茶壺、酒壺等日常生活用具,還有體量較大的建筑物的構件及裝飾等。
這些隨處可見的銅質物件印證了銅加工工藝在藏區傳統生活中曾經扮演過重要的角色,并且在現在甘青藏區民眾生活中也有延續。在考察地青海省湟中縣塔爾寺西南側的小巷時,可以看到街道兩邊全是做銅活的作坊和店鋪。整條街巷都沉浸在作坊匠人們敲制金屬的嘈雜聲中,街兩邊擺滿了打制好的各種銅器(圖1)。

圖1 青海湟中縣商業街上擺放的各類銅件
(二)深度訪談:人物與器物
“人”是民藝行為活動的主體,只有通過對“人”的考察,才能理解“物”的意義。訪談要選擇合適的訪談對象,在準備階段需有一份訪談提綱,進行過程中需要隨機應變,消除被訪談人的刻板影響,在自然聊天的過程中完成深度訪談。
我們的考察從圈發錄師傅的敲銅作坊開始(圖2)。通過訪談我們知道:圈師傅是藏族人,他是這條街上為數不多的藏族匠工。最先跟著他的哥哥做銅活,后來自己獨立開了作坊,在這條街上已經工作了20多年。青海湟中的敲銅小作坊大概有兩三百家,僅在“商業街”上就有一百多家,已經形成一定的規模和市場影響力。據圈師傅說當地敲銅工藝應該有一兩百年歷史。大約20世紀80年代開始,藏區隨著各地開始整修新建寺院恢復信仰傳統,這條街的生意逐漸好轉起來,形成現在這種規模和景象,并且由于藏區特殊的工藝生產需求,產業鏈基本被保留了下來。

圖2 敲銅匠人圈發錄在工作
(三)器物考量:材料、工具與制作
對“物”的考察是民藝田野考察的核心,所有的考察項目都圍繞器物展開,內容豐富、工作量大。在對器物的考量中主要從材料、工具和制作工序入手。考察材料的來源構成和工具的使用考察,包含有對地方物產和地方性知識的研究。具體考察如下:
1.材料:考察材料的來源、種類、性能等。湟中敲銅等大件器具的加工中多取紫銅(純銅)和黃銅(銅鋅合金)。在沒有加工好的成品銅皮出現之前,匠人們要將銅塊打制成薄厚適宜的銅皮再做加工。前些年匠人們選用甘肅白銀產的銅皮,現在主要用河南洛陽產的銅皮和銅錠。在選擇銅原料時,好的工匠一看色澤就可以判斷質量的好壞。
在敲制有浮雕效果的立體造型貨紋樣時,需要在工作案桌上灌涂一種黑色的“膠”作為襯墊,是工匠們自己配制的一種膠狀合成物。主要成分是草灰或木灰,植物或動物油,還有松膠三種原料。現在因為草灰得之不易,很多作坊也用寺院的香灰替代。油是用菜籽油最好,也可以是牛羊等動物的油脂,三種材料按一定比例配方熬制后就形成類似瀝青的膠狀物。
2.工具:工具蘊含著民間的工匠智慧。考察工具種類、功能等,必要時應該做工具的詳細測量。湟中敲銅所使用的手工工具主要有三類。第一類是錘子:有各種型號大小和造型,常用的錘子有十多種,除金屬錘外,還有木質和橡膠錘,分別用于不同器型的制作。第二類是鏨子:主要用來鏨刻紋樣,多是師傅們自己打制或訂做。鏨子的主要區別在前端刃部的樣式上,常用的鏨子有近二十種(圖3)。第三類工具,師傅們把它們叫做“鐵棒”:是一種一端帶有各種造型的鐵棍,主要固定在臺虎鉗或工作案上做支撐,用來敲制不同造型。

圖3 部分敲銅工具鏨子
3.制作:主要考察制作工序及工藝技法。湟中敲銅工藝的工序以常見的裝飾有藏八寶紋樣的經筒為例,主要經過以下幾道工序:選料下料;起線描稿;涂“膠”;敲大樣;退火;細節敲制;組裝完成。在制作寺院經堂頂部的雙鹿法輪,經筒,飛檐檐角的神獸“曲森”、蓮花座、大鵬鳥甚至高達數米的佛像這類圓雕效果的作品時,就會用到不同造型的“鐵棒”或木頭樁(臺)。采用更有技術難度的冷錘鍛打的錘起工藝,先敲制各個局部造型,再焊接拼裝完成整體造型的塑造,最后用酸清洗被氧化的表面或者貼金箔。
(四)素材采集:實物與影像
收集素材包括民藝作品實物或者照片影像資料。記錄的方式除了文字記錄和圖片,錄影是民藝田野考察過程最具實效性的和現場感的方式,是在田野現場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在對湟中敲銅的影像記錄中,記錄了匠工們一天的生活。以對圈師傅的訪談為主線,記錄了商業街的整體面貌,同時試圖以不同景別盡可能多地捕捉與這種工藝相關的信息。將考察的影像素材做成紀錄短片,作為此次田野考察資料很重要的部分,是后期研究最直觀生動的影像資料。
(五)文脈溯源:過去與現狀
對傳統工藝文脈的溯源是對考察對象做更深入的研究工作,主要包括對師承關系的追溯,對文化內在影響的探尋,對工藝演變歷史的考證。一部分是要在田野工作的現場進行,發現線索、收集實物和數據、現場訪問,還有很多需要在后期進行史料的考證和分析。
公元前2000年左右我國進入青銅時代,目前越來越多材料證明,中國境內的早期銅器主要集中發現在西北地區,而且在使用文化上草原地帶的關系超過中原地區的關系[3]。因此,銅的冶煉技術和加工工藝在東傳的過程中,甘青藏區的敲銅工藝無論后來在與各民族文化交融和技術更迭中如何演化,在工藝流傳淵源和文化含義上應該是一種有根可尋的物質文化形態。
湟中敲銅這種工藝形式之所以延續下來,和藏地宗教信仰的背景有重要關系,并且在造物品類上和美學追求上深刻影響著工藝的制作和傳播。在藏區民間流傳下來的其他傳統手工藝中也有類似的情況,制作者的藏傳佛教信仰背景也是人們認可和接受作品的重要參考條件。另外,師徒協作的作坊生產方式也為敲銅工藝提供了技藝傳承的空間保障。在湟中縣商業街,這些建于20世紀80年代的二層磚混建筑提供了作坊的空間條件,使作坊既是工藝知識傳授的地方也是生產工作的工廠,還是作坊成員情感聯結的場所。
(六)造物美學:功能與形式
民藝美的問題離開物質形式的“物”便不復存在,對于工藝品的考察,多從造型美、材質美、工藝美為要點。倘若要以民藝為主題,就要采用新的美學立場,這在民藝學中是明確的,柳宗悅稱為“民藝美學”。民藝的美就是實用之美、無名之美、平常之美。民藝美學考察是以作品功能與形式為中心的,由此而進行的研究,可以在發現美的法則上有所建樹。
從造物美學的角度對湟中敲銅的考察,我們沒有把焦點放在器物的裝飾紋飾上,而是器物功能和呈現形式的內在因素上。因為我們發現,宗教建筑構建是湟中敲銅主要的制作類型,裝飾就是功能的一部分。而在實用器物的制作中,比如銅火鍋、銅壺以及其他生活用品的制作,功能實用是制作過程中首要考量的,表面裝飾是一種刻意表達文化符號和迎合消費者的舉動,并不是傳統器物之美的終極追求。柳宗悅在作為日本民藝運動宣言的《日本民藝美術館設立意趣書》中寫道:若想追求自然、樸素又充滿活力的美,必須求諸民藝之世界。經過長期的摸索,我們發現最原始的美就存在于民藝之中。[2]
(七)現狀反思:問題與應對
如何讓藏區傳統工藝文化在新的時代傳承下去,更新為活態的、符合現代生活的工藝文化生態,是我們考察反思的主要問題。通過對青海湟中敲銅工藝的考察我們看到,藏區傳統手工藝在新時代面臨器物功能向現代生活轉變、機器生產與手工制作的競爭等諸多困境。湟中敲銅工藝在現實中遇到不同層面的諸多矛盾和困難,最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經濟利益與文化傳承的矛盾。
在市場和傳播中不能平衡傳統民間工藝的商品屬性和文化屬性。博物館化的保護不能發揮民間工藝具有的商品屬性,而為了追求經濟利益,降低工藝質量要求,盲目批量生產又喪失了傳統工藝的文化內涵,難以喚起當代人審美情感,淪為低劣的旅游商品。在經濟利益和文化價值兩者之間實現平衡,應該從“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機制構建探索創新模式,也需要手工藝人保持工匠精神,制作生產出真正具有市場和文化價值的作品。
在田野考察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像轉經筒、瑪尼石刻這種蘊含濃厚宗教信仰背景的工藝形式,其功能也在發生變化。在藏區一些著名的旅游景區有售賣便于攜帶的轉經筒、瑪尼石刻紀念品,供游客作為旅游玩賞,這是傳統器物功能在當代的一種變遷。正如美國人類學家弗朗茨博厄斯在《人類學與現代生活》一書中指出:文化背景根本不同的人傳述著相似的神話,其意義依文化興趣而定。對于一個部落是神圣的神話,在另一個部落看來可能完全是為了娛樂。[4]
第二,手工制作與機器生產的競爭。
傳統工藝重視手工技藝,手工匠人掌握著設計和加工的秘訣,他們全神貫注于一個事物,在自己制造的物件上花費大量的勞動時間,作品的價值不僅體現在匠人的精湛手工技藝中,還在于它凝聚著匠人的勞作毅力。這些在農業文明時代傳承下來的手工技藝和生產方式,無一例外地在技術革命浪潮下,受到機器大規模工業生產的挑戰。
2016年第四次到湟中“商業街”考察時我們看到,藏區所需的傳統日常生活銅制用品制作越來越少,也許它們已經被云南或更遠地方來的加工更精致的物品所淘汰,或者被現代工廠生產的廉價塑料商品替代。就連湟中敲銅作坊現在主要制作的這些“大件”——建筑裝飾構建,在塔爾寺附近的一些店鋪已經在售賣一些機器沖壓批量生產的產品。它們丑陋呆板卻價格低廉,在這個崇尚速度和效益的時代,匠工們一錘一鑿的手工生產方式顯得有點笨拙而不合時宜。
三、民藝在高校中的教學實踐
對民間工藝的研究高校學者始終是主要群體之一,將傳統民間工藝納入高校教學體系也已有半個多世紀的探索和實踐。1956年龐熏琹主持創辦的中央工藝美術學院,20世紀80年代中央美術學院建立的民間美術系,是傳統工藝進入高校教學的先驅者。此后中央美術學院民間美術系的更名,中央工藝美術學院與清華大學的合并,到中國美術學院手工藝學院和民藝博物館的建立,都是民藝在高校教學和研究的標志性事件,而伴隨著這些事件引起的學術探討,也影響著地方院校對于民間工藝相關的教學研究。甘肅民族師范學院是一所地處甘南藏區的民族院校,近幾年來也在做適合自身現實的學科建設和民藝教學實踐,以下是民藝從田野考察到課堂教學相關的探討。
(一)從田野到課堂的課程體系
民藝在高校的傳承需要納入高校課程體系中,將田野考察作為夯實學科自身的基礎。若缺少基礎性的田野工作,關于民藝的課堂教學將無法與傳統銜接,不能實現民間工藝在高校的教學意義和傳承目的。以田野考察為基礎的課程體系,是民藝納入高校相關學科教學的基礎之基礎。民藝進入高校課堂的目的,其實還是老命題:如何讓傳統工藝在新時代活態地傳承?從田野工作到課堂教學需要圍繞這個核心命題構建課程體系。
1.田野考察作為基礎實踐課程,每次的考察目標和任務要明確,采用科學嚴謹的考察方法,避免走馬觀花式的散漫民俗采風。對青海湟中敲銅的田野考察是實訓工作室的實踐課題,我們先后十多次進行實地考察,并且和當地藝人形成良好合作關系,為回到課堂做繼續深入教學研究打好了基礎。
2.設計與民藝的融合培養模式
設計學要回望傳統,民藝是繞不過去的大山;而民藝要展望未來,設計藝術是連接貫通的必由之路。我們根據設計學科文理兼容的特點和專業方向在基礎教學中的共通性,將民間工藝納入設計學科體系,以培養從事工藝設計創新人才為目標。在課程中設置了“民藝田野考察”“傳統工藝與設計”“民藝再生設計”“綜合設計”等課程,與學科原有專業課程形成互補融合的課程體系。
(二)由技入道的教學目標
人才培養以提升人的綜合能力為目標,以職業技能訓練為手段,遵循“由技入道”的教學理念。以綜合能力訓練為主的授課,突破課堂講授的空間限制,以課程老師為主導,在田野考察中學習,向民間匠工學習。在反復動手操作中掌握工藝知識,制作技術,從而達到在對民族工藝技術熟練掌握的同時,深刻理解工藝文化意蘊,提高學生對文化傳統的認知,提升工藝設計創新能力。在解決傳授技術的過程中,將民間藝人請入課堂是慣常采用的授課方式,這似乎和20世紀初包豪斯學校的“工藝大師”配合教學的模式相似,也有區別。這里手工技藝的學習目標不僅僅是“技”本身,由技藝學習進入“道”和“美”的領悟是更高的追求。
在新的時代,手工制作與機器生產之間存在的并非只是競爭,更多的應該是合作,現代材料運用、加工工具、設計工具的使用也是重要的學習內容。民藝的美顯現在所用材料上、造型上、技藝上,這一切都被制作者心手合一的專注勞作凝結在器物中,所謂“匠心”是也。好的匠人在手工制作的部分,手工技藝所表現出來的獨特藝術品位和個性價值并沒有失去,塑造現代工匠精神是高校民藝教學的目標之一。在教學和生產中保持匠心才是育人和制作優秀作品的關鍵。
(三)現實關懷的實訓方案
民藝就是生活,民藝與民生息息相關,民藝從田野到課堂,最后還是要回到生活現實。民藝的學習不僅是“技”與“道”的傳承,還要實現“經濟”利益的兌換和市場空間的拓展。“因此,我們應把民藝看作一個系統工程,不僅是學術的也是生活的;不僅是經濟的也是文化的;不僅是鄉村的也是城市的;不僅是過去的也是未來的”。[5]
民藝的實訓教學方案注重對現實的關懷,在文化傳承的同時,探索解決傳統工藝向現代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轉變的路徑。在實訓方案中整理學習當地優秀民間工藝,對一些工藝類型進行再設計,從而探索與市場對接的模式。由此,我們于2014年創建了名為“自習”的安多藏區文創品牌孵化計劃,試圖使課堂教學重返“田野”。其中,作為對湟中敲銅工藝田野考察的進一步探討,我們嘗試與敲銅匠人共同制作一些器物,目前我們和匠人們合作已經完成第一季系列產品的研發(圖4)。我們期待這樣的合作,會為湟中敲銅這種工藝帶去一些新制作形式,也是嘗試甘青藏區民藝調研和教學的一種新模式。

圖4 部分與匠人合作的“自習”項目作品在中國(深圳)國際文博會現場
四、結語
關于民藝,似乎人人都在肯定其價值,但對民藝的認識卻更多停留在感性的階段,如果只是不斷地在感性基礎上重復探討,無益于民藝在當代的發展,學術研究也是書閣中的惋嘆。當我們在討論民藝、傳統工藝美術或設計傳統的研究和教學等方面的問題時,民藝學科背景的民間工藝的田野考察應該被重新認識。民藝田野考察要制訂科學嚴謹的考察方法,只有進行深入的田野考察,才能為民藝進入高校提供后續研究資源和創新基礎,實現從田野到課堂的有效連接。
2018年12月在去湟中的調研中看到,因為環保和旅游環境治理的原因,湟中縣政府決定要將整條街的銅器加工作坊搬遷,全部改為商業店鋪,圈師傅和他的同伴們正在為尋找新的作坊而奔忙。因為當地民間工藝的現實生存生態正在急劇衰落,我們意識到必須盡快、全面翔實地對甘青藏區進行民藝田野調研,并在教學中開展新民藝的探索,以期教學研究成果能夠有效地驅動民藝的活態傳承。
中國的民間工藝與日本民藝在形態上有著許多相類似的地方,中國的民間工藝研究者和愛好者們的收集、整理、展覽、出版等工作有了近一個世紀的歷史,民藝進入高校教學也有長期的經驗和成果積累。從“田野”到“課堂”,通過民藝的更新,讓傳統民藝回歸生活,重返“田野”,這就需要從田野考察到課堂教學的系列工作入手,通過更多的人和社會組織合作努力,才能使優秀傳統民藝在當地文化和經濟生活中得到活態的傳承,實現傳統工藝的振興和“美之社會”[6]構建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