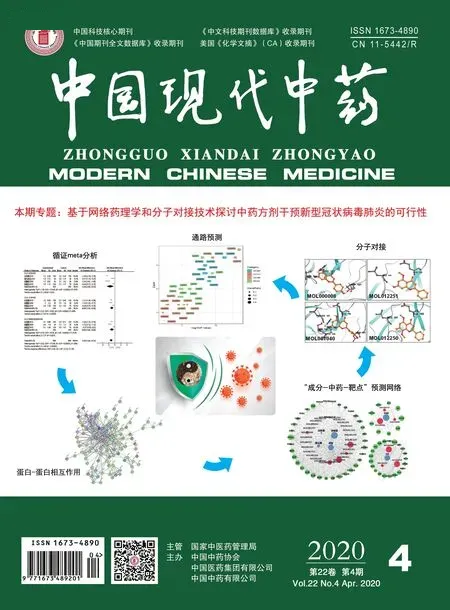基于網絡藥理學和分子對接分析探討消炎退熱合劑干預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可行性△
周瑞,劉妍如,王征,張軍武,李宏, 許洪波,何姬,張玉茹,唐志書*
1.陜西中醫藥大學 陜西中藥資源產業化省部共建協同創新中心/ 秦藥特色資源研究與開發國家重點實驗室(培育)/陜西省創新藥物研究中心,陜西 咸陽 712083; 2.陜西中醫藥大學 制藥廠/陜西省博士后創新基地,陜西 咸陽 712046
2019年12月開始,在我國湖北武漢及周邊城市發生了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或SARS-CoV-2)引起的急性肺炎。此次引起流行的病毒與2003年的SARS病毒相似,都屬于冠狀病毒科的β屬冠狀病毒,傳播快,人群普遍易感[1-2]。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輕度患者出現發熱、乏力、干咳等癥狀,嚴重者可出現呼吸困難、呼吸窘迫綜合征或膿毒癥休克等癥[3]。采用中西醫結合對癥治療已取得滿意的療效,特別是在減少輕癥轉化為重癥,減少重癥,病死率方面體現了明顯的優勢[5-6]。
中醫認為病毒導致的傳染病屬于“瘟疫”的范疇,中醫藥在我國治療各種疾病已有千年歷史,《溫病條辨》《傷寒論》《黃帝內經》等中醫典籍中也記載了大量對這類疾病的診療方法和處方。中醫認為新型冠狀病毒的病因為感受疫戾之氣[7],病位在肺,基本病機特點為“濕、熱、毒、瘀”。在防控緊迫的局勢下,從臨床現有療效確切的抗炎抗病毒中藥方劑中,尋找可以有效防治COVID-19的藥物是更快速、更安全、更有效的策略。消炎退熱合劑是陜西中醫藥大學制藥廠生產的1種中藥復方制劑,臨床針對病毒性感冒發熱、咳嗽等癥具有顯著療效。該復方由大青葉、蒲公英、紫花地丁、甘草4味中藥組成。方中君藥為大青葉和蒲公英,臣藥為紫花地丁,佐以甘草解毒調和諸藥,共同發揮清熱解毒之功效[8-11],其中大青葉、甘草和蒲公英在全國防治COVID-19的中藥方劑中出現頻次較高[12]。消炎退熱合劑全方重在圍繞熱毒而設,非常切合目前COVID-19的中醫病機。因此,本研究推測該復方可能通過抑制病毒復制、調節免疫,有效地阻斷病毒感染引起的炎癥風暴等,實現防治COVID-19。
近年來,網絡藥理和分子對接方法對于研究闡明中藥多成分、多靶點整體治療疾病的機制提供了很好的技術[13-15]。本研究擬通過網絡藥理學篩選出消炎退熱合劑的作用靶點,并進行聚類分析,預測消炎退熱合劑中具有抗病毒作用的核心活性化合物,進而運用分析軟件對藥材-化合物-靶點進行分子對接以及信號通路分析,并預測其治療COVID-19的作用機制,為消炎退熱合劑用于治療COVID-19提供理論參考。
1 方法
1.1 化學成分收集及篩選
借助中藥系統藥理學分析平臺(TCMSP)(http://tcmspw.com/)和Pubchem有機小分子生物活性數據庫(https://pubchem.ncbi.nlm.nih.gov/)檢索,以“大青葉Isatidis Folium”“蒲公英Taraxaci Herba”“紫花地丁Violae Herba”“甘草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為關鍵詞檢索消炎退熱合劑的化學成分。進一步以口服生物利用度(Oral Bioavailability,OB)≥30%或類藥性(Drug Likeness,DL)≥ 0.18作為條件,對化合物進行進一步篩選。
1.2 “化合物-疾病靶點”篩選
從TCMSP和Pubchem數據庫中搜索化合物對應的靶點,以UniProt數據庫(http://www.uniprot.org/uniprot/)對收集的靶點進行規范化和校正,得到成分相關的基因靶點。在MalaCards數據庫(https://www.malacards. org/)、TTD數據庫(Therapeutic Targets Database,http://bidd.nus.edu.sg/BIDD-Databases/TTD/TTD.asp)和OMIM數據庫(http://www.ncbi.nlm.nih.gov/omim)中輸入關鍵詞“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Respiratory Failure”,搜索已報道的與冠狀病毒感染肺炎和重癥呼吸道疾病相關的基因。剔除重復和假陽性基因后,整理得到與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相關的靶點基因。
1.3 “成分-疾病-靶點”網絡構建
將上述得到的化合物相關靶點和疾病相關靶點以Venn工具(2.1.0,https://bioinfogp.cnb.csic.es/tools/venny/)取靶點交集。將交集內靶點導入STRING 11.0數據庫(https://string-db.org/),以人類(Homosapiens)為種屬,查詢蛋白相互作用信息,從而構建PPI(Protein to Protein Interaction)網絡。整合PPI網絡的蛋白互作信息,“成分-疾病-靶點”及“中藥-成分”信息,將數據導入Cytoscape3.7.2(http://www.cytoscape.org/)軟件,構建“中藥-成分-疾病-靶點”預測網絡。以網絡的節點和邊線來描述化合物與中藥、疾病和靶點之間的關系,以Cytoscape的Network analysis插件分析并提取網絡節點和邊的特征。
1.4 生物過程注釋及靶點的通路分析
為了分析消炎退熱合劑的作用機制,采用R軟件包(3.6.2)的Cluster profiler包對交集靶點進行GO (Gene Ontology)生物信息學富集分析,用3個本體(Ontology)來描述基因靶點的分子功能(Molecular Function,MF)、所處的細胞位置(Cellular Component,CC)和參與的生物過程(Biological Process,BP)。然后以KEGG(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https://www.kegg.jp/)數據庫對靶點基因參與的主要生化代謝途徑進行富集和注釋,顯著性差異設定卡值為P<0.05,以R軟件包(3.6.2)的ggplot2包進行繪圖。最終整合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的病理學、分子生物學機制研究,對消炎退熱合劑的多成分、多靶點、多途徑協同抗病毒感染肺炎機制進行闡釋。
1.5 成分-靶點分子對接
采用ChemOffice軟件構建化合物的3D結構,保存為*mol2格式并使其能量最小化。從PDB數據(https://www.rcsb.org/)下載ACE2蛋白質(PDBID:2ajf)的3D結構*PDB格式,采用LibDock分子對接方法,其打分函數LibDockScore>100即表明受體與配體能較好地結合,其值越大則表明對接產生的復合物構象越穩定,配體與受體的親和作用越好。
2 結果
2.1 活性化合物的篩選
結合前期發表的消炎退熱合劑成分鑒定結果與TCMSP數據庫收載的組方中藥化學成分數據,基于樣本量、后續數據分析的復雜性以及研究價值的考慮,以OB≥30%或DL≥0.18作為進一步篩選條件,得到符合篩選標準的活性化合物117個。
2.2 化合物靶點與疾病靶點相互作用網絡
通過TCMSP平臺和Pubchem數據庫中找到消炎退熱合劑化學成分對應的靶點共498個,以Uniprot數據庫搜索校正后生成“成分-靶點”集合。從MalaCards數據庫、TTD數據庫和OMIM 數據庫中得到關于冠狀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和“Respiratory Failure”相關的靶點共計144個,生成“疾病-靶點”集合。將上述得到的“成分-靶點”和“疾病-靶點”集合以Venn工具 2.1.0取靶點交集,得到交集靶點27個(見圖1A)。將交集內靶點導入STRING 11.0,構建PPI(Protein to Protein Interaction)網絡(見圖1B)。
2.3 “成分-疾病-靶點”網絡
將篩選得到的27個靶點與4個中藥進行映射,篩選出18個核心化合物。來自大青葉的4個,蒲公英的1個,紫花地丁的7個,甘草的6個。將中藥、歸經及18個核心化學成分進行映射并生成關聯表,與PPI網絡生成的互作表導入Cytoscape3.7.2軟件構建消炎退熱合劑的“中藥-化合物-靶點”關聯網絡(見圖2)。

注:A. 消炎退熱合劑中化學成分靶點與疾病網絡交集;B. PPI網絡。圖1 消炎退熱合劑“化合物-疾病”靶點相互作用分析

注:藍色節點代表歸經;橘黃色節點代表中藥;綠色節點代表活性成分;紫粉色節點代表疾病靶點。圖2 消炎退熱合劑中“中藥-歸經-成分-靶點”網絡圖
用Cytoscape3.2.1軟件構建中藥-歸經-化合物-靶點網絡,圖中總共涉及125個節點,706個邊。不同顏色的圓點代表了消炎退熱合劑中中藥-歸經-成分-靶點網絡。圖中節點大小代表度數大小,度數越大,說明該節點在網絡中越重要,接近中心度越大,說明節點在網絡中越接近中性。分析4種中藥在網絡圖的連接度值可知,君藥大青葉度值最高為162,其次是蒲公英和甘草度值為72,紫花地丁度值為48。根據組成藥物的歸經信息分析,可以看到,網絡中連接度最大的是胃和心2個節點,連接度分別是45和41,其次是肝的連接度值為20,脾和肺的連接度值均是6。此結果表明消炎退熱合劑主要歸于胃和心,其次是肝、脾、肺。分析化學成分的連接度值,發現大青葉中的核心化合物靛藍(indigo),6-(3-氧代吲哚啉-2-亞基)吲哚[2,1-b]喹唑-12-酮{6-(3-oxoindolin-2-ylidene)indolo[2,1-b]quinazolin-12-one},以及蒲公英的化合物蒲公英萜酮(taraxerone),連接度值均是48,說明這3個化學成分很可能是消炎退熱合劑治療疾病的主要化學成分。其余化合物如鄰苯二甲酸二丁酯(DBP)、山柰酚、毛蕊異黃酮等連接度值是8,靛藍、十八碳二烯酸(ODD)、β-谷甾醇等連接度值是4。通過對靶點連接點度值分析得出,排名前5位的靶點分別是腎上腺素能受體β2抗體(ADRB2)(度值=57)、前列腺素過氧化物合酶1(PTGS1)(度值=39)、腫瘤壞死因子(TNF)(度值=25)、凝血酶原(F2)(度值=23)、腎素(REN)(度值=22)。我們同時發現,與COVID-19密切相關的靶點ACE2的連接度值為14。這結果說明消炎退熱合劑中化學成分可能不僅通過抗炎、調節免疫實現治療疾病,還可能直接作用于病毒受體,實現防治COVID-19的作用。此結果初步闡明“中藥-歸經-成分-靶點”的互作關系,揭示了消炎退熱合劑治療疾病的多靶點、多途徑屬性,其中大青葉節點度數較大,說明其君藥的用藥合理性。核心關鍵化合物為靛藍、γ-谷甾醇、β-谷甾醇、十八碳二烯酸等,主要歸經為胃、心經,表明消炎退熱合劑可能通過多成分、多途徑、多靶點協同發揮作用。
2.4 靶點通路分析
為了闡明消炎退熱合劑抗病毒感染肺炎作用的分子機制,將“成分-疾病”對應的27個靶點通過Cluster profiler進行GO富集分析和KEGG通路注釋,共富集到GO條目910,其中生物學過程(BP)867條(見圖3A),分子功能(CC)6條(見圖3B),細胞組成(MF)條目37條(見圖3C),分別占95%、0.6%、4%。富集到KEGG信號通路10條(見圖4),這些靶點主要分布于質膜外側(GO:0009897,external side of plasma membrane)、鈣離子通道電壓門控(GO:0005891,voltage-gated calcium channel complex)和鈣離子通道復合體(GO:0034704,calcium channel complex)。其分子功能主要與受體配體活性(GO:0048018,receptor ligand activity)、G蛋白耦聯受體結合(GO:0001664,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 binding)、細胞因子活性(GO:0005125,cytokine activity)有關。其生物過程(BP)主要涉及脂多糖反應(GO:0032496,response to lipopolysaccharide)、細菌來源分子效應(GO:0002237,response to molecule of bacterial origin)和血壓調控(GO:0008217,regulation of blood pressure)。這些靶點主要調控的代謝通路為cAMP信號通路(hsa04024,cAMP signaling pathway)、病毒蛋白與細胞因子受體間相互作用(hsa04061,Viral protein interaction with cytokine and cytokine receptor)、腫瘤壞死因子信號通路(hsa04668,TNF signaling pathway)、細胞因子相互作用受體通路(hsa04060,Cytokine-cytokine receptor interaction)、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hsa04614,Renin-angiotensin system)等。以上結果表明消炎退熱合劑中核心化合物可能通過干預ADRB2、PTGS1、TNF、F2、REN、ACE、ACE2等靶點來產生治療疾病的作用,并作用于cAMP通路、病毒蛋白與細胞因子相互作用、TNF信號通路等減輕病毒誘發的炎癥風暴損傷,并且有可能調控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直接作用于病毒與宿主的結合。

注:A.GO(BP)結果分析圖B:GO(CC)結果分析圖;C.GO(MF)結果分析圖。圖3 消炎退熱合劑作用靶點的GO富集分析圖

圖4 消炎退熱合劑KEGG富集分析圖
2.5 消炎退熱合劑中活性化合物與ACE2的分子對接結果分析
在網絡藥理學篩選的基礎上,我們進一步將篩選出消炎退熱合劑的18個核心化學成分與病毒的結合受體ACE2進行對接,通過DS篩選出消炎退熱合劑中潛在的核心治療疾病的化合物。采用LibDock分子對接方法,其打分函數LibDock Score是基于配體與受體對接時的親和力、相對能量和對接模式等進行綜合打分,打分值>100說明配體與受體具有很好的結合。消炎退熱合劑中18個核心化學成分與ACE2的對接打分結果見表1。

表1 消炎退熱合劑中核心化合物與ACE2的分子對接結果
從結果中可以看出,來自大青葉的活性化合物靛藍(107.163)、γ-谷甾醇(106.398)、β-谷甾醇(119.955),來自紫花地丁的活性化合物ODD(110.076)、亞油酸甲酯(107.172),及來自甘草的高麗槐素(104.029)的對接分值接近或高于與臨床推薦治療COIVD-19的藥物氯喹(105.656)。因此,通過分子對接技術,本文最終篩選出消炎退熱合劑中6個核心化合物可能是治療COCID-19的核心活性成分(見表1)。β-谷甾醇、ODD、靛藍及高麗槐素與ACE2蛋白相互作用的3D及2D示意圖見圖5。

注:A.β-谷甾醇與ACE2蛋白結合3D圖;B.β-谷甾醇與ACE2蛋白相互作用2D圖;C.ODD與ACE2蛋白結合3D圖;D.ODD與ACE2蛋白相互作用2D圖;E.靛藍與ACE2蛋白結合3D圖;F.靛藍與ACE2蛋白相互作用2D圖;G.高麗槐素與ACE2蛋白結合3D圖;H.高麗槐素與ACE2蛋白相互作用2D圖。圖5 消炎退熱合劑中核心成分與ACE2蛋白相互作用圖
3 討論
中醫在防治瘟疫方面療效獨特,以“辨證施治、扶正祛邪”為治療原則。中醫藥在出血熱、甲流等流行性傳染病防治中,均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2003年的SARS中,中醫藥治療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廣泛認可[16-17]。國際病毒分類委員會(ICTV)已將新型冠狀病毒正式命名為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2(SARS-CoV-2),表明SARS-CoV-2是SARS冠狀病毒(SARS-CoV)的近親。目前,中醫藥對于COVID-19的治療起到了重要作用。2020年2月14日,湖北省政府召開發布會,邀請中醫藥專家介紹中醫藥參與COVID-19疫情防控的有關情況。專家指出臨床采用中西醫聯合救治COVID-19能明顯提高救治的質量,減少死亡,減少重癥變成危重癥的發生率。
本研究提出的消炎退熱合劑是臨床用于抗流感病毒的中藥制劑。本研究用網絡藥理學方法系統地分析預測消炎退熱合劑對于COVID-19的潛在作用機制。首先通過數據庫查詢獲取消炎退熱合劑中各個中藥的活性成分及其作用靶點,然后構建中藥活性成分-靶點進行分析,找到消炎退熱合劑的117個活性成分及其對應的498個潛在作用靶點,同時與找到冠狀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和“Respiratory Failure”相關的144個靶點,與消炎退熱合劑活性成分-靶點網絡進行交集分析,初步篩選出消炎合劑核心活性成分包括γ-谷甾醇、β-谷甾醇、靛藍、ODD等18個,以及對應的疾病靶點27個。網絡藥理學結果分析消炎退熱合劑中藥物主要歸心、胃經,活性成分作用的主要疾病靶點可為幾個大類,一是與炎癥免疫相關的靶點有PTGS1、病毒蛋白與細胞因子受體相互作用、TNF;二是與病毒宿主結合復制相關的靶點有ACE、ACE2;三是與肺炎損傷機體的并發癥相關靶點如F2,F2是靜脈血栓形成的重要靶點,肺炎重癥患者長期臥床易患靜脈血栓,以上均是消炎退熱合劑核心成分γ-谷甾醇、β-谷甾醇以及靛藍的作用靶點。2019-nCoV感染導致強烈的免疫反應和炎癥風暴,此過程中大量細胞因子被激活[18]。已有研究發現炎癥因子風暴在新冠肺炎的病理進展中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因此,抑制細胞因子的產生也是治療COVID-19的關鍵目標[19-20]。KEGG分析得到與ADRB2、PTGS1、TNF、F2、REN、ACE、ACE2靶點相關且排名前6的通路,分別為炎癥細胞因子相關通路如病毒蛋白與細胞因子相互作用通路、TNF信號通路、細胞因子受體相互作用通路等,推測消炎退熱合劑可能通過調節這些信號通路起到抑制活化的細胞因子、緩和過激的免疫反應、消除炎癥的作用。文獻報道表明[21],ADRB2、REN、ACE、ACE2靶點和病毒蛋白細胞因子相互作用通路、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等在影響RNA病毒的結合、復制以及在治療肺炎的過程中起關鍵作用,說明利用網絡藥理學預測消炎退熱合劑治療COVID-19的潛在化學成分具有一定可靠性。cAMP通路是環核苷酸系統的一種,具有參與機體的發熱機制和炎癥的作用[22],消炎退熱合劑也可能通過調控cAMP信號實現散熱、退熱的作用。研究人員發現感染SARS-CoV的細胞中分離出腎素(REN)和血管緊張素II(Ang II),它們可以和SARS-CoV的刺突蛋白高效結合,且細胞ACE2的表達量與SARS-CoV的S 蛋白的易感性正相關[23]。腎素-血管緊張素II是2019-nCoV結合ACE2受體激活的經典途徑[24-25]。本研究發現消炎退熱合劑的活性成分不僅對ACE2的靶點有作用,且可以調節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信號通路,說明該復方可能含有直接抑制病毒與宿主結合的活性成分,網絡藥理學的結果預測消炎退熱合劑中潛在的治療病毒感染肺炎的多成分、多靶點的分子機制。
2013年Nature報道[26],冠狀病毒的刺突蛋白三聚體先與ACE2的細胞外催化結構域的“疏水口袋”結合,繼而細胞發揮內吞作用,病毒包膜與細胞膜融合,最終進入宿主細胞。研究發現[27],2019-nCoV中病毒感染的途徑也是通過其表達的S蛋白與ACE2的結合,導致病毒侵入機體而致病。本研究通過網絡藥理學篩選出消炎退熱合劑中靛藍、β-谷甾醇、γ-谷甾醇、ODD等18個核心化學成分,進一步通過分子對接技術發現與ACE2具有較強結合力的6個化學成分,為靛藍、β-谷甾醇、γ-谷甾醇、ODD、亞油酸甲酯及高麗槐素,與目前臨床上推薦用藥氯喹的結合力相當,說明消炎退熱合劑可能對COVID-19具有潛在的治療作用。靛藍、β-谷甾醇、γ-谷甾醇、ODD、亞油酸甲酯及高麗槐素是否可以通過作用于ACE2受體調節多條信號通路抗病毒有待進一步工作的驗證。
綜上所述,通過網絡藥理學和分子對接技術,本研究應用網絡藥理學方法對消炎退熱合劑的化學成分、作用靶標進行了系統性的分析,從分子水平闡述了該復方可能通過多成分、多靶點對機體的整體調控,篩選出6個潛在的抗病毒活性化學成分,為該復方干預COVID-19提供了理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