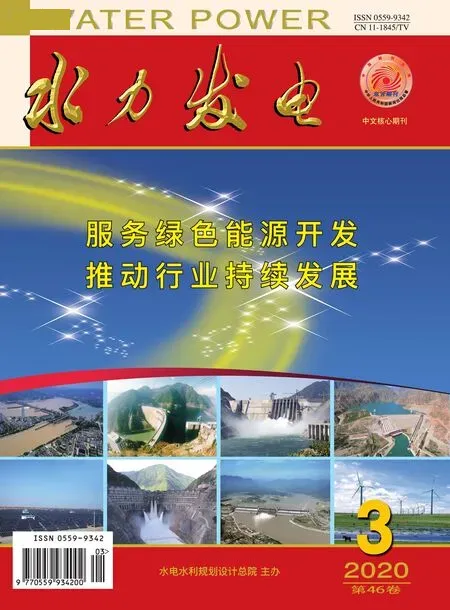“三權分置”改革對水體質量的影響效能分析
許 瑩,陳 莉
(安徽建筑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安徽 合肥 230601)
0 引 言
“三權分置”改革圍繞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進行,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農地所有權與經營權“兩權”變為所有權、經營權、承包權“三權”。這一方面有助于集約化、規模化利用土地,實現農業現代化經營;另一方面,農民的承包權不變,只是把經營權流轉出去,有利于在維護農民權益的前提下,進一步釋放農村勞動力的活力和積極性。2016年10月中辦國辦下發《關于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明確指出,“三權分置”是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農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創新,也是鄉村振興不可撼動的基石。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土地與水息息相關。通常來說,農地中殘留的農藥化肥重金屬等有害物質通過農田排水及地表徑流污染附近河流、水源,同時又滲透土壤進入地下,嚴重污染地下水質。秸稈、地膜、柴草等農業活動產生的廢棄物回收利用率低,直接在田間地頭大量焚燒產生的有毒有害氣體和固體污染物隨大氣沉降、地表徑流等方式進入水體,造成污染。禽畜養殖業產生的排泄物,由于缺乏配套污染處理設施,被直接傾倒入附近河流,造成水體黑臭,富營養化嚴重。在推行“三權分置”改革后,不僅促進了農業的規模經營,也給農村水體質量改善帶來了一定的積極影響。即:一,有序合理土地流轉,促進了農業結構調整。很多研究表明,解決農藥化肥對水體污染的最佳途徑在于調整農業種植結構,減少農作物的播種面積,發展綠色產業。“三權分置”改革后,土地的流轉開發用途從單一的種植、養殖向生產、加工、銷售一體化發展。空間上糧食種植與水資源配位,養殖業與種植業結合更加緊密,提高了禽畜糞便利用率,降低了對水體面源污染的強度。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滿足水環境容量的負荷要求。二,改革將農戶從家庭式的分散經營向規模化的專業大戶、家庭農場和農民合作社等各類新型經營主體集中,帶動農民從事有組織的高效農業、特色農業和綠色農業。龍頭公司發揮示范作用,配套相關環保設施,改善排灌條件,在源頭上控制了化肥、有毒廢水等污染物的排放。三,土地流轉出去后,較好地解放了農村剩余勞動力,農民進城務工或從事新型農業經營活動,可以接觸到高效、低殘留農藥新品種及測土配方施肥等新型環保技術,相較家庭農業活動模式而言,減少了農民使用化肥的意愿,增強了農民環保意識。
為此,本文在探究“三權分置”土地改革與農村水污染關系的基礎上,實證研究“三權分置”對農村水體質量的影響,探索“三權分置”背景下水污治理之路。
1 相關理論研究與模型假設
Brian M. Dowd等(2008)提出來自農業的非點源污染,是造成水質損害的主要原因[1]。Toshiyuki Nagumo等(2004)評估了位于日本北海道中部淺川市的Etanbetsu河流域的污染情況,認為大型畜牧業生產過程中糞肥貯存場的排水和填埋場的排水是嚴重影響河水質量的污染源[2]。Wu, Yonghong等(2017)提出農村地區人類活動產生的非點源污染已導致地表水營養物質輸入過多,水質下降[3]。Han-Tea Kim和Soon-Kuk Kwun(1993)通過對博哈河流域的調查分析,認為流域最重要的污染源是牲畜,其次是人口、土地利用和工業[4]。Maciej Dzikiewicz(2000)選擇波蘭農村作為研究區域,認為農業活動會釋放沉積物、殺蟲劑、動物糞便、化肥和其他無機物和有機物,從而導致了水質惡化[5]。
國內學者針對我國農村的具體情況,認為造成農村水體污染的原因主要有:生活污水、工業廢水、禽畜養殖和農業面源污染[6];其中,面源污染是造成目前農村水質污染的最重要原因[7]。梁瀚文(2011)通過實地調研和現場抽樣的方法,認為農村水體污染源主要來自:生活污水、畜禽養殖污水與糞便,且由于不同地區用水習慣的不同,污水排放的地區差異較大[8]。為解決水污染問題,廖衛東、肖欽(2018)提出優化農村污水治理體系的方法,即鼓勵社會資本與村民共同參與、完善機制體制設計等方法[9]。楊曉婉 (2018)也指出了公共參與的重要性,同時還應配合頂層設計,加強宣傳教育[10]。楊曉英(2012)經過調研提出,農民是水質惡化的直接受害者,也是水體污染的制造者,了解農民對水體污染的態度,是對流域污染實施有效控制的前提[11]。
對農村水體污染的治理是鄉村振興的必要途徑,農村水污染不同于城鎮,具有點多、面廣、分散、量小等突出特點[12],針對我國農村流域水污染的特點,目前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主成分分析法、層次分析法(AHP)、回歸分析法、輸出系數法等。郭晶、王丑明等(2019)利用主成分分析法,選取了8個水質指標,對洞庭湖水質進行綜合評價[13]。鐘平(1986)利用AHP方法分析了農村經濟發展對水污染因素的影響[14]。彭亞輝等(2018)采用輸出系數法對湘江流域水污染狀況進行分析,得出了研究區水污染負荷的時空分布規律及成因[15]。金菊良等(2001)提出了投影尋蹤模型,以驗證水質評價標準的合理性[16]。陳曉宏(2011)等通過建立Binary Logistic回歸模型,對降低農村水污染的驅動因素進行了識別[17]。
本文參考相關文獻和實地調研的結果,結合文章研究的側重點,采用結構方程模型(SEM)來分析“三權分置”改革對農村水體質量的影響效能。SEM也被稱為協方差結構模型,由結構模式的方程和測量模式的方程組成,是一種可以建立、估計和檢驗因果關系的模型。結構方程不僅可以分析測量誤差,還又能夠分析潛在變量之間的關系,還可以估計整個模型的擬合度。具體如下:
結構模式方程η=Bη+Γξ+ζ
(1)
測量模式方程X=Axξ+σ
(2)
Y=Ayη+ε
(3)
式中,η為內生潛在變量(潛在因變量)矩陣;ξ為外生潛在變量(潛在自變量)矩陣;B是結構系數矩陣,表示結構模型中η的構成因素之間的相互影響;Γ為結構系數矩陣,表示結構模型中ξ的構成因素之間的相互影響;ζ為結構方程殘差矩陣;X和Y分別為ξ和η的測量變量矩陣;A為測量系數矩陣;σ和ε為測量方程殘差矩陣。根據相關理論研究基礎和和研究區的實際情況,本文認為“三權分置”改革對水體質量的影響路徑有3條(見圖1)。
具體假設如下:①農業結構調整對水體質量有路徑影響;②新型經營主體對水體質量有路徑影響;③農民意識對水體質量有路徑影響。

圖1 結構方程初始模型
2 研究區域概況及數據來源
鳳陽位于淮河中游南岸,處于北緯32°37′~33°03′、東經117°19′~117°57′之間。境內有淮河、濠河、小溪河、板橋河、窯河、天河等8條河流,總長325.3 km,年均過境水量264.78億m3,其中淮河262億m3。流域總面積1749 km2。鳳陽縣有鹿塘、官溝、鳳陽山、燃燈寺四座中型水庫和花園湖、月明湖、方丘湖、老塘湖四面湖泊,總庫容2.65億m3;小型水庫134座和塘壩總庫容6 491 m3。鳳陽縣小崗村是“中國農村改革第一村”,因此,將鳳陽縣選為研究區,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對于“三權分置”改革對水體質量帶來的影響,本次研究選擇網絡問卷和實地走訪相結合的方式。網絡問卷借助于問卷星平臺,共收集到了108份問卷反饋。實地調研:武崗鎮鎮政府、小崗村村委、六鎮村村委,收集到了37份問卷反饋,共計145份。數據來源調研區域的普通農民、鎮政府工作人員、村委干部、從事“三權分置”研究的學者(見表1)。問卷設計采用Likert(李克特)的5分量法,具體見表2。從統計結果來看,具有較典型的代表性。

表2 問卷量表設計
3 模型分析
3.1 信度效度檢驗
信度分析又稱可靠性分析,它反映了被測指標的真實程度。常用的檢測方法是cronbach’s alpha系數,是目前評價內部一致性的首選。當cronbach’s alpha系數值大于0.7時,表示信度較高;當cronbach’s alpha系數的值在0.35至0.7之間時,表示信度一般;當cronbach’s alpha系數的值小于0.35時,表示信度較低。

表1 樣本情況
本文使用SPSS軟件對指標數據的一致性進行檢驗,結果顯示Cronbach’s Alpha系數為0.778(13項),說明案例所使用數據具有較好的信度。另外,對問卷中每個潛變量的信度分別做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各項潛變量的信度檢驗結果顯示:外生潛變量ξ1、ξ2和ξ3的a值均在0.7以上,說明樣本中的潛變量所包含的測量變量具有比較高的一致性。內生潛變量ξ的信度僅為0.513,說明ξ的樣本并未達到理想狀態,為了提高模型的可信度,在后續研究中考慮修改。

表3 各潛變量的信度檢驗
本文采用SPSS對量表做KMO檢驗和Bartlett球體檢驗,變量的效度檢驗表明,KMO值大于 0.7的標準值,因子載荷無異常,即通過此檢驗,可以說明研究變量具有較好的可靠性,適合做因子分析。
3.2 探索性因子分析
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ion Factor Analysis,EFA)是一項用來找出多元觀測變量的本質結構,并進行降維處理的方法。在此基礎上,對模型的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和平均方差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進行檢驗。CR是表示內部一致性信度質量的指標值,指標之間相關性越強,潛在變量對它們的解釋能力也越強,內部一致性就越好。AVE表示潛在變量對所有測量變量的綜合解釋能力,AVE值越大,潛在變量能夠同時解釋其所對應的測量變量的能力就越強。標準誤差(Standard Error,S.E.),是描述對應的樣本統計量抽樣分布的離散程度及衡量對應樣本統計量抽樣誤差大小的尺度。Amos同時給出了CR的統計檢驗相伴概率P,P值可以從兩個不同角度對荷載系數的顯著性進行檢驗。具體結果見表4。

表4 問卷效度分析
注:***表示P<0.001。
由表4可以看出,各潛變量的CR值全部大于0.6的臨界標準, AVE值全部大于0.5的臨界標準,且除了測量變量Y3,其他變量的因子荷載也全部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量表和模型的設計有需要改進的地方。因子荷載是測量變量與潛變量之間的一種關系系數。表4中,農業產業調整對農業結構調整的影響最大;新型經營主體的4個影響因素作用力相對均衡;農民對水體保護的意識主要體現在因子荷載達0.91的禽畜糞便的處理上;在綜合影響因素中,水體干凈和用水安全的因子荷載分別為0.85和0.81,社會矛盾的因子荷載僅為0.25,說明水體質量主要體現在水體干凈和安全上。
鑒于模型中外生潛變量?的信度相對偏低,測量變量Y3與其他指標的相關性差,考慮對模型進行修正,刪除與潛變量關系不顯著的測量變量社會矛盾Y3。刪除之后重新對樣本數據進行信度檢驗。結果顯示:整體信度的a值由0.773增至0.776(12項),水體質量的信度的a值由0.513增至0.620(2項),模型改進合理。
4 模型檢驗與評價
4.1路徑系數檢驗
路徑系數表示影響因素變化對研究對象所能產生影響大小的參數。本文采用t檢驗法,檢驗模型中的路徑系數是否具有統計意義,結果見表5、圖2。

圖2 水體質量路徑
4.2模型擬合評價
結構方程模型的整體擬合度評價指標包括卡方自由度比((2/d.f.)、RMSEA、GFI、AGFI、NFI、CFIN、NFI等。從評價結果來看,各項指標均達擬合標準,整體擬合度較好。具體結果見表6。

表5 標準化路徑系數
注:***表示P<0.001;**表示P<0.05。

表6 模型擬合度
5 結 論
從最終模型的結果來看,農業結構調整、新型經營主體和農民意識3個潛變量,每增加一個單位的潛變量,水體質量就會分別提升0.49、0.71、0.55個單位。可以看出,新型經營主體對水體質量的影響最大,農民意識其次,農業結構調整的直接作用力最小。考慮研究區環境特點,應充分利用規模化農業生產的優勢,推廣配套環保技術,從源頭上控制排污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