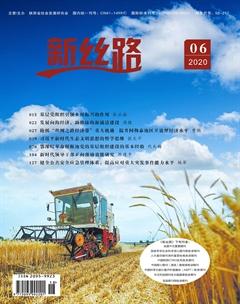川主名實考
摘 要:川主崇拜是四川民間信仰,川主的名稱由來和相關(guān)人物尚存爭議,但功績和影響卻毋容置疑。心有所向,為我所用,百姓各行其“祀”,導(dǎo)致不同時期,不同地域,新舊川主,各領(lǐng)風(fēng)騷。
關(guān)鍵詞:川主;名實
川主成為地方守護(hù)神,成為四川本土鄉(xiāng)神,成為四川百姓的民間信仰,由來已久,但關(guān)于川主身份的爭議卻不絕于耳,包括地方史志在內(nèi)的文獻(xiàn)資料對川主是誰說法不一,與此關(guān)聯(lián),四川以及其他地區(qū)所建川主廟、川主宮中祭祀對象也不盡相同。
一、名稱
名不正則言不順,討論“川主”首先要弄清楚“川主”名稱來源。
“川主”有“山川之主”和“四川之主”的不同。“山川之主”是廣義的“川主”,就此而言,全國各地都有“川主”,但此義項一般語境中少有使用。更多情況下,“川主”是專有名詞,是狹義的,指的是“四川之主”,我們討論的也是一般語境中的“川主”。
作為四川地名的“川”最早出現(xiàn)在唐代,唐肅宗分劍南道為劍南東川、劍南西川,四川有了“兩川”的名謂。宋代改道為路,四川分為益州、梓州、利州、夔州四路,合稱“川峽四路”或“四川路”,“兩川”升級為“四川”。
“四川”地名的來歷還有另外一種說法,可以引用清代彭遵泗《蜀故·方域》一段文字將兩種說法一并介紹:“蜀江之水非一,而岷、瀘、雒、巴,為四大川也,四川之名所由方興。一曰:宋南渡后,始分益、利、夔、梓為四路,故曰四川。”
“川主”之“主”有名詞性的“主人”“先主”“主神”以及動詞性的“主宰”“主政”“主管”等意思,也因此,“川主”大致分為兩類,一是古蜀、蜀漢以及前后蜀之類君王,一是蜀郡、益州之類地方官。無論何種說法,作為專有名詞的“川主”應(yīng)該是唐代以后才出現(xiàn)的。
二、功績
老百姓心中有桿秤,人民眼睛是雪亮的,尤其是蜀人,歷來桀驁不馴、愛憎分明,唯有“治蜀興川”“大安蜀民”,或興修水利,或教民農(nóng)桑,或崇文重教,或輕徭薄賦,或仁慈寬厚,或忍辱負(fù)重,這樣的蜀地君王與地方官才能贏得的蜀人的敬重與熱愛,才可能被奉為“川主”。
特別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古代治蜀必先治水,治川主要就是治水,既防洪澇之災(zāi),又保用水之利,君主也好,地方官也罷,歷史上的“川主”大多有治水功績。
三、人物
1.蠶叢
“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作為古蜀最早稱王的蠶叢,在成都平原建立了早期的國家和政權(quán),時間至少應(yīng)該是夏代。有著“縱目”之特別“顏值”的蠶叢開國立業(yè),教民蠶桑,贏得了蜀民敬愛,無論蠶叢故里青神縣的川主宮,還是遠(yuǎn)在松潘縣的川主寺鎮(zhèn),所祀川主都是蠶叢。
傳說蠶叢死后葬在洪雅縣瓦屋山,與家鄉(xiāng)青神縣遙遙相望,后世人們在瓦屋山修建了“蠶叢墓”“蜀王殿”“川主廟”等建筑祀蠶叢。蠶叢也被稱為“土主”,以前,青神縣城北有土主廟,廟內(nèi)塑有蠶叢雕像,每年正月二十一日蠶叢誕辰日鄉(xiāng)民都要舉辦土主會祭祀蠶叢,縣人到縣城北門青衣土主廟進(jìn)香祭祀青衣神蠶叢氏。現(xiàn)在青神縣青城鎮(zhèn)還有土主村。
需要說明的是,以蠶叢為代表,唐代以前的“川主”,其名號都是后人“追封”的。
2.大禹
生于西蜀,走出盆地,造福中國,享譽(yù)天下,“為山川神主”《史記·夏本紀(jì)》的恐怕只有“獨(dú)雄大王”大禹。
被奉為山川神主的大禹,在四川又被奉為川主神、川主菩薩。今岷江上游汶川、北川古大禹部族活動地區(qū),每年農(nóng)歷正月初四民間迎神的日子,都要舉行大規(guī)模的川主神祭祀會,六月初六為大禹生日,人們則在禹王宮、川主廟、王爺廟以趕廟會的形式紀(jì)念大禹。因為大禹,六月六還成為民間節(jié)日“天貺節(jié)”“祭神節(jié)”,“天貺節(jié)”主要祭祀大禹,要用太牢之禮,“祭神節(jié)”官方和民間都要祭祀大禹,且規(guī)模不小。
3.杜宇
東周時期,“七國稱王,杜宇稱帝”,杜宇先后在“郫邑”和“瞿上”建都,自稱望帝,成為第一個稱帝的蜀王。《華陽國志》記載:“杜宇教民務(wù)農(nóng),一號杜主。”杜宇稱王稱帝,同時教民農(nóng)耕與狩獵,還效法堯舜,將帝位禪讓給賢能的鱉靈。因此,來自朱提(今云南昭通)的杜宇深受蜀人擁戴,被尊為“杜主”,身后得到蜀地百姓的普遍奉祀。
“望帝春心托杜鵑”,都江堰玉壘山的二王廟原為望帝祠,齊明帝建武年間益州刺吏劉季連才將望帝祠遷往郫州。望帝祠傳承了1700年的祭祀活動現(xiàn)在已發(fā)展成“古蜀文化節(jié)”,“拜杜鵑、祭望叢”,進(jìn)而“解蜀語、瞻蜀祭、觀蜀舞、賞蜀景、品蜀味、展蜀史”,目的就是祭祀川主望帝杜宇。
對杜宇的祭祀經(jīng)歷了杜主、土主、川主的演變。樂山市有土主鎮(zhèn),就因其地有祭祀杜宇土主廟而得名。
4.鱉靈
《史記·河渠書》記“蜀守冰鑿離堆,辟沫水之害”,但“蜀守冰”有名無姓,且沫水為今天大渡河,所鑿離堆也是烏尤山離堆,于是,有人考證“蜀守冰”不應(yīng)是李冰,而是古蜀最后一個王朝開明王朝的開國之主鱉靈(鱉靈快讀即冰)。
鱉靈,號開明氏,有豐富的治水經(jīng)驗,李冰時代雕刻的治水“三神石人”除大禹、杜宇外,就是鱉靈。《蜀王本紀(jì)》載:“時玉山出水,若堯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鱉靈決玉山,民得安處。”鱉靈也因此被奉為川主。
鱉靈憑治水功績得到杜宇的禪讓,建立了古蜀第五代王朝,即開明王朝。大概為了顯示正統(tǒng),非蜀地出生的鱉靈慕蠶叢名而稱叢帝。
5.李冰、李冰兒子(李二郎)
末代蜀侯綰之后,蜀地不再設(shè)侯爵,“自此但置守而已”。身為地方官,“空降”到四川的陜西(也有山西之類說法)人“蜀守李冰”按理不可能成為“川主”。作為旁證,都江堰出土的公元168年塑造的李冰石像也只有“故蜀郡守李府君諱冰”的題記,始建于公元270年的松潘縣川主寺祭祀基調(diào)至今依然是“蠶叢魚鳧,古蜀松潘”,分布川外的四川會館,其中的川主宮、川主廟往往供奉的也不是李冰……但“始皇得其利以并天下,立其祠”(東漢應(yīng)劭《風(fēng)俗通》),后歷代朝廷也不斷加封,特別是清雍正五年敕封李冰父子后,奉李冰父子為川主成為主流。當(dāng)然,客觀上,李冰治水、治蜀的作為,被奉為“大國工匠,千秋川主”也是有合理性的。
6.劉備、劉禪
蜀漢時期,成都承繼漢代之繁榮,成為亂世中“市廛所會,萬商之淵”“賄貨山積,纖麗星繁”的樂土,“既崇且麗”,與劉備“雄才蓋世”和劉禪“愛德下士”分不開的。
蜀漢政權(quán)歷二世而亡,劉備在位2年,劉禪在位41年,《三國志·蜀書》有“先主備”“后主禪”兩章。后世文字有“先主章武二年,于漢川鑄一鼎,名克漢鼎”的散句,也有“蜀主思孔明,晉家望安石”的韻文。有人認(rèn)為,川主之名可能就是根據(jù)先主、后主之名衍生而來。
川西一帶每年農(nóng)歷二三月舉行的“川主會”,往往要抬著劉備、關(guān)羽、張飛三人塑像出游。湖北省荊州市沙市區(qū)曾經(jīng)有兩座川主宮,供奉的都是劉備。
7.趙昱(趙二郎)
進(jìn)入唐代,李二郎香火一度暗淡,加之李唐王朝姓氏避諱,李二郎逐漸被趙昱替代。
趙昱在家排行老二,俗稱二郎。據(jù)宋代王铚《龍城錄》,趙昱隱居青城山學(xué)道,隋煬帝迫其入仕,出任四川嘉州(今四川樂山)太守。因治水有功且屢現(xiàn)神跡,老百姓立廟奉祀趙二郎。順應(yīng)民意,唐太宗、唐玄宗先后加封趙昱。
趙昱是樂山歷代地方官中唯一被神化的,趙昱被神化為“斬蛟除害”的“神勇大將軍”“赤城王”乃至“龍神”,以前樂山民間的龍舟競賽主要是為了紀(jì)念趙昱。
8.王建
王建是五代十國前蜀的開國之主,他篤信道教,廉恭儉素,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自己卻勤于政事,“躬覽萬機(jī),親臨庶政”以“有利于民”。王建在位十二年,蜀中得以大治,蜀地社會穩(wěn)定,經(jīng)濟(jì)繁榮,文化發(fā)展,國力強(qiáng)盛。
隨唐僖宗入蜀,后追隨王建的道教學(xué)者杜光庭是醮詞專家,其入蜀后撰寫的醮詞,“蜀王”“川主”是篇名關(guān)鍵詞,如《蜀王本命醮葛仙化詞》《李延福為蜀王修羅天醮詞》《川主太師北帝醮詞》《川主周天地一醮詞》《川主令公南斗醮詞》等。王建稱帝之前,曾被唐王朝封為蜀王,所以,王建先后得以“蜀王”“川主”名。當(dāng)然,也有人認(rèn)為杜光庭筆下的川主指的是李二郎或趙二郎。
9.孟知祥、孟昶
孟知祥、孟昶為父子,分別是五代十國后蜀開國和末代皇帝。與劉備、劉禪、王建等人一樣,孟知祥、孟昶是割據(jù)一方,偏安一隅的“土皇帝”。孟知祥在位時間極短,稱帝不到一年就病逝,后孟昶繼位。
孟知祥曾為劍南東川、劍南西川兩川節(jié)度使,成兩川之主,清同治增修《酋陽直隸州總志》說:“然封號已極崇隆而奉祠著第曰‘川主,蓋‘川主者,蜀人土語之尊稱。孟知祥為兩川節(jié)度使,人皆稱之曰‘川主即為證。”
孟昶在位三十年有余,勤政愛民,勵精圖治,勸課農(nóng)桑,刻石興教,使百姓安居樂業(yè),使后蜀成為五代時期經(jīng)濟(jì)文化發(fā)達(dá)的地區(qū),孟昶也就成為名正言順的川主。《蜀故》載:“蜀主祈畤于青城山,青城令獻(xiàn)美女張麗華”;《蜀中廣記》曰:“世傳川主,即二郎神。衣黃,彈射,擁獵犬;實蜀孟昶像也!”
10.楊戩(楊二郎)
宋代灌口二郎廟趁廟會之際,對參與群眾過度索取,要求向二郎神祈福的人至少敬獻(xiàn)一頭羊,引起群眾反感。由愛生恨,群眾把灌口二郎比作宋徽宗朝的太監(jiān)和奸臣楊戩,況且又有徽宗在東京汴梁(今河南開封)重修二郎廟的史實,以訛傳訛,趙二郎也就變成了楊二郎。
還是與避諱有關(guān),趙宋政權(quán)也樂于見到趙二郎變身為楊二郎。上有所好,下必從之,經(jīng)宋元明清戲曲話本小說大肆渲染,楊戩形象逐漸正面化,成為神威顯赫、法力無邊、懲奸除惡、禳災(zāi)祈福的楊二郎,進(jìn)而取代了趙二郎、李二郎。現(xiàn)在都江堰二郎廟“二郎神像簡介”就明確指出二郎神是楊戩,與之配套,還有贊頌楊戩的“川主寶誥”。
二郎神集水神、雨神、雷神、火神乃至酒神、戰(zhàn)神集于一身,先后有官方正統(tǒng)的李二郎,道教文化的趙二郎,民間傳承的楊二郎,真可謂多神格的典型。
二郎神是多神格的,蜀地代有川主出,川主更是多元化的。除以上“有名有實”聲名顯赫的“川主”,還有一些被奉為“川主”的人物,包括公孫述、張魯、關(guān)羽、李雄等,這里不再一一贅述。
四、現(xiàn)狀
我們認(rèn)為,或崇敬,或感恩,或懷念,或祈求,心有所向,為我所用,老百姓各行其“祀”,導(dǎo)致不同時期,不同地域,新舊川主,各領(lǐng)風(fēng)騷。
川主為民間信仰,集儒家、道教和佛教等元素為一體,正史雖然不載,影響卻久遠(yuǎn)。川主在知仁知禮、重情重義的蜀地百姓中“神一樣的存在”,至今對四川地方官有著示范和鞭策作用,勉勵他們以民為本,勤政務(wù)實,勵精圖治,殫精竭慮,鞠躬盡瘁。
清代川主廟遍布四川省(含今重慶市)內(nèi)各州縣,有方志記載的便超過500處。川主廟也見于云、貴、陜、甘、鄂等地,川渝以外的川主廟兼有川人會館的功能。
過去,四川縣城多建有川主廟,川主廟成為縣城乃至鄉(xiāng)鎮(zhèn)的“地標(biāo)性建筑”。遺憾的是,現(xiàn)在“川主廟”仍然是四川以及西南各省常見的地名,但除卻“地標(biāo)”功能,建筑大多蕩然無存。
參考文獻(xiàn):
[1]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09
[2]常璩著、任乃強(qiáng)校注.華陽國志校補(bǔ)圖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曹學(xué)佺.蜀中廣記[M].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
[4]彭遵泗.蜀故[M].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
作者簡介:
鐘恒,男,德陽廣播電視大學(xué),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漢語言文學(xué)和蜀文化。有20多篇論文發(fā)表,有專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