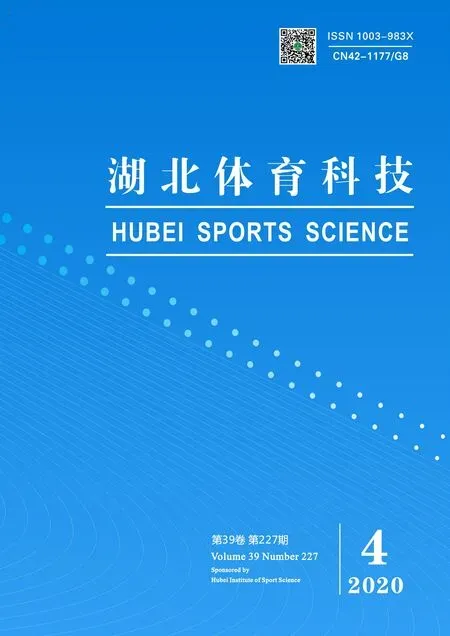湘西苗族圖騰體育的符號學探析
苗 慧,田祖國
(湖南大學 體育學院,湖南 長沙410079)
圖騰,將一些生物或者非生物符號化,賦予世界給人們的感知以意義。圖騰文化是由圖騰觀念衍生的文化現象,在一定社會歷史傳遞中成為超越社會客觀存在的超有機體、也提煉為超越個體心理存在的有意義的現象世界。圖騰體育則是圖騰文化中的體育形式,是一種動態層面上文化基因的表達。圖騰文化從意義上能夠標識一個民族,圖騰體育從形式上影響一個民族情感的外在表達方式,兩者交互滲透融合成為民族文化延存的堅實力量,也使具備靜態穩定性的民族意識被注入動態活性。現階段中國社會處于轉型期,新的社會關系與文化模式尚未生成,社會處于多元文化狀態,人的價值選擇在多種價值觀念沖突中產生混亂[1],圖騰體育作為社會關系中一種活態符號,在社會心理、文化建構、社會秩序構建與發展的脈搏中負載重要意義。本文將以索緒爾符號學的相關理論為支撐,將“圖騰體育”看作是一個完整的動態過程(區別于“體育圖騰”這一具體的靜象表達),對湘西苗族圖騰體育進行探析。
1 湘西苗族圖騰體育的文本內容
1.1 能指與所指:圖騰文化為圖騰體育之所指

表1 苗族圖騰體育的“能指”與“所指”
“所指”是概念、事物及其意義,“能指”是概念、事物及其意義的行為表現或文字表達。在苗族圖騰文化與苗族圖騰體育的關系中,苗族圖騰文化是苗族圖騰體育的所指,苗族圖騰文化處于苗族圖騰體育的背后,并且只有以苗族圖騰體育的存在為依托才能到達抽象意義上苗族圖騰文化的表達 (見表1)。一種文化經久不衰的關鍵因素在于能指行為有堅定的所指意識形態,并使被賦予所指意義的能指行為得以不斷的演練。苗族獅圖騰文化也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傳遞,苗族百獅會于每年正月初舉行,節日當天人們會身披用樹枝、竹子做成的“骨架”、用彩紙做成的“皮膚”的“獅子”,舞獅者伴隨著鼓點模仿獅子的動作[2]。百獅會包含迎獅、盤獅、考獅、搶獅、獅子登高等多個環節,苗族人欲通過此獅圖騰體育活動,表達自己對獅子的尊崇,對驅除邪惡力量和對美好生活的渴望,苗族的獅圖騰文化在此就成為舞獅的所指,同時獅圖騰文化又通過百獅會的表演形式得以展現,成為苗族圖騰文化的能指表達。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系并非一層不變,一些圖騰文化隨著市場的畸形開發,將圖騰體育作為一種交易手段,過于營銷文化符號,致使族人忽略了本族圖騰體育所指的本質。調查小組在湘西花垣縣苗族趕秋節實地調查中發現:苗族舞龍參與者多為為從中攫取經濟利益的臨時演員,對苗族龍圖騰文化缺乏深入了解,表演時情感空洞失去其原始意義上的儀式感和神秘感,與傳統意義上苗族龍圖騰文化所要傳遞給社會的涵義大相徑庭,當一些游客、學者邀請舞龍表演者合影時,表演者將其理解為商業行為,直接提出索要報酬。
1.2 歷時與共時:圖騰體育基因的存在方式
文化是在歷時的轉化為一連串的共時局面中形成的,共時性與歷時性為任何文化特質存在的容量載體。每種文化都具備共時性和歷時性2種特質,以無數個共時局面的片段組合為基礎,通過歷時性連接形成一條發展脈絡,使整個文化氛圍活態化。圖騰體育的共時局面意指圖騰體育中由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要素同時構成的共生局面,圖騰體育的歷時局面意指圖騰體育在時間維度的存在方式,各民族通過在固定或不固定的時間節點舉行圖騰體育,以刺激和深化本民族的圖騰文化意識,如:苗族每年四月份(歷時)過牛王節,屆時要在村寨的場壩里供奉一個紙糊的牛頭[3],供奉精美的食物、燒香叩頭,圍繞牛的牌位跳起極為簡單的舞蹈動作(共時)以感謝牛王送來谷種[4];苗族每年立秋之際(歷時),都會在趕秋節中舉行椎牛活動,屆時苗族人將會先在牛身上不同部位涂上大小相同的白色圓圈,再由椎牛者用一根繩子的一端拴住柱子,另一端拴住牛頭,最后椎牛者將趕牛圍繞柱子跑,并尋找時機用矛棍刺入白色圓圈內直至牛血流盡而亡 (共時)。此外,苗族圖騰體育歷時局面的產生不能脫離共時局面的重復生成,苗族圖騰體育共時局面的破裂將成為苗族圖騰文化歷時傳承中斷的重要因素,如傳承人缺失、生產方式的改變以及生態環境的變遷等,圖騰體育文本內容不能被高頻率深化,這極易造成圖騰體育的文化斷層和共時局面的成像缺失。調研小組通過實地考察與苗族蚩尤拳第八代傳承人石興文師傅談論到苗拳的傳承問題時發現,在蚩尤拳傳承過程中出現了有師傅,沒徒弟的現象,苗族蚩尤拳傳承面臨斷代的可能性,這主要是因為社會現代化的發展造成了直系傳承人的流失(倒逼機制下青少年被動外出求學、務工等),苗族蚩尤拳傳承人不能將自己所學直接傳授于直系親屬,只能被迫轉向社會群體尋求傳承者,在此過程中遭受到了很大的阻力,成為影響苗族圖騰體育歷時局面生成的潛在因素。
1.3 組合與聚合:圖騰體育為苗族文化的組合軸
文化符號被認為攜帶著有意義的具體物或具體行為,苗族圖騰體育作為一種文化符號先從邏輯上在聚合軸上進行選擇,然后產生組合,文本完成后只有組合段是顯現的,屬于表層結構;聚合是隱藏的,屬于深層結構[5]。聚合軸有選擇和比較的功能,各民族根據自身需求選擇適合本族群發展的民族文化,具有極強的符號標識性。組合軸有結合的功能,將受特殊的環境、歷史條件、社會活動、行為習慣等進行臨近黏合。如:蚩尤拳、山地環境、精神需求則是苗族蚩尤文化的組合軸。一方面,原始苗族人面對陌生的自然世界充滿畏懼,為了滿足內心世界對安全感的需要以獲取精神層面的依托,蚩尤(牛面人身)被苗族人視為力量和正義的象征,對牛產生崇拜之情。另一方面,苗族人聚集區多處于山林之中,地勢坎坷不平,沒有大片平整的地面,其活動范圍被限制,因此蚩尤拳拳架具有緊湊、動作弧度小的特征。苗族文化通過自然環境、圖騰體育、價值信仰等不同形式的組合軸進行不斷地重組,歷經時間的打磨,匯聚成當下的聚合軸模式,在一段時間內苗族文化聚合軸呈現出穩定性特點。但是,這種文化模式形成一種穩固的狀態后不會永久性的一成不變,將會隨著苗族社會發展過程中苗族人心理需求的不斷被滿足,繼而反作用于社會產生更大需求,蚩尤拳將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當下蚩尤拳很大程度上面向學校,傾向于成為一種身體教育的手段,這種具有教育性的組合軸(蚩尤拳)將在日益變化的社會文化環境和自然生態環境的交互影響下,進行不斷地重組并賦予苗族民族文化以時代內涵。
2 湘西苗族圖騰體育的社會效應
2.1 范化苗族社會心理
司馬云杰基于文化心理學視角,就文化價值的客觀性進行闡述,文化作為人類的創造物是對外來世界思維的肯定形式,是人類根據自己的需要并通過全部感受及所具有的記憶、聯想、想象、推理等基本思維能力做出的[6]。通過這種思維肯定,人類把客觀存在能指為自己的產物,創造出各種文化特質和滿足自己需求的文化價值,圖騰體育作為一種文化就是基于此所建構出來的產物。苗族圖騰體育作為苗族文化外化表現形式之一,是苗族民族主觀意向性的表達,苗族圖騰體育作為苗族的符號和象征,其一旦形成,將在相當的歷史階段使本民族的心理得到范化,其行為也會表現出統一性。原始苗族人為使基本生存的渴望以及內心安定祥和的需求得以滿足,將具有牛外貌特征的蚩尤奉為祖先,并以牛圖騰文化作為本民族符號衍生出一系列與之相關的圖騰體育,如:苗族根據本民族特有的時間空間,將每年的農歷正月二十五定為斗牛節,通過斗牛彰顯出苗族人對勇敢、追求公正的心理[7],這些民族心理在歷史長河中不斷重復,深化了本民族符號,使族人更加具有歸屬感和一致性。
2.2 增進苗族文化認同
圖騰體育的傳承是行為主體在文本內容上基因的復制與重組[8]。人是客觀圖騰體育的行為主體,對圖騰體育具有創造性、對民族文化具有聚合軸上的選擇性。在選擇的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固有文化世界影響,通過歷時的沉淀交錯糅合成一個超有機體,內化、整合、建構文化價值意識,增進族人之間的文化認同感。苗族對牛圖騰的崇拜,一方面是由于原始苗族人對共同生存的自然環境未能有規律性的認知造成其畏懼自然,認為萬物有神靈,想通過思維萬能的方式從意志上控制自然,祈求風調雨順、五谷豐登,最終族人選擇將農作伙伴——牛神化,牛圖騰體育由此順勢而出。另一方面苗族人具有共同的歷史記憶,具備牢固而可靠的文化紐帶,由此產生強烈的文化認同感。苗族人認為蚩尤(蚩尤外貌被刻畫成牛的形象)為守護家園,在涿鹿之戰中犧牲,遂信奉蚩尤為祖先,苗族對蚩尤的崇拜也如同對祖先的敬愛,蚩尤拳的命名便是為了紀念蚩尤而生。苗族牛圖騰體育經過不斷地適應、整合、分化、重塑,從而形成了區別于其它文化的價值體系,這不但詮釋出本族內各氏族間的關系,還劃分出與其它各民族之間應有的關系[9],同時,圖騰體育的傳承也使其文化價值不斷被賦予新內涵,產生新的文化認同,亦使本民族整個內在意識形態的延續更具向心力。
2.3 規制苗族社會秩序
社會秩序是指人們在社會活動中所遵守的行為規則、道德規范以及法律規章,表示平衡有序的社會狀態[10]。苗族圖騰體育在苗族社會通行過程中存在的規則意識對社會秩序在一定程度上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從歷時維度來看,苗族社會由最初無序、非線性、不平衡的狀態通過社會活動逐步運演為有序、線性、平衡的狀態。苗族圖騰體育中的行為規則、道德規范以社會秩序影響因子的形式存在,當眾多影響因子通過歷時的積累而逐漸增加時,苗族圖騰體育便會潛移默化地聚合成一種具有苗族民族特征的社會秩序鏈,從而制約本民族的行為規范。如苗族賽龍舟項目主要構成人員有橈手、鼓頭、鑼手、艄公、撐篙、艄公,每組龍舟共有橈手三四十名,舟上有鼓頭、艄公、撐篙各一人,鼓頭由頭面人物擔任,一般從寨中大姓產生,負責猛烈擊鼓以鼓舞人心;整個賽龍舟人員分配上體現了秩序性,鼓頭一角在整個賽龍舟過程中起著精神領袖的作用,它影響著團隊的整體狀態;艄公由有經驗懂水性的老者擔任,控制著整個船向,他是賽龍舟人員組成的核心,撐篙者和橈手則是服從于領導核心。在賽龍舟中根據老幼尊卑地位,每個人各司其職,成為構建苗族社會秩序穩定性的積極影響因子,促使整個賽龍舟共時局面有序生成。
2.4 固守苗族特色文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體育文化在演化、傳播、再生成的過程中極易產生同質文化、消滅代表歷史差異的能指和所指,將一切事物同質化[11]。西方體育文化所指的本質是生理機制上的極限突破——更高、更快、更遠[12],追求差異化來獲取衡量標準,苗族圖騰體育與之不同,主張內在的人與自然的和諧,西方體育文化作為強勢文化在全球化過程中將不可避免地在苗族社會中產生同質文化,弱化苗族圖騰體育的存在感。然而,也不能割裂本民族圖騰體育與其他民族體育的交融關系,否則將會造成我國傳統體育在發展過程中固步自封,其價值選擇定向,過于模式化發展,從而形成一種封閉型的價值特性,走入發展中的死胡同[13]。苗族圖騰體育作為苗族的意識符號,具有標識功能,能夠區別于其它民族的體育文化符號。通過對其賦予新內涵能夠使苗族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從而固守本民族特色文化。如:苗族的圖騰體育“搶獅”,在應對文化全球化時利用當代先進技術以及教育等多途徑的扶持,使搶獅得到良性傳承。搶獅的延存也在固守當地文化特色的同時,有效防止了被異質文化的吞噬[14]。
3 湘西苗族圖騰體育的發展路徑
3.1 深描苗族圖騰體育的所指內涵
符號的用途是表達意義[15]。苗族圖騰的所指是指苗族圖騰體育邏輯鏈背后的含義。深描苗族圖騰體育的所指內涵是指,通過豐富苗族圖騰體育所要表達的意義符號,深化記憶符號,將圖騰體育普及化、常態化[16],達到發展苗族圖騰體育的目的。如:苗族賽龍舟競賽項目,應當深入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比賽過程中應當強化選手尊重比賽規則、秩序,裁判秉持平等、公正的態度,在競賽過程中團隊成員和諧相處的主題思想,由此弘揚社會主義價值觀念,深描苗族圖騰體育的所指內涵。
3.2 創新苗族圖騰體育的共時局面
創新苗族圖騰體育的共時局面是指,在同一歷時維度下,通過創新苗族圖騰體育自身的存在方式,達到發展苗族圖騰體育的目的。如:苗族圖騰體育教育化。將苗族圖騰體育引入校園,并且依據不同年齡階段學生的特征對苗族圖騰體育進行改編,使其成為現代體育教學內容的一部分。苗族圖騰體育生活化。提煉苗族圖騰體育中代表性動作與大眾舞蹈相結合,以廣場舞形式使廣大群眾參與其中。苗族圖騰體育信息化。利用虛擬現實技術使苗族圖騰體育便于被數字化,從而縮短苗族圖騰體育表意時空的距離,使身處異地的人也能夠體驗到苗族圖騰體育。通過對苗族圖騰體育人口的增加,促進苗族圖騰體育的發展[17]。
3.3 豐富苗族圖騰體育的組合軸
豐富苗族圖騰體育的組合軸是指,通過拓展苗族圖騰體育存在的客觀環境,達到發展苗族圖騰體育的目的。如:創新苗族圖騰體育的生存環境。面對不可避免的全球化、工業化和城鎮化引起的苗族圖騰體育空間的破壞甚至是覆滅的現狀,尋求更符合歷史發展的客觀條件去彌補已經消失的或者正在消失的部分,如建設苗族圖騰體育文化博物館以及苗族圖騰體育主題公園。開拓苗族圖騰體育的市場空間。當下體育商品的消費價值主要由它的符號和象征交往價值決定[18],因此,可挖掘苗族圖騰體育市場價值,如營銷苗族圖騰體育紀念品、吉祥物等。完善保護苗族圖騰體育的制度。不僅需要對苗族圖騰體育進行正值引導,提供資金和政策扶持,同時也需要進行負值限制,對于一些危害或潛在威脅苗族圖騰體育發展的行為進行懲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