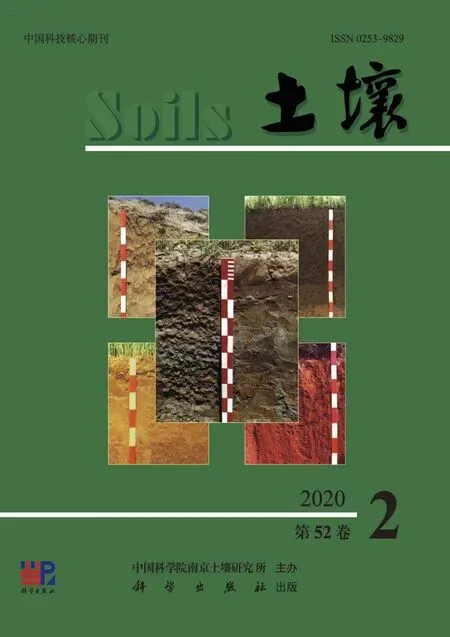木本泥炭對紅黃壤性水田土壤有機質提升和細菌群落組成的影響①
陳美淇,馬 壘,趙炳梓,范樹印,譚 鈞,鞠振山,朱錦尉,徐國華,王淑媛,徐基勝,張佳寶*
(1 土壤與農業可持續發展國家重點實驗室(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南京 210008;2 中國科學院大學,北京 100049;3 國土資源部土地整治中心,北京 100035;4 北京中向利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100004;5 浙江省土地整理中心,杭州 310007;6 杭州市桐廬縣國土資源局,杭州 311500)
土壤有機質(SOM)是土壤肥力的重要指標,也是土壤質量組成成分[1]。田間長期試驗結果表明,SOM 含量與作物產量顯著正相關,也與土壤生化性質顯著正相關[2]。SOM 主要指土壤腐殖質,包括非腐殖物質和腐殖物質。非腐殖物質是與有機殘體組分類似的普通有機化合物,占SOM 的 20% ~30%,腐殖物質主要指經微生物作用合成的高分子化合物,占SOM 的70% 左右[3]。腐殖物質是土壤中不易為微生物利用、最為穩定的有機質部分。因此在土壤中人為添加與腐殖質類似物質,可能短期能快速提高 SOM 含量。木本泥炭是木本植物殘體在沼澤環境中轉換、積累形成的有機資源,含碳量高,纖維素含量低,是一種重要的腐殖酸資源[4],但其施入土壤后對作物產量和理化性質的影響尚不清楚。
秸稈還田是提高 SOM、改善土壤肥力的重要措施之一[5],然而秸稈還田也可能引起當季作物減產以及土壤養分提升緩慢等負激發效應[6],主要由于秸稈分解緩慢,養分不能為當季作物利用,分解過程中土壤微生物與作物爭奪養分所致[7-8];此外,秸稈還田引發病蟲害的幾率也可能增高[9]。因此,如何通過各種方法加速秸稈分解成為熱點問題。室內研究表明,添加菌劑能有效促進秸稈分解,提高土壤速效養分含量以及酶活性[10-11];也有田間試驗發現,秸稈還田后接種菌劑能降低秸稈殘渣中C/N,有效加快秸稈分解[12],趙偉等[13]在東北黑土區田間試驗表明添加菌劑能顯著增加土壤有機質、微生物生物量碳氮含量。但也有研究與上述結論相反,吳琴燕等[14]發現添加3 種菌劑并不能促進秸稈分解,秸稈分解主要依賴自身含有的微生物。同時,現有菌劑制品在田間實際應用效果并不穩定,劉海靜等[15]發現,菌劑對木質素降解能力有限,并且在不同栽培模式下,菌劑作用也有顯著差異。這就需要從另一個角度尋求秸稈快速分解技術。外源有機碳有刺激微生物繁殖、提高微生物活性的潛力[16],從而可能激發秸稈的分解[17],但激發效應如何(正或負),與添加的碳類型相關。已有研究發現,碳類型是影響微生物群落結構改變的主要因素[18],這可能與土壤微生物與不同類型外源碳之間耦合關系不同有關[19]。
浙北地區為典型紅黃壤性土壤,當地主要種植系統為每年單季水稻。丘陵山區具有大量的未開發土地,如何快速提升基于丘陵山區土壤的新墾耕地的SOM 含量是評估其是否具有開發潛力的必要條件之一。本研究擬以新墾紅黃壤性水田土壤為研究對象,選擇 3 種不同碳源的商用激發劑,通過田間試驗比較研究不同激發劑對腐熟秸稈和木本泥炭聯合施用的水稻土上的產量和土壤性質的影響,同時基于高通量測序技術明確不同激發劑對土壤細菌群落結構的影響,并評估其潛在的秸稈激發能力,為激發劑推廣應用提供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田間試驗
田間試驗開始于2016 年,位于浙江省桐廬縣鐘山鄉隴西村(119°21′56.7″E,29°49′19.5″N)。該地區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區,年均溫16.5 ℃,年降雨量1 443.1 mm,無霜期252 d[20]。當地典型種植模式為單季水稻,6 月上旬插秧至9 月底收獲。水稻土發育于紅黃壤,試驗前土壤pH 為6.15,有機質含量10.4 g/kg,全氮28.4 mg/kg,全鉀50.4 mg/kg,全磷 358.1 mg/kg,土壤砂粒含量680.5 g/kg,粉粒248.9 g/kg,黏粒70.6 g/kg。
試驗共設6 個處理,3 次重復,共18 個小區:①不添加任何材料對照(CK);②施用腐熟秸稈(S);③施用腐熟秸稈+木本泥炭(SP);④施用腐熟秸稈+木本泥炭+商用激發劑-I(SPJ1);⑤施用腐熟秸稈+木本泥炭+商用激發劑- Ⅱ(SPJ2);⑥施用腐熟秸稈+木本泥炭+商用激發劑-III(SPJ3)。腐熟秸稈、木本泥炭、激發劑僅2016 年插秧前施用一次,2017 年開始僅常規秸稈還田。小區面積為0.062 hm2,長41.5 m,寬15 m,所有處理隨機排列。腐熟秸稈還田量為2 998.5 kg/hm2,購自江陰市聯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木本泥炭與激發劑均購自北京利豐高科科技有限公司,木本泥炭施用量為30.0 t/hm2,激發劑施用量1 499.3 kg/hm2。
供試作物為水稻,品種為Y 兩優900。水稻種植前,施用碳銨449.8 kg/hm2,之后將土壤打糊,靜止過夜后進行插秧,以30 cm(行距)× 20 cm(株距)插秧,保證小區種植密度一致。在水稻種植7 d 后,將尿素(224.9 kg/hm2)和除草劑拌勻后一并施進稻田,之后不再追肥。基肥施用純氮總量為168.7 kg/hm2。
1.2 樣品采集與測定
本試驗所用樣品采自2017 年水稻收獲季,即考察木本泥炭和激發劑施用2 a 后水稻產量與土壤性質變化。每個試驗小區內5 點取樣法測產,得到產量因子值后,計算求得各小區平均產量。土樣采集為每個試驗小區內取表層土壤(0 ~ 20 cm),多點采集混合而成一樣品,重復3 次,然后用四分法取出足夠的樣品,一部分保存于4 ℃ 冰箱中用于土壤基本性質測定,一部分存于 –20 ℃ 用于土壤DNA 提取及細菌群落測定。
土壤基本性質測定參照文獻[21],土壤 pH 采用電位法測定;硝態氮(NO–3-N)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測定;銨態氮(NH4+-N)采用靛酚藍比色法測定;有機質(SOM)采用重鉻酸鉀氧化-外加熱法測定;有效磷(AvaP)采用碳酸氫鈉浸提-鉬銻抗比色法測定;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MBC)、氮(MBN)采用氯仿熏蒸浸提法測定,易氧化碳(EOC)采用 333 mmol/L 高錳酸鉀氧化法測定,可溶性有機碳(DOC)測定采用水提取、過濾方法。團聚體采用濕篩法測定,土壤顆粒組成采用吸管法測定。土壤團聚度計算采用公式:y=[(x1–x2)/x1]×100%,式中,y為土壤團聚度,x1為>0.05 mm 微團聚體測量值;x2為 > 0.05 mm 土壤顆粒組成測量值。
土壤總 DNA 采用 Fast DNA Spin Kit for Soil(MP Biomedicals, Santa Ana, CA, USA) 試劑盒提取。每個樣品稱取0.5 g 鮮土,按照說明書操作提取DNA。選取特征引物515F (5′-GTGCCAGCMGCCGCGGTA A-3′) 和 907R (5′-CCGTCAATTCMTTTRAGTTT-3′)16S rRNA 基因 V4 ~ V5 區進行 PCR 擴增。反應體系:Q5 聚合酶 0.25 μl,5 μl 5×Q5 反應緩沖劑,5 μl 5×Q5 GC 強化劑,2.5 mmol/L dNTP 2 μl,10 μmol 正向反向引物各 1 μl,超純無菌水 8.75 μl,DNA 模板2 μl。反應條件:98 ℃ 預變性 2 min,98 ℃ 變性 60 s,55 ℃ 退火 60 s,72 ℃ 延伸 30 s,26 個循環之后,72 ℃ 延伸 5 min。反應產物采用 QIA quick PCR Purification kit (Qiagen) 進行純化。將不同樣品的PCR 擴增產物等摩爾混合后,采用 Illumina 公司MiSeq 測序儀完成序列分析。
1.3 數據處理及統計方法
利用 QIIME(quantitative insight into microbial ecology)軟件進行微生物數據處理,相似度為97%的序列合并為同一可操作分類單元(OTU),結果采用RDP(ribosomal database project) 方法與Green-Genes 數據庫進行物種比對(置信度80%),鑒定微生物群落組成并計算 α-多樣性指數(observed species,Chao1 和PD whole tree)。土壤基本性質數據統計分析采用SPSS 17.0 軟件,LSD 多重比較,微生物數據分析采用R 軟件,繪圖采用Origin 2016。
2 結果
2.1 水稻產量
各處理水稻產量如圖1。S 處理產量與CK 相似,而SP、SPJ1、SPJ2、SPJ3 處理分別比CK 增產9.3%、15.9%、11.5%、18.8%,與單施秸稈或不施用任何有機物料CK 相比,施用木本泥炭有提高水稻產量趨勢,其中SPJ1、SPJ3 處理增產達到統計學上顯著差異。表明,在SP 處理基礎上添加激發劑Ⅰ、 Ⅲ 能顯著提高作物產量,增產效果優于激發劑Ⅱ。

圖1 不同處理水稻產量Fig. 1 Crop yields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2.2 土壤性質
2.2.1 土壤有機質及其易利用部分 由表1 知,SP、SPJ1、SPJ2、SPJ3 處理間SOM、EOC、DOC結果相似,并在所有處理中屬最高水平,其中SOM值比S 和CK 處理分別增加20.6%、12.1%、18.8%、20.6% 和39.3%%、29.5%、37.3%、39.3%,EOC 較S 和CK 處理分別增加124.6%、95.5%、104.1%、123.1% 和48.9%、29.9%、35.3%、47.9%,而DOC僅比S 處理顯著增加67.2%、52.7%、50.8%、75.5%。盡管SP 處理的MBC 含量顯著高于添加激發劑的3個處理(SPJ1、SPJ2、SPJ3),但添加木本泥炭處理均顯著高于其余處理,SP、SPJ1、SPJ2、SPJ3 處理分別比S 和CK 處理高13.5 倍、10.9 倍、10.5 倍、11.3倍和16.1 倍、13.0 倍、12.5 倍、13.4 倍。SPJ3 處理的MBN 值顯著高于其他處理,而其余處理間無顯著性差異。上述結果導致S 處理的MBC/MBN 值與CK類似,而SP、SPJ1、SPJ2、SPJ3 處理MBC/MBN 值分別是S 和CK 處理的12.4 倍、10.6 倍、8.3 倍、5.1倍。相關分析表示,EOC 和MBC 呈顯著正相關(圖2),表明施用木本泥炭有刺激微生物生長趨勢,而微生物的迅速繁殖反過來又可促進活性有機質的累積。

表1 不同處理下稻田土壤有機質及易利用部分Table 1 Organic matter and its easy-to-use fractions in paddy soils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2.2.2 土壤pH 及速效養分 表2 表示,S 與SPJ1處理的pH 類似,但顯著低于其他處理。除SPJ1 處理顯著提高了土壤NO–3-N 含量,SP、SPJ3 處理顯著降低土壤NH4+-N 含量外,其余處理速效氮含量未有明顯變化。本試驗選擇的3 種激發劑施用均顯著增加了土壤AvaP 含量,而不同激發劑之間沒有顯著差異,CK、S、SP 處理間也沒有顯著差異,施用激發劑處理(SPJ1、SPJ2、SPJ3)的AvaP 含量比SP、S、CK 處理提高了63.9% ~ 91.7%、46.2% ~ 70.9%、44.7% ~ 69.3%。

表2 不同處理下稻田土壤pH 及速效養分Table 2 Soil pH and available nutrients in paddy soils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2.2.3 土壤團聚度 由表 3 可知,與 CK 相比,S、SPJ1 處理 >0.25 mm 團聚體含量分別提高了0.9%、5.6%,SP、SPJ2、SPJ3 處理 >0.25 mm 團聚體含量分別降低 4.2%、3.6%、5.0%,但均未達到顯著性差異。圖 3 表示,本試驗條件下土壤團聚度分為顯著不同的兩組:施用激發劑組和不施用激發劑組,組內結果類似,但施用激發劑組比不施用激發劑組團聚度顯著提高,SPJ1、SPJ2、SPJ3 團聚度較 SP顯著提高了 28.8%、43.6%、26.4%。表明施用激發劑顯著改善了微團聚體水穩性,而不同激發劑之間沒有顯著差異。

表3 不同處理下稻田土壤團聚體組成(%)Table 3 Composition of soil aggregates in paddy soils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2.3 土壤細菌多樣性與群落組成變化
2.3.1 細菌多樣性 高通量測序結果經質量控制后每個樣品均獲得16 836 條高質量序列,經比對后歸并為1 255 個OTU,歸屬于385 個屬,264 個科,197 個目,105 個綱以及36 個門。α-多樣性指數是表征樣品內部多樣性以及均勻度指數,以Shannon 指數表征細菌多樣性,PD_ whole_ tree(PD)指數表征細菌系統發育多樣性。結果發現(圖4A):單一秸稈還田降低了土壤細菌多樣性以及系統發育程度,而配施木本泥炭后細菌多樣性與系統發育程度均不同程度提高,施用激發劑后細菌多樣性處于較高水平。相關性分析發現,細菌多樣性指數與DOC、細菌系統發育多樣性指數與EOC 顯著正相關,表明施用木本泥炭以及激發劑后,DOC、EOC 含量的增加是土壤細菌多樣性與系統發育程度提高的主要原因。

圖3 不同處理下稻田土壤團聚度Fig. 3 Aggregation degrees of paddy soils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圖4 不同處理下稻田土壤細菌群落α 多樣性變化(A)、Shannon 指數與DOC 之間關系(B)、PD 指數與EOC 之間關系(C)Fig. 4 α-diversity of bacterial community (A),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nnon index and DOC (B), relationship between PD index and EOC (C)in paddy soils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2.3.2 細菌群落組成及其與環境因子關系 圖5A表示,Proteobacteria、Acidobacteria、Chloroflexi 是稻田土壤中優勢物種,相對豐度分別為41.95%、19.17%、14.78%。Actinobacteria(5.34%)、Firmicutes (2.85%)、Gemmatimonadetes(2.54%)、Planctomycetes (2.43%)、Nitrospirae(1.59%)、Cyanobacteria(2.02%)、Bacteroidetes(1.42%)是其余相對豐度大于1% 的物種。對不同處理細菌群落進行PCoA 分析如圖5B。結果發現:主坐標前兩軸解釋了群落變異的44.95%,S、SPJ1 處理與其余處理沿第一軸分開,CK、SP 處理與其余處理在第二軸上分開。Anosim 分析結果也說明,添加外源有機物料處理(S、SP)與CK 群落結構差異顯著(R2=0.75,P= 0.005),同時施用激發劑處理(SPJ1、SPJ2、SPJ3)群落結構與SP 處理也具有顯著差異(R2= 0.44,P= 0.001)。上述分析表明有機物料與激發劑的添加能顯著影響土壤細菌群落組成,改變群落結構。
為明確不同處理下土壤環境因子間關系以及其對于土壤細菌群落結構分異的影響,基于Bray-Curtis距離算法,將土壤環境因子擬合到不同處理的非度量多維尺度(NMDS)排序圖上。脅強系數用以反映降維過程中數據失真水平,其值越小,表明圖中空間關系越能準確表征數據信息。由Stress = 0.12 可知,該排序分析結果能解釋不同處理間群落分異與環境變量關系88% 的信息(圖6)。與圖5B 結果類似,SPJ1、SPJ2、SPJ3 處理位于第一軸下方,而其他處理均位于第一軸上方,表示施用激發劑處理的土壤細菌群落組成與其他處理差異顯著,這差異主要與AvaP、MBN、EOC、DOC 有關(圖6)。

圖5 不同處理下稻田土壤細菌群落組成變化Fig. 5 Changes of bacterial community composition in paddy soils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圖6 不同處理下稻田土壤細菌群落結構與土壤性質之間關系Fig. 6 Relationship between bacterial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soil properties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3 討論
本研究采用高通量測序技術,研究了不同外源有機物料添加對稻田土壤性質的影響以及細菌群落響應。結果表明,不同外源有機物料造成土壤理化性質差異,從而影響作物產量以及細菌群落多樣性和結構。
3.1 有機物料還田配施激發劑對土壤理化性質、水稻產量的影響
木本泥炭含碳量高,作為一種重要的腐殖酸資源,是制作有機肥料的優質原料。秸稈也常作為重要的有機物料,用于還田以改善土壤質量。大量研究表明,添加有機物料能改善土壤理化性質,從而提升土壤肥力,促進作物增產[23-25]。本研究中,與CK 相比,秸稈還田(S)、秸稈還田+木本泥炭(SP)、秸稈還田+木本泥炭+激發劑(SPJ1 ~ SPJ3)均有效提高土壤有機質含量,其中SP、SPJ1 ~ SPJ3 處理能顯著提高易氧化碳(EOC)、可溶性有機碳(DOC)、微生物生物量碳(MBC)等土壤活性有機質部分,SPJ1 ~ SPJ3 處理對土壤AvaP、團聚度有顯著提升作用。就作物產量而言,S 處理未能有效提高作物產量,這可能是由于秸稈的高C/N 比,微生物在分解過程中會從土壤中吸收礦質氮固定在體內,與作物爭奪有限營養,引起負激發效應[16];也可能是由于秸稈還田未能提高土壤活性有機質含量(表1),土壤有機碳含量高低僅說明有機質數量并不能直接說明其質量[26],而活性有機質是土壤中易被分解轉換、活躍度高的部分,也是微生物活動能源和土壤養分的驅動力[27]。本研究發現EOC 與MBC 均呈良好的線性關系(圖2),表明施用木本泥炭提高EOC 含量,能有效刺激微生物生長,進而可能提高作物生長所需的養分循環轉化。木本泥炭由于其復雜結構,能有效吸附銨,從而減少氮素揮發提高氮素利用率[28],也能通過同晶置換提高土壤中磷的有效性[29],有明顯增產作用。這與王亞彪等[30]在甘蔗上應用木本泥炭研究結果一致。秸稈還田配施木本泥炭既補充了土壤中碳源,也增加了土壤氮素的持續供應能力[31];激發劑的添加提高了土壤有效磷(AvaP)含量以及團聚度(圖3),為微生物提供良好生存環境,提高農作物對養分利用率,加速土壤中養分物質循環過程[32],促進作物高產,其中激發劑Ⅰ、Ⅲ效果更優。
3.2 有機物料還田配施激發劑對土壤細菌多樣性的影響
土壤微生物群落參與有機質分解和腐殖質形成分解過程,是土壤中物質轉換和養分循環中重要一環[33],多樣性指數是評價土壤的微生物群落多樣性非常有效的方法之一。袁紅朝等[34]利用 T-RELP 和定量 PCR 技術研究了長期不同施肥對紅壤性水稻土細菌多樣性的影響,結果發現,施肥處理(氮磷鉀配施和秸稈還田)土壤細菌多樣性均高于不施肥處理。郭梨錦等[35]采用PLFA 方法也發現秸稈還田顯著提高表層稻田土壤微生物多樣性。本研究結果顯示外源有機物料對稻田土壤細菌多樣性產生了影響(圖 4)。與 CK 相比,秸稈還田(S)細菌多樣性有所降低,可能是土壤性質改變增加了某些優勢種群數量,而相應減少了其余細菌種類和數量,從而細菌多樣性降低。SP、SPJ1 ~ SPJ3 處理提高了土壤細菌多樣性指數和系統發育指數。相關性分析表明 DOC 與 Shannon 指數、EOC 與 PD 指數均顯著正相關(圖 4),表示施用木本泥炭與激發劑后,DOC、EOC 含量的增加可能是土壤細菌多樣性與系統發育程度提高的主要原因。
3.3 有機物料還田配施激發劑對土壤細菌群落結構的影響
施肥作為影響土壤肥力最主要的農業措施之一,對于土壤微生物群落組成、結構也具有重要調節作用[36-37]。袁紅朝等[22]研究了長期施肥對土壤細菌組成影響,結果發現 Proteobacteria、Acidobacteria、Chloroflexi 為稻田土壤主要細菌類群。王霞等[38]利用克隆文庫技術發現不施肥和秸稈還田的稻田土壤中優勢菌種均為 Proteobacteria,秸稈還田后Proteobacteria 相對豐度提高了 5%。本研究與上述研究結論一致,Proteobacteria、Acidobacteria、Chloroflexi 是稻田土壤中優勢種群(圖5A)。
PcoA 與 Anosim 分析結果表明有機物料還田和配施激發劑能顯著改變土壤細菌群落結構,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與土壤理化性質密切相關。劉瓊等[39]利用 T-RFLP 技術通過培養試驗發現,土壤pH、SOC對水稻土中具有碳同化功能的微生物群落結構有顯著影響。張敬智等[40]研究發現淹水能提高土壤 DOC含量,加速土壤微生物對碳源的利用,從而影響群落結構。陳曉芬等[41]采用 PLFA 技術研究長期不同磷肥處理對紅壤水稻土微生物群落影響,結果發現有效磷、有機碳是影響群落結構和功能多樣性的關鍵因素。本研究利用非度量多維尺度排序(NMDS)分析發現,pH 和 AvaP 是影響土壤細菌群落的最主要環境因子,施用激發劑處理與其余處理群落差異還受MBN、EOC、DOC 的影響,與上述研究結論一致。
4 結論
1)秸稈還田配施木本泥炭和激發劑較不施肥和單一秸稈還田處理顯著提高了土壤有機質及其活性部分(EOC、DOC、MBC),作物增產9.3% ~ 18.8%。外源有機物料配施激發劑進一步顯著提高了土壤團聚度和AvaP 含量。
2)秸稈還田基礎上配施木本泥炭和激發劑后,土壤EOC、DOC 含量的增加提高了細菌多樣性和系統發育程度。Proteobacteria、Acidobacteria、Chloroflexi是稻田土壤優勢菌種。本試驗施用的3 種激發劑均顯著改變了細菌的群落組成,其改變與土壤性質AvaP、MBN、EOC、DOC 顯著相關。表明激發劑可以通過改變微生物的群落結構,從而有可能改變其功能,最后導致土壤理化性質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