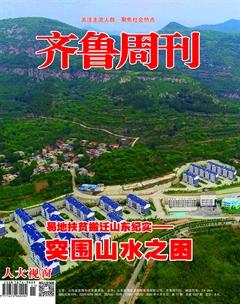房子的故事:沂蒙深處有人家
吳永強
沂南縣孫祖鎮代莊村
一張全家福上的兩個新娘
53歲的趙書英騎上電動車,3分鐘可到一里外的鞋廠。依托臨沂巧鏵鞋業設立的扶貧產業車間,吸納了許多勞動力就業。如果多騎幾分鐘,可到幾里外的娘家。前段時間,94歲的老娘突然臥床,她每天奔波在家、鞋廠、娘家之間,后來干脆請了20天假,去陪老娘。
回到家,迎接她的是庭院里的鮮花,桂花、茉莉、蘆薈,一盆盆有序擺放,芳香四溢。一百多平的寬敞新房,容納了她對生活新的向往。客廳的顯要位置,擺著一張全家福,照片上出現了兩個“新娘”。
回顧往事,三個年份改變了趙書英的生活。
1992年,一個叫尚彥文的青年走進了她的生活。回憶起當時的情景,她只說:“出去玩,在街上認識,就在一起了。”青春時代的美好回憶被一語帶過,戀愛、結婚,她走進了尚彥文家。沒有蓋新房,山溝里的老房子又黑又小。公公去世早,丈夫是小兒子,他們和婆婆住在一起。
憶及往事,趙書英嘿嘿笑,說自己那時候傻,“被愛情沖昏了頭腦”,不管男方家里什么條件,一股腦兒嫁過來。“小黑房”雖破舊,卻也承載了他們樸素溫馨的生活,一女一兒相繼出生,夫妻和睦,婆媳關系也好。
直到2014年,生活的天平瞬間傾斜。
婆婆去世,老公突患疾病,家里的頂梁柱垮了。一方面,老公四處求醫;另一方面,家庭壓力全都由趙書英承擔。老公的病情時有反復,舊病剛好,新病又至,兩個孩子需要撫養,趙書英說,“那幾年能活著就不錯了”。
轉折發生在2017年。
這年8月,一家人搬離“小黑房”,住進新房。作為易地扶貧搬遷項目的一部分,代莊村實現109戶村民(其中,建檔立卡貧困戶50戶)集體搬遷。所有房子都是平房,地上圈梁立柱,統一規劃,根據具體情況,提供四種戶型,滿足不同村民的需求。
雖舍不得住了20多年的老房子,新房剛蓋好的時候,過來參觀,“就不想走了”,立刻決定徹底告別破爛的“小黑房”。
搬家帶來的“好處”一個接一個。
作為貧困戶,村里提供各種補貼,還在合作醫療的基礎上,為他們購買了商業保險。兩個保險疊加起來,個人住院承擔的費用不超過10%。一次,老公去臨沂住院,付錢的時候,“今天三千沒有了,明天三千又沒有了,花錢如流水”。眼看著囊中羞澀,她和老公臉上都蒙了一層陰云。但經過報銷,趙書英驚喜地發現,自己并沒有花幾個錢。

代莊村,趙書英(中)向記者講述這些年的生活變遷。客廳的顯要位置,一張有兩個“新娘”的全家福非常顯眼。
丈夫的病終于穩定下來,卻干不了重活,去幾十里外的一家工廠看大門。丈夫一走,女兒也出嫁了,兒子住校,家里就剩了她一人。丈夫打電話時,囑咐最多的,竟是家里的花,她有點生氣。
尚彥文喜歡花,生病時就在家里擺弄花草,一盆盆桂花、茉莉,點綴了他們的生活。
趙書英笑道:“我干活挺累,還得給你伺候花。”
雖口上抱怨,她當然樂意,這些花已成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
她平時在附近的鞋廠打工,最多時,每月能收入3000多元。和村里的姐妹們一起上班,一起下班,她感嘆道,“要是年輕幾歲就好了,還能多干幾年”。打工上班,不耽誤農活,相當于給生活加了一道保險。
她人緣好,搬了新家,新鄰居們直夸她脾氣好。前幾天,娘去世,鄰居們前來吊唁,總共捎了2000多元錢。到娘家落賬,人們很驚奇,怎么這么多?她說:“以前的老鄰居還不知道這事呢。”
對于自己的人緣,她嘿嘿笑:“我也怪羨慕我自己。”
老鄰居們常從幾里地外過來串門,紛紛說:“真美,你這么大年紀了還住上新房。”也有沒搬遷后悔的,跑去咨詢,這樣的機會還有沒有?
生活也有遺憾,她是文盲,發誓“砸鍋賣鐵也得讓孩子識字”。兒子已讀到高三,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剛開學不久,但學習好,估計能考一個滿意的大學。她跟兒子說:“這幾年生活不愁了,一定把你供到大學畢業。”
娘去世了,每想起來,就一陣心痛。家門口有個小廣場,晚上姐妹們在那里跳廣場舞,以前邀請她,她不跳,有空騎上電動車就去了娘家。現在突然閑下來,姐妹再來邀請,她有時也站在門口看看。想起吃苦一輩子的娘,想起這些年生活的大起大落,心里五味雜陳。
2018年,趙書英又當了一次“新娘”。
女兒結婚前,去拍婚紗照,特意讓一家人都跟著去了。孝順的女兒幫趙書英換上婚紗,尚彥文穿上禮服。夫妻二人挽著手,一對兒女立旁側,兩個新娘定格在這幅溫馨的全家福上。
這是趙書英第一次穿上婚紗。
看著不再年輕的丈夫,想起最初戀愛的時光,女兒問她穿婚紗什么感受,她說,怪難為情的。
談起丈夫,記者和趙書英之間發生了如下對話:
“你當初喜歡他什么?”
“我還不喜歡他呢,他追著不放,這樣就成了。”
“你們平時吵架嗎?”
“不吵,他挺好的,生病期間把煙酒戒了,今年又撿了起來,我挺生氣。他說,我只是晚上喝一次。我怎么知道,平時又見不到。”
平淡的真實,生活透露出一個個閃亮的瞬間。
沂南縣孫祖鎮紙坊村
再也不會“天塌地陷”
一聲悶雷,讓王關菊打了個趔趄。
正月初四晚上9點多,天氣晴朗,并沒有下雨的征兆。王關菊外出回家,快進家門時,前方出現了響動,她打開手電筒照了照,眼睜睜看著一棵十幾米高的楊樹消失于無形。隨著楊樹下沉,呼呼的熱氣冒了出來。
她呆住了。大地在眼前震怒,到底發生了什么?
王關菊家在村子邊緣,塌陷的地方距離她家豬欄很近。她想起半年前,這個地方就發生過一次塌陷,和新的塌陷位置相隔20米。那天晚上,家里的狗不斷吠叫,第二天出門查看,出現了一個坑。
房子前的豬欄塌下去不少,房子里也出現了幾道裂紋。萬幸的是,塌陷的地方在院門外,并沒有人受傷。王關菊嚇壞了,趕緊找到村支書徐以福。徐以福立即向鎮上匯報。
2013年前后,當地天氣干旱,河流幾乎斷流,后來的地質勘探報告中,對塌陷原因總結了三點:
1.該區淺部巖溶發育強烈,可溶巖頂板起伏較大,并有洞口和裂口,洞穴無充填物或充填物少,且充填物多為5261砂、碎石、粉質黏土。
2.細沙易隨地下水流失,取水較為渾濁。
3.地下水與地表水補給情況符合巖溶塌陷特征。
王關菊看不懂專業術語,但她知道,一場從未有過的災難降臨到了頭上。幸虧塌陷發生在院門外的野地里,誰能預測,下一次塌陷降臨在哪里?如果房子突然塌了,那該怎么辦?
孫祖鎮黨委副書記王義禎,那時候擔任鎮武裝部長,見證了從塌陷到搬遷的整個過程。恰值周末,王義禎在鎮上值班,得到塌陷的消息后,跑過去查看。“塌陷的洞呈圓錐形,口很小,大概直徑三米,越往下越大,里面空間不小。”
看著只剩末梢的楊樹,人們心悸不已。
經過討論,當天,王關菊和老公高振友就搬到了同村的女兒家。2013年八九月份,鎮上聘請省里的地質勘探隊前來勘探,最終確定了4戶比較危險的村民房舍,必須立即搬遷避讓。鎮上制定了搬遷方案,給每戶村民提供房租,讓他們外出居住。
那幾年,村里許多人生活在擔驚受怕之中。尤其是下雨后,許多房屋出現裂紋。生活,真有種“天塌地陷”的感覺。
2015年,一套地質災害搬遷避讓方案制定出來。2016年4月,《山東省“十三五”易地扶貧搬遷規劃》出臺,紙坊村涉及到搬遷的90多戶,正式列入搬遷計劃。
接下來的幾年,王關菊夫婦時而住在同村的女兒家,時而住在臨沂的兒子家。兩個人身體都不好,她有腰疼、腿疼,血糖高,干不了重活,老公在附近的建筑工地打零工。他們時常去不遠處的建筑工地查看,新房什么時候蓋好?
2018年農歷八月,村民終于搬進了新房。

大崮后村,搬家那天,正好趕上黃建愛老人過生日。一家人舉辦了老屋里最后一次生日宴。澗邊頑石/圖

搬入新居后的大崮后村村民。
通過抓鬮,王關菊選擇了一個不大的小院。作為貧困戶,直到住進新房,沒用他們出一分錢。容納90戶人家的社區,一座座平房呈現在眼前。中間是小廣場,不時有老人孩子在玩耍。
搬遷后的村莊進行復墾,土地承包給村民,種植玉米、花生。王關菊偶爾下地干活,經過之前老宅的位置,房舍已不在,過去的豬欄、庭院,已經成為農田的一部分,塌陷形成的大坑也早就填平了。她想到過去的生活,恍如隔世。
擔驚受怕的日子,再也不會出現。
沂水縣諸葛鎮大崮后村
再見,大山
天不亮,一個孩子走出了村莊。背上的包里,足足裝滿了30多個煎餅,還有一罐辣椒炒咸菜。他要翻過三個山頭,前往十幾里外的初中。煎餅和咸菜,是一周的糧食,一天吃6個煎餅,五天吃完,多余的幾個以備不時之需。咸菜能放得住,可以吃許多天,一旦提前吃沒了,只能干啃煎餅。
他的身前身后,同樣裝束的孩子很多。小伙伴們打打鬧鬧,穿行在貧瘠的山路上。下雪時,就見一群小雪人,艱難攀上山崖,呲溜一下滑出去老遠。
——49歲的劉慶東經常想起兒時的這一幕情形。
直到許多年后,他外出當兵,退伍后經商,再回到村里,孩子們依然延續著這樣的求學歷程。幾十年時間,對于大崮后村來說仿佛停滯。山下的世界日新月異,山上的世界有如刀耕火種,一代代人的命運被禁錮在半山腰。
大崮后村,位于海拔520米的高山的半山腰,因居住分散,分三個自然村,大崮洼、大崮后、土崮后,有131戶338口人。
村里有一塊石碑,記載了1935年村民躲避土匪的情形:“吾沂苦匪患久矣,賴此山以保全者,不下數千戶。委以此山形勢險峻,除南北盤路可通出入外,四面懸崖峭壁,攀援莫登……”
亂世躲土匪之地,必定是荒僻的山野。有一首民謠在當地流傳:“大崮后,缺三缺。缺水、缺菜、缺老婆。”靠天吃飯,井都打不出水的村莊,缺水是常態;因為缺水,連辟出一塊地種蔬菜都是枉然,根本種不活;這樣的貧困山區,有多少外地姑娘愿意嫁進來?
劉慶東決定為村里做點兒什么。
他回村之前,沂水縣已經開始實施易地扶貧搬遷工程,確定大崮后村整體搬遷至8公里外的諸葛鎮城鎮次中心——原新民鄉駐地。時任村支書劉力學一直忙著村民搬遷的工作,一戶一戶村民做工作,還要承擔工程建設的諸多任務,妻子去臨沂看孩子不在身邊,終因積勞成疾去世。
劉慶東臨危受命,擔任新的村支書,繼續村里的搬遷工作。他覺得,老少爺們既然把重任壓在自己頭上,就應該做好。
2017年下半年,村民逐漸告別祖輩生活的大山,搬到新家。
搬家時的情形,有不舍,更有新的期待。一位攝影師用文字和鏡頭記錄了當時的情形:“我在村中轉來轉去,來到了一戶正在搬家的老人家里。老人告訴我,他叫劉庭業,今年80歲,老伴叫黃建愛,82歲,今天搬家,也正好是老伴的生日。今天是一邊搬家,一邊還要在這老房子里給老伴過最后一個生日,過完生日就要搬到山下的工具房里去了。”
老人一共有四個女兒一個兒子,女兒們除了一個遠嫁東北,其他都來了。兒子兒媳就在本村,里里外外也好互相有個照應。
“劉庭業老人告訴我,在這座老房子里,他們家一共生活了四輩人,有上百年的歷史了。如今一下子搬走拆掉,心里難免有些不舍。”一家人在老屋里舉辦了最后一次生日宴,舉杯同祝老人健康長壽。離開之前,攝影師為他們拍下了一張全家福。
告別故土,迎接新生。
過去鄉上的初中撤銷后,新家占用了校園,村前是一條國道,交通便利,隔壁是小學,孩子們再也不用翻山越嶺求學了。走在新小區里,健身廣場、老年活動中心、閱覽室一應俱全。“目前還存在一個問題,冬天比較冷,正在考慮如何取暖。如果能集中供暖,老年人的生活會更好。”劉慶東說。
他想起讀書時的情形,努力還原過去初中校園的樣子。如今生活在當初的校園里,人生的很多瞬間交疊在一起。
老村的石碾、石磨移到了新村,一方面供人懷舊,另一方面也為村民提供方便。那塊記載著躲避土匪歷史的石碑,重新豎在了村口。
居住條件、生活水平提升了,大崮后村一甩過去的面貌,人居環境超過了周邊不少村。最明顯的例子是,過去的光棍全都找到了媳婦。
今年五一,最后一個光棍結婚,大崮后村再也沒有單身適齡青年。
村里的老房子,大都殘破不堪,拆除后進行復墾。今年3月25日,隨著一聲巨響,一口280米深、每小時出水量30方的大口徑水井噴薄而出——利用從鄰村協調來的一塊地,打出一口井,通過管道輸送到山上。
新村離老村還有一定距離,村民每天騎三輪車往返種地不太方便。村里為每家每戶蓋了工具房,農忙的時候,許多村民就住在里面。
當然,搬遷并不能徹底解決目前農村普遍存在的問題——人口嚴重老齡化,現在種地的主力,已是五六十歲的老人,他們管理著村里近千畝果樹。再過一些年,大崮后村也會面臨無人種地的局面。
平時,新村里只剩下老人孩子。甚至老人也很少,許多人回到過去的村莊,管理果樹。只有在過年的時候,在外打工的年輕人回家了,新村逐漸熱鬧起來。
記載躲避土匪的石碑上,還有一段文字:“今也地方安謐,公民等念山頂樹株,原系大家捐植,日后成材,應由公議抽賣,以作大家公用。凡住山各莊莊長首事等,共同負責保護,嗣后圍墻以內,只許添植樹株,不準開墾種田。”
從過去的“添植樹株”,發展到現在的土地流轉,大規模山林開發,也可以從一個側面看到鄉村的發展變遷。
費縣朱田鎮崔家溝村
“光棍村”脫單記
裴懷成身在山溝,心憂天下。
70歲的他,對國際國內新聞特別關注,聊起來頭頭是道。他最近一直關注兩會的新聞,聯想到這幾年村莊的變化,感慨良多。
崔家溝——位于費縣西南部的大山深處,幾乎“滿足”了我們對貧窮的所有想象:行路難、吃水難、上學難、就醫難、娶媳婦難。
比如上學,1998年崔家溝村小學被撤并后,孩子們只能到16里外的地方上學。年輕人外出打工,接送孩子上學的事兒,交給家里的老人。早晨5點,老人領著孩子走出家門,爬山過溝,把孩子送到學校后,再走16里路回村。匆匆吃口午飯,又得走出村去接孩子。一天四趟,64里路,累了老人;一天兩趟,32里路,累了孩子。

搬遷前的崔家溝老村。
村里以前只有一條僅能步行的羊腸小道。2003年,舉全村之力,修了條3米寬的出山硬化路。山路太陡,彎太多,轎車、摩托車能走,也只限于路上沒有冰雪時;電動車根本爬不上大坡,更不用說自行車了。有的老人30年不下山,幾乎與世隔絕。到附近村鎮打工,不可能,下了班回到山腳天就黑了,摸黑走夜路上山,危險難以想象。
裴懷成想起人們對水的渴望。
一處不到一平米的小泥潭,成為村民吃水的源頭。水量小,好不容易下到幾米深的潭底,一瓢一瓢把渾濁的泉水舀到桶里,挑回家,一半水,一半泥。問起如何洗澡,裴懷成驚道:“水那么珍貴,誰還用來洗澡?一年只有夏天才能洗上澡,找個小河溝洗一洗,平時身上全是灰垢。”
娶媳婦之難,無法想象。裴懷成調侃道:“過去的光棍,都快夠‘一百單八將了。”娶媳婦的痛楚,深深扎根于每個村民心中。一個叫光棍崖的自然村,以前村里有一家人,八個男丁只有兩個娶了媳婦。相親時,娘家人來到村里看了看,把新娘拉上車一去不返;有的新娘硬頂著壓力住進崔家溝,堅持兩三個月,最后還是協議離婚;有的兩口子在外地打工結識,孩子都生了兩個,最后還是分了手。
山上的姑娘,從小就想著嫁到外面去,遠離這片窮山溝;山下的姑娘怕了山上的苦,若非真的是愛情的力量,誰愿意嫁上去?再加上男女比例失衡,光棍數量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一切的根源,是崔家溝的地理位置。
崔家溝村由15個自然村組成,1670名村民生活在海拔460米的大山里。最東邊的自然村與最西邊的自然村相隔8里山路。嚴格來說,這片土地已不適合人類居住。只有那些樸實的村民,對物質需求降到幾乎冰點,一代代在這里繁衍生息。
物質需求降到冰點,精神呢?山下智能手機早已普及時,山上許多人連無線網是什么都不知道。封閉,限制了人們的想象。
2014年,時任費縣縣委書記程守田到崔家溝調研后說:“出路只一條,搬出去。”而且,不僅要搬得出,還要穩得住、能致富。
2016年,崔家溝全村一次性整體搬進了新居。
新建的村子在朱田鎮駐地,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村莊,變成了“崔家溝社區”。新社區供暖、物業免費,建成了幼兒園、衛生室等公共設施和3處就業安置區,村民在家門口就能就業。
仿佛做夢一般,村民徹底告別大山,和過去的生活割裂。
村民有的到附近的產業園區打工,有的自己開店經商,老年人外出采金銀花,還有人在崔家溝原來的山坡上經營家庭農場,年收入四五萬元很平常。過去種地、喂牛一輩子的闞大姐,走進了鎮上的制衣廠,每月收入兩千多元錢。村民們再次忙碌起來,不再與土地有關。
最顯著的變化,是光棍少了。僅在搬遷后的一年,崔家溝就辦了41場婚禮、迎來46個小寶寶。
過去,一對小青年談戀愛,女方母親乘車去男方家,還沒到村就被山路繞暈了,痛哭流涕。后來拗不過女兒,勉強讓他們結婚,但條件是不能住在山上,而是住到岳母家。2016年,崔家溝搬遷后岳母親自把他們送回了新村。
2017年,村里舉辦了一場特殊的婚禮。
28個男青年集體結婚,其陣勢,讓人動容。其中年齡最大的一對,經歷非常坎坷。男青年早年去揚州打工,認識了當地一個女孩。女孩是獨生女,父母本身就反對,來崔家溝看了之后,更是感到絕望。女方父母耍了個心眼,沒回揚州,而是偷偷又住了一些天,等到男青年外出打工,領著女兒回了揚州。

2017年,崔家溝村舉辦集體婚禮
愛情的力量最終讓他們走到了一起,兩人偷偷住到一起,有了孩子。直到2017年,一場集體婚禮補辦了他們遲到的儀式。
村支書曹厚海,可能是當地近幾年做證婚人次數最多的村支書。一場接一場的婚禮,讓他看到了村莊的未來。
樹挪死,人挪活。換一個環境,一旦生活便利起來,克服了過去各種限制因素,勤勞所帶來的收益,呈正比不斷攀升。
不過,耿直的裴懷成也有憂慮。看到不斷走進社區的外地女孩,他有點看不懂年輕人的戀愛觀,覺得婚姻不是兒戲,不能“亂來”。
生活環境的驟然改變,肯定會帶來一些“裂痕”,需要時間來修補。
從朱田鎮駐地到崔家溝原址,距離15公里。一條投資近兩億元、65公里長的柏油路,蔓延在那片曾經閉塞不堪的大山上,崔家溝田園綜合體已現雛形。
隨行的朱田鎮鎮長彭建介紹,崔家溝原有的1.7萬畝土地,整體流轉給多家農業企業,還成立了許多合作社、家庭農場,實行“合作社+家庭農場+農戶”的規模化運營模式,打造農村經濟發展的田園綜合體。在易地搬遷土地整理過程中,村里新增了4000畝土地,已經全部流轉出去后,每年又可為村集體增收240萬元。
換一個角度看待大山,閉塞的另一面是幽美的環境。山崮連綿起伏,層層梯田煥發生機,現代農業技術普及之后,將徹底改變這片區域的面貌。
崔家溝,將作為一個地理名詞,不斷產生新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