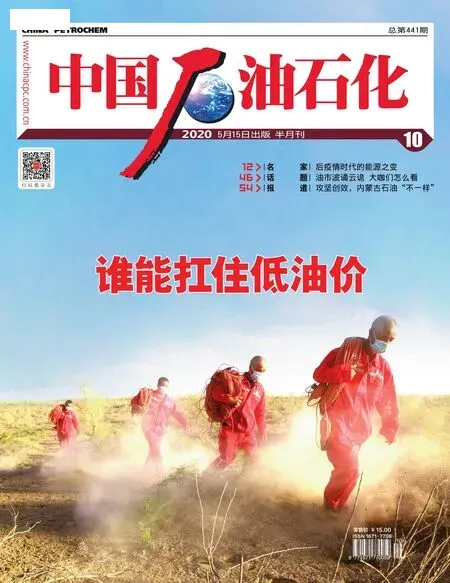油價跌勢空前
文/張 抗
供大于需的走勢日趨明顯和新冠疫情大暴發為低油價形成的首要因素。

▲全球經濟即將面臨大蕭條,中東的原油賣往哪里去? 供圖/IC Photo
2020 年開局油價便出現了明顯下降。以頭50天計,布倫特原油期貨均價為60.67 美元/桶,比2019、2018 年同期分別下跌了0.92 美元/桶、6.98美元/桶。年度開盤價為66.41 美元/桶,2 月20日收盤價為59.12 美元/桶,跌了7.29 美元/桶。這似乎是為油價年度走勢敲響了警鐘,此后便出現了越來越快的降勢。
2 月末到3 月初價格下降到48 美元/桶左右。3 月6 日歐佩克(OPEC)與俄羅斯未能就其減產達成協議。沙特阿拉伯(以下簡稱沙特)單方面宣布其大幅度增產石油的計劃,揚言4 月起將原油日產量從當前的970 萬桶調高至1000 萬桶,在必要的情況下,甚至可能增至1200 萬桶。沙特以增產降價搶占市場份額為標志的行動等于是向石油市場上不肯妥協的伙伴下達的最后通牒。被稱為維也納聯盟的“歐佩克+”之間為期三年的擴大減產的協商局面也暫時破裂。以此為拐點,油價降勢大為加速,3 月9日被稱為國際油價的“黑色星期一”,單日最大下跌幅度達到33.65%,刷新了1991 年海灣戰爭以來的最大單日跌幅。
至3 月底布倫特油價降至23 美元/桶,WTI 最低報價降至19.92 美元/桶,俄羅斯烏拉爾原油現貨從2 月的50 美元/桶下降到15 美元/桶。國際能源署(IEA)的報告指出:3 月油價下跌55%,為2002 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一場慘烈的新油價戰開始了,是多項因素的疊加促使油價大跌。
相對低價背景上的油價“低谷”
縱觀上世紀后半期以來的油價變化,大致可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為二戰后到1973 年的特低油價期,第二階段為兩次世界石油危機高油價背景上的油價劇烈動蕩期,第三階段為1986~2004 年有所起伏的較低油價期,第四階段為2005 至2014 年劇烈起伏的特高油價期。顯然其特點是高油價期和低油價期的周期性相互間隔。
本世紀初,布倫特油價從2005 年均值54.25 美元/桶開始快速上升。2011~2013 年曾大于111 美元/桶。油價升高所刺激的產量增加和所影響的經濟發展速度變慢使市場出現了越來越明顯的供大于需的局面。終于在2015 年油價大幅下跌至52.39 美元/桶,一度曾下跌至30 美元/桶,業內人士稱之為腰斬式、斷崖式下跌。這就是驚動了石油界和經濟界的所謂低油價期。包括筆者在內的許多人認為此次油價下跌是供需新的平衡的表現,甚至預計在近中期油價仍會徘徊在年均值每桶40~50 美元的中等或者說是較低水平上。事實驗證了這個推斷,近年來的布倫特油價(表觀油價)一直徘徊在50 美元/桶左右。因此可以說,這次低油價是在油價年均值相對低的背景上出現的油價“低谷”。
顯然,此次低油價與上世紀后期兩次石油危機人為的特高油價后(1986~1999 年)所出現的低油價性質有重大區別。后者其實仍然是在需求旺盛的基礎上所出現的回歸式的油價平衡。
供大于需的走勢日趨明顯
從市場經濟的一般原理上講,在不出現強力的非市場因素干擾下,供需雙方大致保持著基本平衡狀態,出現價格的相對平穩,或者說是出現“振幅”不大的周期性波動。即使出現多種因素所造成的較長期或較大的波動,在成熟的市場上也終會出現新的供需基本平衡,而不會產生明顯影響經濟發展的危機。誠然,從新的不平衡出現到其得到恢復,表現出油價變化的周期性。
油氣市場當然也遵循著上述一般性的規律。但稍有特殊的是,油氣的產能和產量之間可以存在著一定的差額。油氣田產能和實際產量之差稱為剩余產能。一定量剩余產能的存在是保持生產穩定的條件之一,但過高的剩余產能卻是對油氣產業的一種負擔,意味著投資的沉淀或者積壓,也賦予了它隨著需要增加產量的愿望和能力。許多歐佩克國家,特別是中東的產油大國,如沙特、科威特、伊朗等,非歐佩克國家中的加拿大、俄羅斯等都有著相當大的剩余產能。當遇到需要提高產量來壓低油價或獲得自己國家的特殊利益的時候,這些剩余產能便會大量拋出,影響了世界市場供需平衡。如,即使在油價相對較高的2007~2013 年,歐佩克國家仍然有相當大的剩余產能。主要由于市場份額的限制,使它不能再以減少剩余產能來增加產量。
石油供需形勢在2015 年以后,發生了越來越大的變化。在許多石油生產國產量提高的背景上,俄羅斯、美國和沙特產量的提高特別明顯。經過蘇聯解體所遭受的嚴重打擊后,俄羅斯的產量在本世紀有所恢復,在2009 年達到了5 億噸,2015 年以來保持了5.5億噸左右的年產量,甚至曾居世界首位。近年產量上升最快的是美國,其石油產量的增加主要是由于美國頁巖油產量的持續提高。2014 年后超過了5 億噸,在2017 年以后超過了俄羅斯而居世界首位。

▲供圖/視覺中國 人民視覺
與上述趨勢相應,從2000 年到2018 年,美國和俄羅斯占世界石油產量的份額也分別由8.5%和9.5%上升至13.2%和13.5%,出口量也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份額。沙特是世界傳統的石油生產大國和出口國,作為歐佩克的首領, 也自 愿承 擔了浮動生產 國的 角色。 由于它具有巨額的剩余產能和世界最低的平均油氣生產成本,所以成為左右世界油價的重要力量。應該看到,近年來沙特長期壓縮年產量但石油價格仍走低,在相當程度上損害了自己國家的經濟。這種形勢在2018 年下半年以來,變得特別明顯。
在世界石油市場供應量日趨充分的同時,由于經濟走勢的長期低迷,石油需求增速緩慢,甚至有時出現了負增長。這使得石油再次出現價格下降的巨大壓力。由于各國的情況有巨大的差異,歐佩克內部對于產量增減的集體決定很難達成一致意見。即使歐佩克達成了一致,增產或減產的數量也已經不能完全左右世界石油價格的走勢。于是,出現了“歐佩克+(若干非歐佩克產油國)”會議,集體協商決定當前的減產數量及其在各國間的分配定額。顯然,這種會議的主角是沙特和俄羅斯。可以理解,各國間利益的巨大差異往往使達成無嚴格約束力的協議也十分困難,并且很難保證其后的執行狀況。
2019 年布倫特原油期貨均價為64.2 美元/桶,同比降幅10.5%,世界石油市場已出現日益加大的風險。2020 年初國際油價持續下跌的狀況,已嚴重威脅了所有的石油輸出國。在這樣的背景下,“歐佩克+”仍然未能就減產達成協議,于是沙特阿拉伯決定于2020 年3 月6 日開始單方面大幅降低油價,拉開了新一輪石油價格戰的序幕。
上下游同時出現了危機
在以往的油價波動中原油價格降低直接損害了石油輸出國上游的利益,往往大幅降低著其利潤,甚至使某些公司難以持續運營。但原油價格的降低,給石油工業鏈的下游帶來了利好,成本的降低往往使其產品的利潤增加。這使上下游一體化的石油公司總體利潤的影響不會太大。
近年來,這種情況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下游煉化企業淘汰了大量老、小煉廠的同時,在數量上特別在產能和技術水平上有巨大的提高。這在包括中東在內的許多產油大國表現得特別明顯。如沙特與中國合作在紅海沿岸煉能已超過2000 萬噸/年的廷布煉油廠投產后,中國與科威特合作又建成了規模更大的煉油企業。2019 年,我國大連長興島2000萬噸/年的煉化廠投產,舟山4000 萬噸/年煉化項目一期也投入了運行。煉油產能的快速增加與需求的下降使全球煉化產業出現了日趨加大的產能過剩,產品的市場競爭異常激烈,頻現嚴重虧損。
新冠疫情的爆發使油品過剩局面更加明顯。據Refinitiv 公司統計的數據顯示:全球煉油商生產運輸燃料的利潤進一步下滑,汽油生產利潤一年多來首次轉為負值;亞洲煉廠煉制布倫特原油生產的每桶汽油目前虧損78 美分,為13 個月來最大虧損額。航空燃油的煉油利潤已經跌至每桶4.7 億美元,為該公司自2009 年3 月開始跟蹤該數據以來的最低水平。據IEA 等三大機構的初步統計預測,2020 年一季度全球油品需求同比減少43.5 萬桶/日,下降9.3%,全年需求同比可能下降20.8%。
為解決我國油品供應量的過剩,近年來出口曾有大幅度增加,2019 年汽油、柴油出口同比分別增長27.15%、15.41%。現在看來,這一局面難以維持。世界煉油業為應對虧損和油品庫存爆滿的局面紛紛減產或暫停生產活動。值得關注的是,由于我國國內油品價格已明顯偏高,又開始出現多年未見的油品批量走私進口的情況。顯然,就全球范圍來看,在此次低油價時“上游損失下游補”的情況,已難以完全實現。
全球經濟低迷雪上加霜
影響遍布全球的新冠疫情目前正向經濟落后、醫療條件更差的地區延伸。其對全球經濟的負面影響,還很難做出全面的估計,但無疑會大幅度降低全球GDP 增長的速度。2020 年4 月,國際貨幣組織(IMF)初步估計:全年將會出現GDP 增長-3%的情況,為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還預計美國經濟將萎縮5.9%。在歐洲疫情可列為中等的法國,預測今年的GDP 將出現8%的下降。如果這一預測大致正確,那么疫情更加嚴重的西班牙、意大利和大致相當的德國也會出現相當大幅度的GDP 下降。而英國還將受到“退歐”疊加的巨大影響。至于經濟發展程度差一個等級、醫療水平更差、城市貧民窟遍布的印度、巴西等國,疫情已接近爆發的階段。如果疫情的發展過程與其他國家類似,那么經濟的發展所受的影響會更深重。
中國采取了比較正確的對策,使大規模的封城隔離主要出現在2020 年的第1 季。據國家發改委的公告,該季度的GDP 產值同比仍然降低了6.8%。IMF 在4 月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提出:全球將出現自上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以來的最嚴重的惡化。這種警告值得認真關注。它將使對油氣的需求更大幅度、更長時間降低。這將是此次低油價的特點之一。
經濟形勢惡化最明顯的標志之一是金融的動蕩。油價的下跌伴隨著美國紐約股票市場的大幅度波動、股票指數大幅下跌,以至多次熔斷。這更加動搖了石油美元的地位。美元對其他貨幣和黃金的貶值提醒我們:以不變美元值計的油價比目前使石油市場的表觀價格更低(這往往不被一些觀察者注意)。
油氣發展不確定性增加
進入21 世紀世界將出現“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形勢更加清楚地展現在世人面前。美國更加明顯、囂張的霸權主義和多個地區出現的國家、民族、宗教間的矛盾乃至局部戰爭,使世界形勢詭異多變。可以說油價的變化正是這種形勢在石油上的表現之一。

▲低油價下更要有效率有效益地打井。 攝影/沈志軍

▲修修補補又三年,降本才是硬道理。 攝影/張明江
從油氣供應側來說,美國、沙特、俄羅斯“三巨頭”政治利益上的矛盾,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油價的走勢。上世紀后半期,沙特以美國的盟友和附屬為彼此關系的主要方面。但近年來這種關系有了微妙的變化。一方面美國依托其頁巖油氣的快速發展不但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國,也成為世界石油的首要生產國之一,對進口中東石油的需要大幅度降低。而作為重要的石油出口國,“美國優先”的宗旨卻使其成為世界石油市場份額的重要競爭者。另一方面美國仍然力圖控制中東的政治和石油出口,這不僅是使其作為石油美元的重要支柱,而且可以利用其作為打壓俄羅斯、伊朗和委內瑞拉經濟的重要武器。
沙特雖然保持著與美國的盟友關系,但越來越強調其經濟的獨立性,也更加強調以石油出口收益支持其日益困難的經濟。其打油價戰的策略直接與美國發展頁巖油氣出口的需求產生新的矛盾。特別是目前新王儲薩勒曼所面對的王位繼承的斗爭越來越激烈,困難的國內外形勢使其在政治經濟政策上的不確定性更加明顯。
在美國日益加強的經濟制裁打擊下,俄羅斯的油氣生產和出口已蒙受著巨大損失。顯然它不可能完全同意沙特阿拉伯的低油價策略,不但在遵守減產協議上有巨大的不確定性,也成為“歐佩克+”各種會議討論中難以應付的對手。“三巨頭”間的種種矛盾為世界油價走勢帶來了相當大的不確定性。
作為世界霸主的美國不斷地實施“長臂管理”,插手重要石油出口國的內政制造動亂,正是伊朗、伊拉克、委內瑞拉、利比亞、尼日利亞等國石油產量大幅度波動、出口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這也從另一方面增加了石油價格的不確定性。
除了供大于需的趨勢增強之外,新冠疫情的黑天鵝和幾乎影響到全世界的政治動亂、經濟發展萎縮疊加在一起成為此次石油價格大降的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