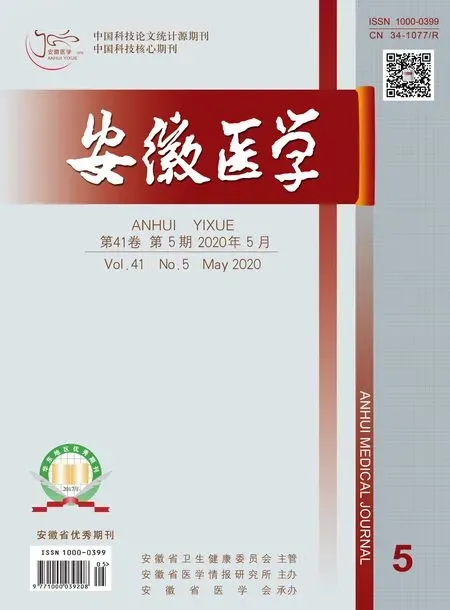通過二代基因測序技術診斷非結核分枝桿菌肺病1例并文獻復習
王馬艷 劉 華 王小軍 胥 英
1 病例資料
患者女性,52歲,農民,主因“發熱、咳嗽、咳痰半月”入院,患者半月前(2018.12.20)感冒后出現發熱,伴寒戰,未測體溫,給予布洛芬退熱后,體溫有所下降,間隔數小時再次出現發熱,性質同前,并逐漸出現咳嗽、咳黃白色粘痰,遂就診于當地縣醫院,胸部CT檢查:左肺上葉片狀滲出影,見支氣管征象,診斷為“社區獲得性肺炎”,給予抗感染、化痰、止咳、補液等方案治療11天后,患者癥狀明顯好轉,于2019年1月5日出院。出院當晚再次發熱,體溫39.6℃,自行口服布洛芬后體溫降至正常,間隔4~6小時體溫再次回升,伴惡心、乏力、納差,癥狀持續4天未見明顯緩解,遂就診于另一家醫院,胸部CT檢查:雙肺間質性改變,左肺上、下葉滲出性改變,給予莫西沙星口服4天后,上述癥狀未見緩解,患者及家屬為求進一步診治就診于甘肅省人民醫院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以肺炎收住。既往史:平素體健,否認慢性病史,否認結核等傳染病病史,否認家族遺傳性疾病。入院查體:生命體征平穩,口唇輕度發紺,雙肺呼吸音粗,左肺下可聞及濕性啰音,雙肺未聞及胸膜摩擦音;心率110次/分,律齊,各瓣膜聽診區未聞及病理性雜音。腹平坦,腹軟,無壓痛及反跳痛,肝脾未觸及,移動性濁音陰性,叩診呈鼓音,雙下肢無水腫。輔助檢查:血氣分析提示為Ⅰ型呼吸衰竭。細菌感染兩項降鈣素原、白介素-6明顯升高,血常規提示白細胞、淋巴細胞在正常范圍內,呼吸道病原體陰性,結核抗體陰性及真菌感染兩項均陰性。肝功檢查:白蛋白25.4 g/L,肝酶輕度升高,肺癌腫瘤標記物未見明顯異常,血沉較快。腹部超聲及全身淋巴結超聲檢查均未見明顯異常。心臟彩超:左房輕度增大,左室射血分數56%。入院后行胸部增強CT:左肺異常密度影,雙側少量胸腔積液,雙側胸膜肥厚、粘連,雙肺門及縱膈淋巴結腫大,部分鈣化(見圖A)。初步診斷:①重癥肺炎(左肺) Ⅰ型呼吸衰竭 ;②肝功能不全;③低蛋白血癥。治療經過:入院后給予抗感染、抗病毒、化痰、保肝、營養支持等對癥治療。評估病情后在CT引導下進行經皮肺穿刺活檢,病檢結果回報:(左肺上葉)慢性炎性改變,未見異型細胞。電子支氣管鏡檢查:支氣管粘膜略充血、腫脹,余未見明顯異常。支氣管肺泡灌洗液細菌培養陰性,未找到結核分枝桿菌。治療2天后復查血常規:白細胞較入院時升高,肝酶有所下降,患者仍有咳嗽、間斷發熱,體溫波動在38.5℃左右;同時復查胸部CT:左肺病灶未見明顯變化(見圖B、C)。2019年1月22日再次在CT引導下行經皮肺穿刺活檢,病檢結果:(左肺下葉)慢性炎性改變,同時將穿刺肺組織外送病原體宏基因檢測。二代基因測序(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NGS)技術結果提示:非結核分枝桿菌。明確診斷為非結核分枝桿菌肺病。當天調整治療方案:莫西沙星 0.4 g口服,1次/日;利福平:0.6 g口服,1次/日;治療3天后復查血常規恢復正常,患者體溫恢復正常,精神明顯好轉。再次復查胸部CT:左肺炎癥病灶與2019年1月15日變化不大,建議繼續治療(見圖D、E)。出院后給予口服莫西沙星0.4 g,1次/日;利福平0.6 g口服,1次/日。半月后再次復查胸部CT:左肺異常密度影明顯吸收(見圖F)。隨訪過程中偶有咳嗽,無發熱,無痰。

圖1 胸部CT
注:A,2019年1月15日胸部CT示左肺上下葉異常密度影,雙側少量胸腔積液,雙側胸膜肥厚、粘連;B~C,治療4天后于2019年1月20日復查示左肺上葉滲出有所吸收,下葉病灶進展;D~E,2019年1月28日復查示左肺上葉滲出病灶有所吸收,下葉病灶進展;F,2019年2月12日復查示左肺滲出病灶明顯吸收
2 討論
非結核分枝桿菌 ( nontuberculous mycobacteria,NTM)廣泛存在自然界中,牛奶、鳥類及水源均可受NTM的污染[1-2]。NTM 有百余種,僅20余種NTM侵入人體后,引起肺、消化道、皮膚軟組織、骨關節、淋巴結等部位感染。NTM肺病患者臨床癥狀不典型,與肺結核患者表現相似,如咳嗽、咳痰、發熱、盜汗、消瘦、咯血等,也可無任何臨床表現[3]。但大多數NTM患者存在基礎疾病,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氣管擴張癥、肺囊性纖維化、塵肺病、肺結核和肺泡蛋白沉著癥等。NTM肺病患者的胸部影像表現復雜多樣,無特異性,可表現為滲出、空洞、結節、干酪樣和纖維化等多種病變,該例患者肺部病變以滲出為主,與常見病原體及結核桿菌感染鑒別困難,常規抗感染治療效果差,取病變組織采用NGS技術證實為NTM感染,給予針對性抗感染治療后患者臨床表現、影像學均明顯好轉。
NTM可通過呼吸道、胃腸道和皮膚等途徑侵入人體,其致病過程與結核病相仿,NTM 的菌體成分和抗原性與結核分枝桿菌具有相似性,但其毒力、致病力弱于結核分枝桿菌[4]。NTM肺病的病理變化與結核分枝桿菌類似,但干酪樣壞死較少,機體組織反應較弱。NTM侵入機體后通過一系列途徑激活多種效應細胞,并釋放多種細胞因子引起免疫反應。
NTM肺病的診斷主要參考2012年我國頒布的專家共識[5], 患者具有呼系統癥狀和/或全身癥狀,經胸部影像學檢查發現有孤立空洞、多灶性支氣管擴張及多發小結節病變等,并排除其他疾病,在確保標本無污染的前提下,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可做出診斷:①痰NTM 培養2 次均為同一致病菌;②支氣管肺泡灌洗液 ( 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BALF) 中NTM 培養陽性1次,陽性度為2個“+”以上;③BALF中NTM培養陽性1次以上,且抗酸桿菌涂片“+”以上;④肺活組織檢查發現有分枝桿菌病的組織病理學特征性改變(肉芽腫性炎癥或抗酸染色陽性),且組織NTM培養陽性;⑤肺活組織檢查發現分枝桿菌病的組織病理學特征性改變,且痰和/或BALF中NTM培養陽性。無論NTM肺病、肺外NTM病或播散性NTM病,均需進行NTM菌種鑒定。
目前治療NTM病的藥物主要有新型大環內酯類、利福霉素類、乙胺丁醇、氨基糖苷類、氟喹諾酮類、復方磺胺甲噁唑等。大環類酯類中的克拉霉素和阿奇霉素是近20 年來治療NTM最常用的藥物,利福平、乙胺丁醇、氧氟沙星、莫西沙星、替加環素、頭孢西丁、磺胺類等對NTM均有一定作用,但不同的菌種具體用藥及劑量有所差異,治療需個體化,總療程為培養陰轉后12個月以上[5]。
由于 NTM 肺病患者的臨床、影像學表現均與肺結核相似,鑒別診斷較困難,臨床上對痰涂片陽性,抗感染治療效果差,除考慮肺結核外,還要考慮 NTM 肺病的可能,可通過分子生物學等新的檢測技術早期診斷 NTM感染,及早給予針對性治療可縮短住院時間,節約醫療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