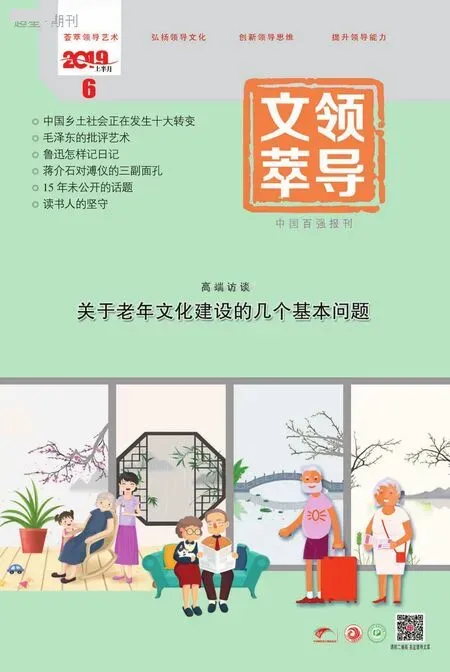朱德和陳毅的詩交
王彪
朱德和陳毅,既同是創建人民武裝力量、身經百戰功業彪炳的軍事家,又都是抒情言志發為心聲的詩人。兩位元帥在近半個世紀的漫長革命生涯中,無論是音訊難通、天各一方的情勢,還是近在咫尺、促膝談心的時分,常以詩歌互訴心聲。他們數十年的情誼,數十年的詩交,給后人留下了許多情誼真率的詩篇。
一
紅軍草創時期,朱德任紅四軍軍長,陳毅任政治部主任。在創建中央蘇區的斗爭中,朱德和陳毅三下閩南,轉戰贛南,在粉碎敵人的五次“圍剿”中,朱德任總司令統帥三軍,陳毅則常以地方武裝配合主力作戰,并為鞏固后方作出了重要貢獻。
1934 年 10 月,朱德率主力紅軍長征,陳毅奉命堅持南方游擊戰爭。“大軍西去氣如虹”“秦隴消息倩誰問”,這是陳毅在最艱難的歲月里懷念戰友的心聲。朱德也以一樣的心情關注著這位戰友的音訊。
1940 年 10 月,陳毅和粟裕指揮黃橋戰役取得巨大勝利。消息傳到延安,在總部參加領導全國抗戰的朱德為戰友的重大勝利感到由衷的喜悅。1941 年,“皖南事變”后,陳毅被中央軍委任命為新四軍代軍長。不久,他即果敢地指揮了討逆(李長江)之戰和陳道口戰役,為創建和鞏固華中根據地作出了重大貢獻。捷報頻傳延安,朱德喜不自勝,欣然吟成七律一詩《我為陳毅將軍而作》:
江南轉戰又江東,大將年年建大功。家國危亡看子弟,河山欲碎見英雄。盡收勇士歸麾下,壓倒倭兒入籠中。救世奇勛誰與識,鴻溝再劃古今同。
朱德將此詩抄示“懷安詩社”同仁,讓延安的戰友們共享勝利的喜悅。這真是“一片深情,盡見于辭”了。
1946 年 11 月,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正是氣勢洶洶、不可一世的時候。這個月的 29 日,恰值朱德同志 60 誕辰之際。毛澤東做了“人民的光榮”的題詞,周恩來也寫下了熱情洋溢的祝詞。
這時在山東解放區指揮作戰的陳毅同志,正面臨著初戰不利的嚴重形勢,但他仍然成竹在胸,堅定樂觀,慰勉部下:“在艱苦困難的日子里,我從來不抱怨部屬,不抱怨同事,不推卸責任,因而不喪失信心,對自己也仍然相信能搞好。”懷著這樣的信念,在連續后撤中集中兵力捕捉戰機以改變戰局的緊張繁忙之中,陳毅揮毫寫下了《祝朱總司令六旬大慶》:
高峰泰岱萬山從,大海盛德在能容。
服務人民三十載,七旬會見九州同。
這首祝壽詩不啻也是一曲人民革命的勝利之歌,僅僅三年工夫,詩人“七旬會見九州同”的預見便提前實現了。
二
1947 年 6 月,劉鄧大軍飛渡黃河揭開了解放戰爭戰略反攻的序幕。9 月,陳毅在指揮沙土集戰役后不久,赴平山向劉少奇、朱德主持的中央工委匯報工作。抗戰勝利一別,匆匆又是二年,一朝重逢,徹夜扺掌深談。陳毅指揮華東野戰軍粉碎了敵人的“重點進攻”;朱德統攝全局,籌劃反攻大計。回顧艱難歷程,展望戰局演進,怎不令人勃發詩興,陳毅即以《平山呈朱德同志》為題吟成一絕:
滹沱河畔與君晤,指點江山氣象殊。
南指中原傳屢捷,石門北望慶新郎。
南指北望,縱論戰局,意態從容,溢于行間。平山一晤后,陳毅攜帶中央工委的意見赴陜北參加黨中央召開的“十二月會議”,與毛澤東、周恩來等同志共商反攻大計。幾乎同時,朱德用杜甫《秋興八首》原韻,寫下了一組膾炙人口的《感事八首》,展現了解放戰爭轉入戰略反攻后的壯闊前景,壓卷之作是《寄南征諸將》:
南征諸將建奇功,勝算全操在掌中。
國賊軍心驚落葉,雄師士氣勝秋風。
獨裁政體沉云黑,解放旌旗滿地紅。
錦繡河山收拾好,萬民盡作主人翁。
總司令對逐鹿中原的劉鄧大軍、陳粟大軍和陳賡兵團作了高度的評價并寄予了極大的期望。在后來的戰略決戰中,陳毅所建樹的功業是無愧于這種贊譽的。
陳毅由陜北回到中原前線后,即與粟裕率華野一部在濮陽開展新式整軍運動,迎接即將到來的大決戰。1948 年 5月,朱德代表黨中央出席了濮陽會議,作了“耍龍燈”“釣大魚”等一系列重要指示。陳毅在歡迎會上發表了《向朱總司令學習》的演說,介紹了朱德的生平,發自肺腑地號召指揮員學習總司令的偉大人格。陳毅興會淋漓地賦詩四首,“呈朱總司令以志其親臨南線之快”。
陳毅拜讀了朱德的《感事八首》,激賞“總座新詩氣如磐”。這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一次唱和。
戰局按元帥的預見進展,一年之后,陳毅參加開國盛典歸來,再一次發為心聲:
元首耀北辰,元戎雄泰岱。
群英共檢閱,盛業開萬代。
這是陳毅對毛澤東和朱總司令的傾心謳歌,也是邁開萬里長征第二步的豪邁誓言。
三
新的時代開始了。人民在創造著新的生活,詩人也以新的篇章傾吐著自己的心聲。
1962 年 4 月,在陳毅的提議下,《詩刊》雜志社就詩歌創作問題在北京舉行了一次規模空前的座談會。朱德和陳毅都到會發表了激情洋溢的講話。朱德說:“我們的偉大事業,光榮事業,將來的革命前途,我們都有責任把這些東西真實地反映出來,給人們看,給我們的后代人看。”他還就繼承和創新問題語重心長地指出:“中國幾千年歷史中,好東西確實不少,無論在文化上、經濟上、政治上,都有我們自己的特點。我們這六億多人能夠團聚著生活下來,就總有自己的特點,自己的長處。有些人有返古復舊的想法,那是不對的。”陳毅緊接著發言,說:“剛才總司令講要把新舊(詩體)揉合起來,這也是我的主張。我寫詩,就想在中國的舊體詩和新體詩中取其所長,棄其所短,使自己寫的詩能有些進步。”他高度評價了“五四”以來新詩的巨大成績,強調詩歌創作要百花齊放,大膽創造,突破框框,充分發揮每個作家的個性。兩位老帥的發言贏得了與會者熱烈的掌聲。
1963 年 9 月,經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的批準,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第一部詩集《朱德詩選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出版之前,朱德對陳毅和李一氓說:“你們倆個看看,修改修改。”陳毅接過朱德詩稿的清抄本,對李一氓說:“你可不要亂動手,總司令是總司令,總司令的詩有總司令詩的本色。”陳毅作詩,重在本色;他的詩論,亦著眼于此。
幾十年的情誼,幾十年的詩交,在即將告別人世的最后年頭,陳毅對朱德及其詩作的真摯情感是十分動人的。
1972 年 1 月 6 日,年僅 71 歲的陳毅與世長辭了。朱德十分悲痛,不顧 86 歲的高齡和正發著燒的病體,執意要人攙扶著向陳毅遺體告別。意志堅如鋼的總司令凝望著年輕自己15 歲的戰友,老淚縱橫,嗚咽出聲,顫抖著行了一個莊嚴的軍禮,向這位自南昌起義后與自己并肩前行的有著 45 年情誼的知交告別。回到病房,朱德仍流淚不已,他已多年沒有寫詩了,這一次,在大慟之中,他心聲凝為詩句,是對亡友的至深至切的追念,也是對鬼蜮蟊賊的義憤填膺的撻伐:
一生為革命,蓋棺方定論。
重道又親師,路線根端正。
(摘自《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