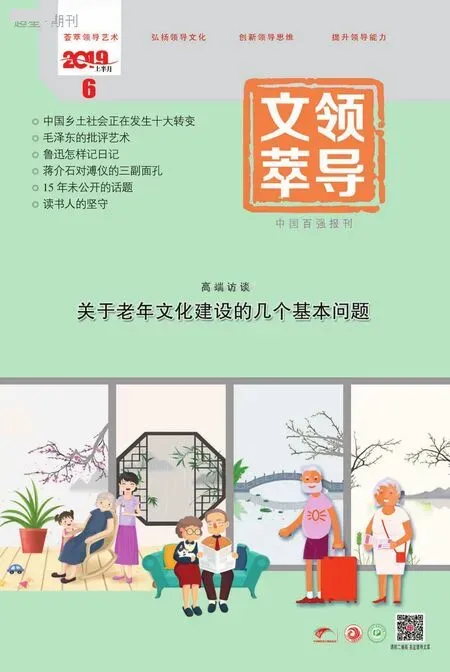史密森的神秘禮物
林達

每個大國都有自己頂尖的博物館。到法國,不可不去盧浮宮;到英國,不可不去大英博物館;到俄羅斯,不可不去冬宮。到我們中國來的“老外”,沒有一個不想去故宮博物院。這些博物館,無一例外都是當年的王室遺產,那里面成百上千年的精華積淀,不是花錢就能建得起來的。美國只有200多年歷史,沒有王室遺產這一說,在藝術收藏上先短了一口氣。可是,你要是跟美國人這么說,他們在點頭承認的同時,或許會悠悠地回你一句:“不過,我們有史密森尼,他們有嗎?”
史密森尼就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華盛頓的國會大廈前是著名的國家廣場,廣場的南北兩邊,有一座座壯觀的大廈,北邊是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國家藝術博物館,南邊有弗利爾美術館、沙可樂美術館、國立非洲藝術博物館、藝術工業大廈、赫尚博物館、雕塑園、國家航空航天博物館等等。這些博物館和位于別地的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國家動物園、肯尼迪藝術中心,以及在紐約的庫伯·休伊特國家設計博物館等,組成了所謂的“史密森尼學會”。而華盛頓國家廣場兩側的這些博物館,號稱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館體系。
在國家廣場南側,有一座歐洲中世紀文藝復興風格的大樓,伸展著高高的塔樓。和附近的國家航空航天博物館相比,雖然體量不大,但是古典風格十分引人注目。這就是史密森尼大廈。從南大門進去,在進入正廳以前有一段不長的走廊。走廊左側是一個大理石的房間,正中的高臺上放著一個花壇形狀的大理石石棺。洋洋大觀的美國史密森尼學會就是從這個石棺開始的。
200多年前,英國有一位年輕的科學家叫詹姆斯·史密森。他的生父是諾森伯蘭公爵,母親有皇室血統,可以說他身上流著英國高貴的血液。但可惜,他是一個私生子。按照當時的法律和習俗,他不能繼承父親的爵位,而且會一輩子受歧視。他天賦極高,聰明過人,由于受歧視而極其用功。21歲自牛津大學畢業,一年后他就被選為皇家學會會員。他在科學上卓有成就,有一種鋅礦就以他的名字命名。
因為是私生子而遭受歧視,使他始終耿耿于懷。據說,他曾經對他的父親說:“我會讓自己青史留名,即使在將來,人們把諾森伯蘭忘得干干凈凈,也會永遠記得我的名字。”
1829年6月29日,64歲的史密森死于意大利。他在遺囑中把遺產留給了侄子。奇怪的是,在遺囑最后,他附加了這樣的條件:如果侄子死的時候沒有子嗣,那么這筆遺產就捐贈紿美利堅合眾國,“用于增進和傳播人類的知識”。
這樣的遺囑,在當時就引起人們的好奇。歐洲和美國的報紙上都披露了這則新聞,人們對史密森的動機議論紛紛。史密森從來沒有去過美國,他為什么要把遺產留給這個新興國家呢?
6年后,史密森的侄子去世,去世時果然沒有子嗣。1836年,美國第一個平民出身的總統安德魯·杰克遜宣布,在歐洲有這樣一筆私人遺贈有待美國領取。誰知道這一消息在國會引起了一場政治辯論。反對美國接受這筆遺贈的主要是州權的維護者,他們的理由是,憲法沒有授予聯邦政府代表整個國家接受這種遺贈的權力,這樣做會在事實上縮減州的權力。參議員約翰·卡爾洪說:“接受任何個人的禮物,美國就喪失了它的尊嚴。”
當時,一位眾議員——前總統約翰·昆西·亞當斯認為,這筆遺贈對于年輕的美國意義深遠,因為這會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他主張將這筆錢用于科學研究。
安德魯·杰克遜總統也是主張接受這筆遺贈的,他認為,美國人民可以將這筆遺贈用于有益的事業。但是,他也拿不準自己是否有權這樣做,所以他要求國會立法允許他派人去領取。
1836年7月1日,國會同意接受史密森的遺贈。杰克遜總統立即派出公使理查德·拉什前往英國。這個時候,史密森侄子的家人已經向英國法庭提出申請,要把這筆遺產留在英國。
拉什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同時也是一名律師。這一場遺產官司打了整整兩年,拉什也在英國待了兩年,被這場訴訟熬得筋疲力盡。1838年5月9日,英國法庭宣布,價值約50萬美元的史密森遺贈屬于美國。
該怎樣利用這筆遺贈呢?怎樣是最好的“增進和傳播人類知識”的用法?美國又展開了一場辯論。一開始,人們主張用它來建立一所國立大學。
建立一所怎樣的大學?很多人主張,現在是科學昌明的時代,要建立一所重視科學考察、探索、研究和應用,而不要傳統的哲學、文學和思辨的大學。用我們的話說,就是大家都主張辦一所理工科的大學,不要辦文科大學。而在此前承襲歐洲傳統的大學,都是以人文學科為主的。
眾議員羅伯特·戴爾·歐文是著名的烏托邦社團創辦人歐文的兒子,他主張創辦一所師范學校,還要促進農業和化學的研究。
還有一些人持不同的看法。有些科學家提出建立國家科學研究所,有人提出建立天文臺,還有人提出建立國家圖書館。這些主意都不錯,都符合史密森“增進和傳播人類的知識”的初衷。這樣的辯論從1838年持續到1846年,最終還是出于對州權的維護而放棄了辦國立大學的方案。國會終于立法,用史密森的遺贈創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個集博物館收藏、展覽、研究、交流和教育于一體的綜合機構,這就是史密森尼學會。
史密森尼學會的第一座建筑物就是史密森尼大廈,這座于1855年落成的古典風格的大廈現在被俗稱為“城堡”。這一城堡成為當時年輕的美國致力于促進科學和傳播知識的象征,后來美國各地的大學學院紛紛仿效“城堡”的建筑風格。
在以后的100多年里,很多人為史密森尼學會慷慨解囊,國家廣場兩側的博物館大廈相繼建造。隨著工業化發展,民間財力增強,大量藝術珍品悄悄流入美國,成為一些富有的商人、工業家、銀行家的私人收藏。其中許多收藏又悄悄地成為史密森尼博物館的收藏。20世紀30年代,銀行家安德魯·梅隆出資5000萬美元為史密森尼建造了“城堡”對面的藝術博物館,并且捐出自己價值1500萬美元的藝術精品收藏。他拒絕用他的名字為大廈命名,堅持博物館應該命名為國家藝術博物館,因為只有這樣,才會有更多的人加入捐贈和維護藝術收藏的行動。
游走于華盛頓的史密森尼博物館中,你可以感受到那種奮發上進的精神狀態。在美國歷史博物館里,小到一根針,大到火車頭,你可以看到各行各業的發展。在國家航空航天博物館里,有各種高科技的航空航天器。在國家藝術博物館里,有價值連城的繪畫、雕塑精品。
1905年,在史密森去世76年后,史密森尼學會理事會的貝爾受美國之托,前往意大利一個叫日諾阿的地方——史密森去世后被安葬在這兒的墓園。貝爾將史密森的遺骸,連同精美的大理石石棺,帶回華盛頓,安放在“城堡”——史密森尼大廈門廳的墓室里。每年有上千萬的游客,從這里開始游覽華盛頓的博物館。
“歸來了,終于歸來了!”也許,只有史密森本人知道,他為什么要把遺產贈送給在那個時代還顯得相當蠻荒的美國,但是美國人都深信不疑,史密森這樣做絕不是沒有理由,絕不是偶然的。他們懷著對這個素未謀面的英國貴族后裔深深的感激之情,深信“增進和傳播人類的知識”是他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摘自《一路走來一路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