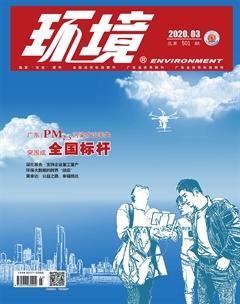黃幸達 公益之路,幸福抵達
江镕


他,是特區斗轉星移、日新月異、飛速發展的親歷者。
他,是深圳滄海桑田、世事變遷、點滴蛻變的見證人。
他開過載客小車,做過服裝批發;他買過工程機械,當過村委主任。
他還抓過嫌犯,建過酒店,捐過學校,做過訴訟。
他叫黃幸達,在環保公益之路上,不懼艱難,潛心而行,只待最終幸福抵達。
苦于奔波的日子,尋找幸福
上世紀六十年代,黃幸達出生在深圳市福田村。作為土生土長的當地人,黃幸達的頭腦中一直保存著深圳鄉村舊有的樣貌。
“在我小時候,深圳可遠不是現在的樣子。當時我們福田村到處都是廣袤的田地,從皇崗一直延伸到筆架山,山坡起起伏伏,家家戶戶以耕田為生。別看福田現在已經是繁華的中心區,在當時這里只是位于邊境上一小塊貧瘠的地方,為了生存,不少村里人都輾轉跑到和我們只有一河之隔的香港謀生。”
生活的窘迫當然也在困擾著黃幸達一家,他的父母都是農民,收入原本微薄,又要養活黃幸達兄弟姐妹五人,壓力可想而知。為了不給家里增加負擔,學習不錯的大姐考到了深圳中學后,不得不放棄讀書機會,出來工作供弟妹上學。
不過作為家中最小的孩子,黃幸達屬于幸運的一個,至上世紀80年代時,家庭條件已經逐漸好轉,為此黃幸達也得以順利讀完了初中。
但那時適逢社會變革風起云涌,大刀闊斧的改革正在福田村展開,村里的大部分耕地都被征收,黃幸達和其他村民一起在瞬間失去了土地。沒有了土地,也就意味著沒有了賴以生存的基礎,必須尋求其他謀生手段,但是附近那些剛剛建起來的工廠又愿不招收持有農村戶口的人。
所以當時的黃幸達生活實在是有些飄搖,只能在這股市場經濟浪潮的沖擊下,不斷嘗試著尋找適合自己的位置。
“那時候我輾轉于不同的行業,找了很多活干,也不知道哪個可行,反正首先得能養活自己才行。”
在當時,而今隸屬于福田區的沙頭街道還被稱作沙頭村,因為比起福田村,這里更落后一點,所以沙頭的很多村民就會跑到福田來做些小生意或者讀書工作。
“所以我也看到了一些工作機會,就讓家里人幫我湊錢買了一輛四輪小車,開始在這兩個地方之間來回拉客。那段路都是土路,坑坑洼洼的,車上最多能坐六七個人,跑一趟大概十多分鐘,我一天能拉上六七趟。”
但隨著農村環境改造,這份工作也受到了影響,村里建成了越來越多的水泥路,也增加了越來越多的公交車,黃幸達的收入每況愈下,不得不另謀出路。
在之后的幾年里,黃幸達也是迫于生計,東奔西走。他曾來往于深圳與虎門之間做過服裝批發生意,又在廣州開過服裝店鋪;他曾籌錢購買了一輛挖土機,在滿是工地的深圳尋找各種工程參與建設;后來又在廣州花都準備興建的珠江水泥廠挖土挖泥。
那些日子里,黃幸達起早貪黑,不辭辛苦,也希望在某個領域能找到一個自己的立錐之地。
但時代洪流浩浩湯湯,個人沉浮有如滄海一粟。“雖然我也很想把一件事情堅持下來,一直做好,但是形勢經常變化,有時也由不得自己。”說起一些往事,黃幸達亦頗感無奈。
忙于嘗試的日子,積累幸福
1991 年,在外歷練多年的黃幸達終于回到福田,幸福地結婚成家,結束了在外奔波的日子。他還在村委謀求了一份管理的工作,算是真正安定下來。
起初,黃幸達在村里擔任聯防隊長,到1992 年福田村成立村民股份公司,他們一家的戶口都由“農”轉“非”,他又當上了村里的居委會主任。衛生、治安、計劃生育……大大小小、紛繁蕪雜的事務他都要參與處理。
“這個村委會主任也不是那么好干的,就像一個大管家,什么都要幫,什么都要管。甚至我還抓住過一個殺人嫌疑犯。”
因為村里地勢低洼時常積水,黃幸達經常帶領同事為水淹后的街道和房屋打掃衛生。有一次大雨后,他們正在清掃,突然聽到樓房上面有人喊“救命”,于是黃幸達和兩個同事馬上跑到三樓,發現已經有人倒在血泊中,而手持兇器的嫌疑人看到有人來變立即向他們沖了過來。
“那個嫌疑人上來就對我們一個同事捅了兩刀,同事馬上倒下了。趁著我們安頓那位同事,嫌疑人一下就逃走了。我安排另一位同事叫救護車,自己就跟著嫌疑人跑過去。追了一段路,那個人跑進了一棟還沒有竣工的樓房,我就堵在門口,叫人過來,因為無路可逃,最終嫌疑人被大家制服了。”
我問黃幸達,遇到這種情況不害怕嗎?他說,當時也顧不了那么多了,遇到壞人總要有人抓,你越顯得害怕,壞人就會越囂張。
不僅如此,之后黃幸達也是多次見義勇為,在街上幾次幫忙抓住了當街實施搶劫的嫌疑人,幫助群眾避免了財產損失。
雖然中等身材的黃幸達在外表上和健壯、孔武并不沾邊,但一個男人的勇敢和擔當卻在這些事件中顯露無遺。
隨著改革開放程度的不斷加深,福田村也得到了由村股份公司集資興建大廈后可供出租盈利的優惠政策。于是黃幸達的身份又轉換成大酒店“福慶大廈”的籌建辦主任。
從集資、監督工程質量到報建、安排落地實施,這個籌建辦主任的工作事無巨細。
“那時候我每天都要往工地跑,一開始很多事情都不懂,但是我逼著自己,不會的就學,不懂的就問,慢慢地也從一個外行成為了工程領域的熟手。后來我又報了會計培訓班、導游培訓班,包括當時深圳剛剛開辦的電腦培訓班。反正能學的我盡量都學,我想‘適者生存,能多找到一些謀生途徑總是好的。”
積土為山,積水為海。黃幸達的付出都沒有白費,在順利完成福慶大廈的建設后,他又在村股份公司成立的旅行社里,擔任了兩三年總經理。后來他又在股份公司出任文明辦主任一職,綜合他多年來積累的工作和學習經驗,在他所負責的文化宣傳、長者福利、工會活動等領域,繼續發揮所長,為村民服務。
在自身能力和經濟條件都有所改善后,黃幸達和家族成員們也開始希望向社會奉獻更多愛心。
2005年,在得知位于廣西蒙山縣樂擁村的樂擁小學已經成為危房、導致200多名小學生學業停滯后,黃幸達徹夜未眠。
因為深知學習對于農村孩子的重要性,黃幸達萌生了一個想法——集資改建學校。但一個人畢竟勢單力薄,于是將自己的打算和哥哥姐姐們進行了溝通,也得到了大家的支持。最終黃幸達一家人集體捐資29萬元,幫助樂擁小學建設了新的教學樓、操場,使200多名學生重返校園。
“經過這件事,我對公益有了新的認識。其實我很早就想做一名義工,盡自己的力量為社會做一些事情,但由于種種原因一直沒有參與進去。捐助學校的事情也讓我覺得其實參與公益并沒有想象中的那么難,只是一個人、一個家庭的力量畢竟有限,只有發揮合力才能完成更大的事情。”
2006年,黃幸達一家喜獲“深圳最具愛心家庭”殊榮,他也結識了很多同樣熱心投身公益的人士,此時他感覺自己“真正找到了組織”。
從此之后,黃幸達就成了一名參與公益活動的積極分子。“環保嘉年華”“地球一小時”“首屆戶外清潔日”“手拉手校服回收”“環保水杯進校園”……幾乎每項活動都可以看到黃幸達忙碌的身影。作為深圳市義工聯環保組的組長,他帶領著三千多名環保義工參加各種大型社會服務活動,堅持身體力行、服務一線。
2013年,深圳市綠源環保志愿協會(以下簡稱“綠源”)在黃幸達的全力推進下“呱呱墜地”,由此,黃幸達的環保公益事業也進入到一個新領域、發展到一個新境界。
樂于奉獻的日子,收獲幸福
“我之所以想創辦‘綠源這個環保公益組織,是因為過去的公益工作讓我感到,義工們雖然經常是做了很多,但是很多服務不夠專業,還帶有很多形式化和行政化的色彩,而且有些時候更在乎服務數量,而不講求服務質量和成果。所以我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讓這樣的情況有所改善。”
“綠源”成立之初,主要是以濱海濕地保護和開展社區宣傳為主,還發起了“衣壺暖流校服回收”項目。為了更好地掌握深圳紅樹林的分布情況,2014年春節,黃幸達放棄了與家人團聚的時間,從大年初二開始和幾個伙伴一起,每天提著干糧,對深圳整個紅樹林的分布進行調研。
“當時在調研中我們發現,寶安西堤有一大片紅樹死亡,后來知道這些紅樹都是因水污染導致的,這也讓我們第一次開始關注水質問題。不久后對西鄉河和新圳河進行調研,結果又讓人大吃一驚。在大家的印象中,深圳是一個天藍地綠的美麗城市,沒想到全省污染最嚴重的5條河流,深圳就占了3條。我們也想都去摸清情況,但如果按原來的方法,靠一兩個專業人員去調研,深圳這么多河流什么時候才能調研得完呢?”
黃幸達說,好在“綠源”擁有大批志愿者,只是此前不夠專業。為此“綠源”邀請了來自香港大學、哈工大深圳校區以及清華大學深圳研究生院的專家教授,對志愿者分批進行培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015年12月26日,“綠源”組織召開了“深圳垮界河流調研報告”發布會,邀請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政府相關部門人員、媒體、環保同行等參加,在當時只引起一點輕微反響。然而到了2016年1月1日,黃幸達突然接到了很多當地媒體的電話,問“綠源”能不能派志愿者帶他們去查找污染源。黃幸達感覺很奇怪,問了相熟的資深記者才明白究竟。
“原來是市領導發話了,問為什么社會組織發現這么多污染問題,而我們政府部門卻沒有發現?要求深圳所有媒體在10天內查找出河流的污染源并進行報道,這之后深圳市投入816億元的治污工程也全面展開。”
為推動政府更加有效治污,2016年,“綠源”還專門拍攝了一部微電影—— 《明溪》,來反映深圳治水中存在的問題。
2016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出了全面實施河長制的通知,為了更好地配合河長制實施,促進公眾參與和監督,“綠源”與深圳晚報社聯合向全社會公開招募“深圳民間河長”,最終經過面試篩選和培訓實習期的考核,第一批確定了45名人選。
黃幸達說:“這些‘民間河長當中有教師、工程師、公務員、律師、武警戰士、普通工人、家庭主婦等等,他們既是利益的相關者,也是污染的受害者,所以也是最有發言權的一幫人。他們會在發現問題后很快將情況發到群里,相關責任部門負責人需要進行認領,并第一時間反饋處理結果。當處理不及時或處理結果不滿意的時候,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就會站出來說話,再處理不好的時候,媒體就會現場調研報道,人大代表也會組織現場調研,向有關責任部門問責。”
2017年,為更好地配合大灣區發展,“綠源”發起“共愛珠江”項目,開始對珠江流域的水環境予以關注。
僅2019年一年,“共愛珠江”項目組就開展了18場流域調研、17場能力建設培訓,組織了14次媒體報道,60多次實地關注珠江流域河流情況,帶動了40多個公益團隊關注珠江流域水資源、資金支持了29家機構的在地行動。
目前項目組共計走訪了100多家流域在地伙伴,促進65個團隊開始行動起來,齊心協力地共同關注身邊的水環境問題。
7年來,黃幸達身體力行,傾情投入,目前“綠源”已招募會員上千人,形成一股巨大合力。
而且幸運的是,多年來家人始終對黃幸達的公益事業十分支持,使得他在工作之余,也能對環保公益事業全身心投入。特別是黃幸達對事業的執著與熱情,也深深感染了兩個子女,目前,小女兒從事貿易工作,大兒子在香港理工大學就讀博士,研究材料科學,他們也成了熱心公益事業的積極分子。
“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
面對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車水馬龍的小巷大街,很多人心中都有一縷揮之不去的兒時情愫,黃幸達亦是如此。
天藍水碧,明朗清澈,這是黃幸達頭腦中未來深圳的理想圖景,也是他內心中回歸本真的期待目標。
愿黃幸達乘著心意也能早日抵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