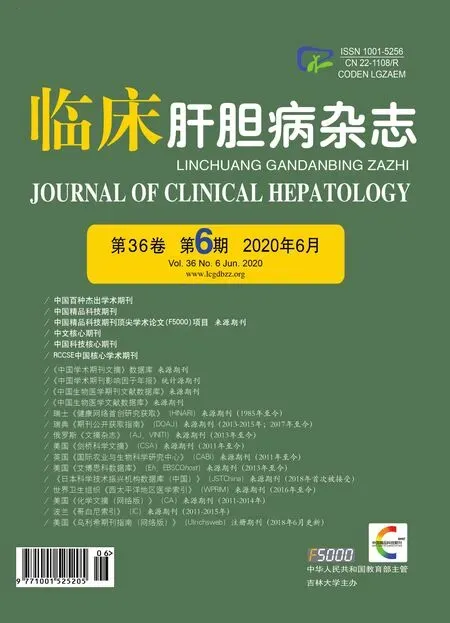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相關肝細胞癌的發病機制
羅 燕,施軍平
1 杭州師范大學附屬醫院 轉化醫學平臺, 杭州 310015; 2 杭州師范大學 肝病與代謝研究所, 杭州 310015
肝細胞癌(HCC)是全球排名第二的致死性腫瘤。隨著肥胖和糖尿病的流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SH/NAFLD)已經逐漸發展成為西方發達國家HCC的主要病因之一[1]。NAFLD的疾病譜包括單純性脂肪肝、NASH、肝纖維化、肝硬化和HCC。盡管在我國病毒性肝炎仍為當前HCC的首要病因,隨著NAFLD患病率逐年增高,NAFLD相關HCC(NAFLD-HCC)的發病率也在悄然上升。相對于病毒性肝炎相關HCC,NAFLD-HCC病程更隱匿,其腫瘤往往更大,預后更差[2]。目前,臨床上尚缺乏治療NASH的特效藥物,也無有效手段預防NAFLD-HCC的發生。因此,加強對NAFLD-HCC發病機制研究,尋找有效的預防及治療NAFLD-HCC的藥物和手段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1 臨床特征
NAFLD是代謝綜合征在肝臟的表現。目前,NAFLD在世界范圍內的患病率為25%~30%,約4%~22%的HCC病例歸因于NAFLD[3]。NAFLD已成為隱源性肝硬化和原因不明HCC的常見病因。一項大規模的回顧性隊列研究[4]結果表明,采用超聲診斷NAFLD患者發展為HCC的年發病率為0.043%。Bengtsson等[5]對2004年-2017年在瑞典卡羅琳斯卡大學醫院就診的1562例HCC患者分析發現,37%的NAFLD-HCC患者無肝硬化,且90%的非肝硬化NAFLD-HCC患者在就診時年齡≥65歲,研究證實非肝硬化HCC在NAFLD中比在其他引起HCC的病因中更常見,盡管在診斷時年齡較大,腫瘤較大,但非肝硬化NAFLD-HCC與其他肝癌患者的生存率相似。Leung等[2]發現非肝硬化NAFLD-HCC的腫瘤體積比有纖維化基礎的腫瘤更大,預后更差。由此可見,NAFLD-HCC疾病進展隱匿,更易被忽視,往往會錯過治療的最佳時機,深入發掘NAFLD-HCC的分子機制,制訂合理有效的防治策略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
2 NAFLD-HCC的分子機制
關于NASH的發病機制,目前比較公認的“二次打擊”學說,認為第一次打擊主要是脂肪攝入增加、肝臟合成增加、脂肪酸β氧化障礙以及極低密度脂蛋白分泌減少引起脂質蓄積,第二次打擊是氧化應激進一步導致肝臟發生炎癥、壞死和纖維化。但多重打擊學說認為,肝臟炎癥是NASH向纖維化進展的首要原因,而不是脂肪變性。NASH是多種因素同時作用的結果,包括遺傳變異、脂代謝異常、氧化應激、內質網應激、線粒體功能障礙、免疫應答改變和腸道微生物群失衡等。雖然肥胖及NASH/NAFLD促進肝癌發生的機制目前尚不完全清楚,但多種腫瘤微環境因素,如促炎細胞因子升高、免疫細胞反應、脂肪代謝失調、腸道微生物群改變等,均可引起或協同促進肝癌的發生發展。
2.1 炎癥因子及信號通路 90%以上的HCC發生在肝臟炎癥的背景下,慢性炎癥誘發免疫細胞分泌多種細胞因子,包括TNFα、IL-6、瘦素、脂聯素、趨化因子等。TNFα會進一步激活NF-кB和c-Jun氨基末端激酶等信號分子,造成DNA損傷,增加基因突變率。IL-6可以激活致癌轉錄因子——信號傳導與轉錄激活因子(STAT3),從而增加細胞增殖,促進細胞存活、血管生成、侵襲、遷移和腫瘤的生長。趨化素樣因子1可以通過IL-6/STAT3信號通路誘發在原發性肝癌中的炎癌轉化[6]。在單純性脂肪肝和NASH患者血清中瘦素的水平往往較高,瘦素與HCC細胞中相應受體結合可激活JAK2/STAT、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和磷脂酰肌醇-3激酶信號通路,同時可以上調端粒酶逆轉錄酶,導致腫瘤細胞的永生化[7]。脂聯素可抑制瘦素誘導的肝癌細胞增殖和侵襲。脂聯素是一種抗炎細胞因子,由脂肪組織細胞分泌。許多實驗數據顯示脂聯素可以激活AMP依賴蛋白激酶(AMPK),抑制哺乳動物雷帕霉素靶蛋白復合物和其他促癌信號分子,也可以通過激活AMPK增加胰島素的敏感性,減輕炎癥[8]。瘦素和脂聯素在炎癥導致的纖維化生成和血管生成中是相互拮抗的作用。
NAFLD-HCC的發生發展與炎癥及腫瘤相關信號通路的突變有關。動物實驗研究[9]發現,C57BL/6J小鼠長期暴露于高脂飲食可導致NASH和自發性HCC的高發生率,對HCC小鼠腫瘤組織和非腫瘤組織的mRNA表達譜分析發現,主要參與的兩個信號通路分別以Myc和NF-кB為中心。對二乙基亞硝酸(DEN)合并高脂誘導的ob/ob肥胖小鼠和DEN合并普通飲食誘導的野生型小鼠的腫瘤組織和瘤旁組織進行全外顯子組測序及KEGG富集分析發現,肥胖小鼠中有8個重要的通路存在明顯的失調,分別為Calcium信號通路、間隙連接通路、黏著斑通路、細胞因子間的相互作用、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信號通路、趨化因子信號通路、MAPK信號通路和腫瘤信號通路。在瘦小鼠中僅有MAPK信號通路和腫瘤信號通路兩個通路改變[10]。對鏈脲佐菌素合并高脂高膽固醇飲食誘導的NASH-HCC小鼠腫瘤組織與非腫瘤組織轉錄組分析發現,主要涉及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信號通路、MAPK信號通路、Calcium信號通路、血管內皮生長因子信號通路等[11]。
2.2 參與NAFLD-HCC的免疫細胞 NAFLD患者存在衰老現象,衰老細胞能分泌大量的炎癥因子、趨化因子等衰老相關分泌表型 (senescence associated secretory phenotype,SASP),SASP可改變組織局部微環境,從而促進炎癥和組織修復、血管生成、細胞增殖,參與腫瘤的發生發展。前列腺素E2及趨化因子CCL2可以影響自身抗腫瘤免疫功能而發揮促癌作用。SASP會影響周圍實質細胞、基質細胞以及免疫細胞構成腫瘤微環境,從而促進肝癌的發生[12]。
骨髓來源的抑制細胞(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MDSC)具有免疫抑制活性,可使癌癥逃避免疫監測。MDSC可減少T淋巴細胞浸潤腫瘤,從而大大降低免疫檢查點治療的臨床療效[13]。在肝癌患者腫瘤組織和血液中均發現MDSC升高,HCC中的MDSC能夠抑制T淋巴細胞和NK細胞,激活調節性T淋巴細胞。一項研究[14]發現,腫瘤患者肝X受體激動劑GW3965耐藥與MDSC的升高有關,升高的MDSC主要是粒細胞和單核細胞。MDSC還能產生高水平的基質金屬蛋白酶9,從細胞外基質釋放血管生成因子、血管內皮生長因子,促進血管的生長。
中性粒細胞是人體內最主要的固有免疫細胞之一,在炎癥性應答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外周血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比值增高作為機體慢性炎癥狀態的標志,是HCC在內多種惡性腫瘤預后不良的預測因子[15],且在多種腫瘤瘤體中發現中性粒細胞募集和浸潤。可見中性粒細胞浸潤這一慢性炎癥狀態是惡性腫瘤發生的重要因素。來自Hepatology的研究[16]發現,通過DNAase干預和PAD4-/-小鼠兩種方法抑制中性粒細胞細胞外陷阱(neutrophil extracellular traps,NET)形成,并不會改善脂肪變,但是對炎癥有減輕作用,最終降低NASH-HCC的發生,而游離脂肪酸可以促進NET的形成。通過綠色熒光蛋白標記骨髓細胞發現NASH-HCC小鼠在12周前表現出中性粒細胞浸潤、NET形成,而在12周后主要為巨噬細胞浸潤。Bijnen等[17]研究發現,肥胖小鼠的脂肪組織巨噬細胞可以募集中性粒細胞,從而誘導肝巨噬細胞積累,促進NASH的發展。中性粒細胞釋放的彈性蛋白酶和脂質運載蛋白-2通過神經酰胺和CXC趨化因子受體2,介導中性粒細胞在肝內浸潤同時激活Kupffer細胞,推動NASH進展[18-19]。
肝臟內的巨噬細胞在長期慢性炎癥浸潤刺激下可以促進HCC的發生和發展。Kupffer細胞是定居在肝內的固定巨噬細胞。定位于肝竇隙內,肝臟受到損傷時可激活Kupffer細胞,免疫激活后,其表面Toll樣受體與免疫原膜表面配體結合,釋放NO、花生四烯酸、水解酶等協助破壞抗原,同時釋放各種細胞因子,如IL-1、IL-6、TNFα等,Kupffer細胞介導的慢性炎癥反應在肝損傷修復及再生等方面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與原發性肝癌的發生、發展關系密切。
2.3 脂質代謝失調 脂代謝失調是腫瘤發生發展的一個新標志。傳統上認為瓦博格效應(Warburg effect)是腫瘤細胞代謝的主要特征,糖酵解產能是癌細胞能量的主要來源。然而近年來研究發現,腫瘤細胞之所以生長迅速且能快速適應各種逆境,與其代謝重編程密切相關。腫瘤微環境的改變如缺氧、谷氨酰胺和乳酸的含量等均會影響腫瘤細胞的代謝。脂肪酸合成酶(FASN)是一個代謝性癌基因,在多種腫瘤組織中被發現表達升高,FASN抑制劑對腫瘤的治療有積極作用[20]。Beloribi-Djefaflia等[21]對HCC進行了全基因組表達譜和代謝譜分析,發現硬脂酰輔酶A去飽和酶1(SCD1)參與的脂質合成通路與HCC患者的進展和臨床結局顯著相關。膽固醇調節元件結合蛋白-1c參與調控FASN、SCD1、乙酰輔酶A羧化酶(ACC)的表達,也與腫瘤的生長密切相關。
在HCC患者中,侵襲性強的腫瘤組織中可以檢測到脂質生成的異常激活。許多脂肪相關腫瘤在抗血管生成治療方案中表現出很強的耐藥屬性。抗血管生成會引起缺氧致使腫瘤細胞代謝重編程,激活AMPK-ACC-肉堿酰基轉移酶1(CPT1)信號通路,促進脂肪酸代謝供能[22]。ω-3多不飽和脂肪酸可以通過下調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和前列腺素E2的表達減輕血管新生從而抑制肝癌細胞的侵襲和轉移[23]。因此,在脂肪性相關腫瘤中,同時靶向血管生成和脂質代謝治療脂肪性相關腫瘤是一種理想有效的治療模式。
膽固醇也參與了NAFLD-HCC的發生和發展。在飲食誘導的NASH及NAFLD-HCC動物模型中發現,單純高脂飲食僅引起單純的肝細胞脂肪變,而高脂高膽固醇喂養的小鼠發展為NASH。添加膽固醇會促進炎癥因子MCP-1、IL-1β和TNFα的表達。膽固醇會引起Ras、蛋白激酶B、Src、鈣信號的改變及代謝失調從而促進腫瘤的發生發展。此外,膽固醇可以調節不同受體的功能,參與囊泡的轉運。同時膽固醇是類固醇激素的前體,對乳腺癌和前列腺癌具有公認的促進作用。
游離脂肪酸及其代謝產物通過誘導脂質過積累而成為脂毒性的重要介質,脂質過積累導致脂毒性肝細胞損傷和NAFLD的進展。研究發現游離脂肪酸可以上調肝臟MPST的表達,進而抑制胱硫醚-γ-裂解酶/H2S通路,導致NAFLD發生。HCC患者血清的代謝組學分析發現C24∶1(cis-15)神經酸和C24∶0二十四烷酸含量極低,幾乎檢測不到。C23∶0二十三烷酸在前列腺癌患者腫瘤與瘤旁組織的代謝組學分析中發現,在腫瘤組織中的含量明顯高于非腫瘤組織。Lu等[24]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譜-質譜聯用技術,對80例肝癌組織及癌旁非癌組織進行酰基肉堿代謝譜分析,發現在HCC組織中飽和長鏈酰基肉堿增加,短鏈和中鏈肉堿減少。CPT2在HCC組織中表達下降。體外實驗發現,CPT2的下調顯著增強了肝癌細胞的致瘤活性和轉移潛能。在DEN誘導的NASH-HCC小鼠腫瘤組織中CPT2的表達也顯著下調。進一步研究發現,CPT2基因功能異常可造成代謝物酰基肉堿堆積,促進HCC發生。在動物實驗[25]中,將肉堿加入高脂飲食飼料中誘導NASH-HCC模型,發現肉堿可以加重NASH-HCC。提示CPT2缺陷引起的脂肪酸代謝障礙可以促進NASH-HCC的發生,CPT2可以作為NASH-HCC監測和治療的一個靶點。
2.4 腸道微生物 NAFLD患者腸道菌群結構和炎癥有關,表現為擬桿菌和瘤胃球菌科增多,雙歧桿菌屬減少[26]。NAFLD患者腸道細菌的過度生長可促進胰島素抵抗和膽堿缺乏等的出現,并且與脂肪肝嚴重程度相關。肥胖能引起腸道微生物構成和數量改變,增加腸道通透性和血漿內毒素水平,促使脂多糖從腸道轉運至門靜脈系統,依次激活Toll樣受體和NF-кB,促進炎癥及腫瘤的發生。給予抗生素和腸道滅菌可降低肥胖小鼠中的HCC患病率,提示菌群失調在HCC的發病機制中起著重要作用。
隨著代謝組學廣泛應用和發展,許多小分子代謝產物如膽汁酸、短鏈脂肪酸等均被發現與NAFLD-HCC的發生相關。腸道細菌代謝產物脫氧膽酸可以促進DNA損傷,是 SASP 的觸發因子。Yoshimoto等[27]發現抑制脫氧膽酸生成可以抑制肥胖小鼠體內的肝癌生長。腸道菌群的代謝產物也可通過調節宿主免疫誘導NAFLD和NAFLD-HCC的炎癥反應。肥胖誘導的小鼠腸道革蘭陽性菌成分脂磷壁酸移位到肝,可與脫氧膽酸協同作用,促進前列腺素E2通過EP4受體抑制CD8+T淋巴細胞抗腫瘤免疫,促進HCC的發生[28]。從健康人群供體中分離的11個菌株聯合體可以通過誘導IFNγ促進CD8+T淋巴細胞產生進而促進機體的抗腫瘤效應[29]。
多組學技術及生信分析在臨床和基礎研究上的聯用,使NAFLD-HCC的機制研究也更加深入和精準。其中炎癌轉化、脂質代謝重編程、腸道微生物及其代謝產物以及它們在免疫細胞中的相互作用均是NAFLD-HCC目前研究的熱點。針對NAFLD及其相關HCC發病率逐年升高的趨勢,剖析炎癌轉化、代謝改變及肝腸軸在腫瘤發生中的內在機理,確定HCC的功能分子靶點,將有助于NAFLD-HCC的精準預防及開發新的治療策略,以減輕未來的疾病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