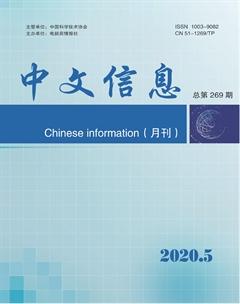論海子詩歌創作主題選擇的三個維度
伋靜
摘 要:在海子詩歌創作中,他的主題選擇獨特而誠摯,這既來自淳樸父母的關愛,也來自鄉村環境的熏陶,更來自具有深厚人文底蘊的北大的涵養。海子的詩歌創作呈現出了博大胸襟和崇高境界,他將自己的生命假以詩歌進行藝術化,并以此作為自己的終生追求。海子力圖以詩歌為方舟,去拯救日益物質化的人類。海子的詩歌是他生命本體與詩歌藝術的合二為一。
關鍵詞:海子 詩歌 主題維度
中圖分類號:I207.2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9082(2020)05-0-02
海子的詩歌蘊藏著誠摯而坦誠的情感,源于他所接受的淳樸的父母之愛和農村鄉土環境的教育,海子把自己的生命藝術化為了詩歌,詩歌又承載了海子的理想和信念,他那充沛的詩歌內涵是其個體生命和詩歌藝術的互融。
一、具有原型意味的景象
海子對于大地有著永遠割不斷的情結,正是基于這一情結,海子的抒情詩里出現了許多帶有大自然元素性質的意象。這是海子對詩人、世界、大地之間關系的揭示。海子的抒情詩中,我們可以看到湖泊、麥子、遠方等意象,感受到詩人率真的情感,領略他那奇譎而優美的語言。這些都反映著詩人海子對生命個體的終極思考,對個體生存困境的深沉感悟,對美好事物的深情眷戀。面對養育他的土地,詩人感受到一種源于內心深處的拷問。正是這個曾經給海子留下了深刻印記,培養了他赤子情懷的大地,促成了海子關于生命意義的思考。
海子找到了大地上生命存在的元素感,把景色中的元素變成詩的呼吸和語言,并對這些元素懷有無可置疑的感恩之情。這樣,海子的詩歌便成為了一個完整結構的藝術生命體。他在實現了對大地生命的詩歌化后,便開始了在大地上空的精神漂泊。他以人類文化為心靈之鏡,折射大宇宙投射于個體生命。于是,天空中的景象便也成為海子抒情詩的主要元素,詩歌題目中就有很多,諸如《夏天的太陽》、《十四行:夜晚的月亮》、《九月的云》、《天鵝》、《雪》、《日出》《云朵》、《北斗七星》等,而在他的詩文里則更多展現了對宇宙的遐想和沉迷。在《夏天的太陽》里,海子把自己與基督聯系起來,在他的臆想中,“我”應該也同當年的基督一樣,拯救這充滿黑暗、需要陽光的世界。海子在他的詩論里也說道:“應拋棄文人趣味,直接關注生命存在本身。這是中國詩歌的自新之路。”
二、深情摯愛的人們
海子的詩有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對他所關愛的事物給以人性化與親情化的處理,從而洋溢著他特有的博愛精神。海子不僅寫詩,而且也真誠地像所寫的“詩”那樣去生活,他愛農村,愛家鄉,愛女性,愛民族,愛這世界上一切他所能愛的人與事物,他的愛在不斷延伸。海子是個地地道道的“愛心詩人”。他寫了許多詩歌送給或獻給他所熱愛的人們,這是對他所景仰或深愛著的人們在心靈和思想上的一種神交和敬重。在他的詩歌題目里,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名字:《寫給脖子上的菩薩》、《給母親》、《阿爾的太陽——給我的瘦哥哥梵高》、《給卡夫卡》、《梭羅這人有腦子》、《遠方——獻給草原英雄小姐妹》、《給托爾斯泰》、《北斗七星 七座村莊——獻給萍水相逢的額濟納姑娘》、《獻詩——給S》、《詩人葉賽寧》、《盲目——給維特根施坦》、《給薩福》、《公爵的私生女——給波德萊爾》、《不幸——給荷爾德林》等等,這些獻詩無一不是詩人博大的胸懷內所充溢的淳樸而熾烈的愛的外露和詩化,是語言在生命化中燒結出的藝術白金。這些詩歌的誕生與海子十五歲以前就初步形成的善良、淳樸、博愛的性格和精神氣質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海子給予他們的愛,正如少年時代故鄉和親人給予他的愛一樣,是質樸而溫暖的。
三、時空的永恒和生命的短暫
生命的短暫相對于時空的永恒是渺小的,而人類卻渴望用短暫的生命在永恒的時空里留下印證他們曾經存在的痕跡,人類于是陷入了對終極價值的思考。這其中自然也包括我們的詩人海子。1987年以后,海子創作的許多短詩,對于生存的孤獨、痛苦和時空轉換進行了深入的思考,濃縮著對于個體生命、整個宇宙以及二者相互之間聯系形而上的考量。看看以下這些詩歌的名字,我們就能感知:《八月尾》、《在昌平的孤獨》、《死亡之詩(之一)》、《我感到魅惑》、《淚水》、《秋》、《秋日黃昏》、《八月黑夜的火把》、《夜色》、《眺望北方》、《七百年前》、《遠方》、《冬天》、《面朝大海,春暖花開》、《黎明(二月的雪,二月的雨)》、《春天,十個海子》……在這些詩歌里面,聚集了海子多方面的情思,有關于愛情的《眺望北方》,有對世俗溫馨向往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但海子思索的最終旨歸并不是世俗的幸福,而是對以“遠方”為象征的永恒時空的眷戀和對死亡的“傾心”。“遠方”是海子詩反復出現的重要形象,這種對于遠方的向往是基于海子對時空的深邃和神性的一種虔誠信仰,對遠方的遙望和尋求則表現出了詩人對生命終極意義的探索。他的精神追求促使他做出了一次次的以感受生命和尋找宇宙神性為使命的青春遠行。在海子的生命行為中表現為對流浪遠方的偏愛,在海子的詩歌中則表現為對空曠、遠方和四季、歲月的反復吟唱。為此,海子進行了以精神追求為目的的“長途跋涉”,可他遠行的地方總是離他的起點很遙遠:四川、甘肅、青海、西藏,這些在地理意義上本就意味著貧窮落后而且空曠荒涼的地方,是他遠行歷程中的驛站。遠行中,他飽嘗了孤獨的滋味,體驗到一種混合著幸福感的痛苦。然而,選擇了遠方和永恒事業的海子注定不會放棄自己的追求,對于擁有一顆赤子之心的海子來說,寫作與生活之間沒任何距離,詩歌就是生命。但是,當他一旦面臨藝術和生命之間不可調和的痛苦時,生命的分量相對于詩歌藝術和他的詩歌理想來說,就顯然太微不足道了,他甘愿承受生命的痛苦來為他的詩歌理想作“一次性”的詩歌沖擊,這樣海子詩歌里的“死亡”意象就不難理解了。
死亡本就是哲學上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海子將死亡意識全部注入作品之中,在海子的創作歷程中,“死亡”這個意象的內涵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存在一個發展的過程。在他早期的詩歌里, 死亡只是一種符號,象征著生命的歸屬,在《亞洲銅》這里,死亡還沒有作為審美的對象進入海子的詩歌。只有在痛苦已經無法使人面對、世界已經無處容身的時候,死亡才被賦予了精神安寧的希望。《肉體(之二)》中,海子想象著,或者說充當了靈肉分離之后靈魂的角色,成為自己死亡的旁觀者。靈肉分離的幻想終究是遮擋不住理性思考和現實苦痛雙重焦灼的,海子的敏感使他在不久之后就敏銳地感覺到了這一點,他在詩歌《淚水》里沉痛地表達了對死亡虛無的困惑。但也正是因為如此,對于沉陷在痛苦中的海子來說,它是一種永遠的誘惑。海子在他最后一首抒情詩《春天,十個海子》里說:“這是一個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傾心死亡/不能自拔”,任何一位選擇遠方和永恒事業的人,注定無法解開有限的終極意義、生命短暫與時空永恒之間的死結;這時,死亡也便順理成章了。可以說,海子的短詩不是策略性的寫作,而是完全自發的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