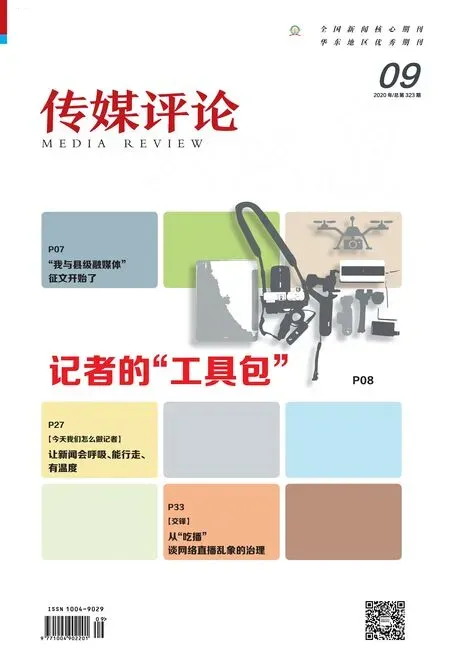都2020年了,記者的采訪包里放些什么?
文_林斐然
寫完這個題目突然想起兩件有趣的瑣事。一件發生在3年前,我去云南某個偏僻的鄉鎮采訪,遇上了一位基層干部,他上下打量了我許久,看得出來忍著沒好意思開口,最后在返程的車上,他私下問我,“林記者,你的攝像機放在哪里了?”
另一件事發生在今年。春節回老家,一位遠房長輩聽說我是記者以后,打趣地說,“聽說記者出門都要背大相機的,你的相機怎么不拿出來,給我們拍拍照片,讓我們也上一下報紙啊?”
這兩件事未必真反映了什么共同看法,只是回想起來感到有趣,似乎大家對記者的印象幾十年如一日,不是舉著攝像機,就是背著大單反。這“兩大件”一左一右,仿佛已經成為證明記者身份的標配。
話說回來,一轉眼都21世紀20年代了,當代記者的工具包里面,到底應該放些什么東西呢?時代變遷,記者除了硬件迭代,在軟件上又有哪些利器能派上用場呢?
從文字到視頻,越來越重的書包
剛入行的時候,我在國內一家新聞網站做記者。由于沒有專門的攝影記者,大部分時候都需要自己拍照片。于是我出差的標配是一臺筆記本電腦、本子、筆、各式證件,還有尼康D90相機。
最重的部分可能就是單反相機了。那時候我喜歡用18-105mm的鏡頭,它能適用大部分常規新聞場景。非要說缺點,就是相機太重,我習慣出差只背書包,以保持較好的靈活機動能力。出差時往往東奔西走,一背好幾天,加上厚重的筆記本和換洗衣物,壓得我肩膀生疼。
來新京報以后,書包的負重量得到了很大減輕。由于有專門的攝影記者,加上2015年以后,手機像素不斷提高,情急的時候,哪怕沒有攝影記者幫忙,掏出手機拍點救急的照片,一般來說也能“堪大用”。沉重的單反相機反而被我掛上二手網站賣掉了。
很多時候,孤身深入新聞現場,經常會有自己是“特種部隊”的感受。長途跋涉需要應對各種突發狀況,除了常備的換洗衣褲等,我還習慣帶上壓縮餅干、礦泉水、雨傘、創可貼、感冒藥等應急道具。
在各色受災地區采訪時,對住宿很難有要求,經常有今晚沒明晚,清晨負重出發往往沒有回頭路。所以每次出門,我都要帶走自己所有的東西。

2017年新京報記者上全國兩會攜帶的設備
書包最重的時候,可能還是自2016年下半年開始。彼時新聞直播正在野蠻生長,哪怕移動直播從大型直播車轉入手機,出門需要攜帶的東西還是不少:某品牌移動云臺、備用云臺電池、直播手機、移動電源、三腳架、桌面腳架、攝像燈、小蜜蜂麥克風、運動相機、各色充電設備、筆記本電腦、牙刷剃須刀等生活用品,最后還需要另外準備一個箱子裝大疆精靈4無人機。所有的裝備得有四五十斤,所幸書包的質量還不錯,從來沒有被撐破過。
這些裝備的用途也可以簡單描述下,以我曾經在江西景德鎮發起的水災單機直播為例,我需要穿著半身雨褲,背著書包涉水進入小區。這時候我可以在高處放置一個三腳架,插上充電電源作為空鏡過渡畫面使用,右手持云臺,外接小蜜蜂單機采訪直播,左手可以撐起雨傘,保證自己全身干燥。在隨后趕來增援的拍者的配合下,我找到一個雨水稍微緩和的間隙,使用無人機航拍現場,完成了現場單機直播。
這里插入一個小技巧,即出差一定要帶現金,在邊遠地區、災區現場,很多時候沒辦法保證網絡信號,準備一疊現金很有必要。
我一度前胸背書包,后背背著無人機盒,進過河北、江西、湖北等好幾個省的洪災現場,跋涉過幾十公里破碎山路進入災區。碰到接近胸口的水位,就把書包頂在頭上,想辦法趟過去;碰到大雨,就找個塑料布包一下自己的書包;日常手機的電量要隨時保持充沛,有必要的時候,還需要負重臨時開機發起直播。
那時候書包實在太重,除了跋涉時經常覺得不堪重負以外,晚上把書包放下那一刻,都有一種得到解脫的感受。
戰術迭代:從“單兵”到“群狼”
在2015年的時候,新京報試圖打造過一批“全能型”記者,即一個記者單兵作戰,能完成多種工作,圖文、視頻,業務能力全面均衡。在設想里面,這批記者應該像“尖刀”一樣,扎進新聞現場,分批分次,源源不斷地為后方提供用之不竭的現場素材。
這種姑且稱之為“單兵作戰”的要求,對于大部分記者來說實際上難度太高:記者抵達前方,完成直播后,還需要處理文字網絡快訊、報紙版面、拍回現場圖,并且執行短視頻任務。
然而在多次實戰中我們發現,互聯網信息時代里,新聞爭奪最激烈時往往以分秒計數,一個人實在分身乏術,效率也有參差不齊的地方。
意識到這一點以后,單位很快就由“單兵作戰”換成了“群狼戰術”:前方有了更多的搭檔,除了記者,還有拍者配合完成工作,后方有了專門的記者負責對接統籌協調,前后方配合,形成了“前方+后方”“統籌+編導+記者+拍者+編輯”的聯動模式,融合起來完成采訪工作。
在前方記者采編人數充沛的情況下,原本單人采訪時應該背負的設備,就能由兩個人分擔。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甚至不少時候,等飛機一落地就租車趕往現場。設備往后備廂一丟,盡可能幫助記者“輕裝上陣”,讓他們在新聞現場移動起來更輕便一些。
以今年7月,中國首次火星探測任務“天問一號”探測器直播方案為例。“我們視頻”直播組從5月初開始,從直播點位、直播設備以及流程等進行全方位的籌備,提前與航天科技集團、北京天文臺以及海南當地媒體做好聯絡和溝通工作。在前后方群策群力之下,前方記者常卓瑾、李陽與拍客團隊4人定了三個極佳直播機位,拿到第一手的發射現場畫面,多維度地展現了“天問一號”探測器成功升空。

2018年新京報記者上全國兩會攜帶的設備
在發射前一周,遠望7號測量船曾抵達任務海區進行1:1模擬演練,進行人員訓練和設備維護等系列準備工作,我們還派出記者賈潔卿在遠望7號測量船進行隨船報道。發射前,記者賈潔卿發來海上演練時的7分鐘全網獨家珍貴畫面。
7月23日12時41分,前后方在確保直播安全性的前提下,第一時間向受眾傳遞發射場現場畫面。拍客團隊采用佳能c200電影機、索尼N280攝錄一體機、外加適馬150-600焦段鏡頭、V66直播機,V68 5G直播機,將發射升空前后約5分鐘的圖像順利回傳播出。
發射后30分鐘內,后方編輯李家桐在統籌安排下,處理多角度直擊火箭發射升空畫面混剪視頻,90秒短片在官宣發射成功后,面向全網分發與傳播,并附帶現場發回的照片,分批制作成數字海報和小視頻,進行二次傳播。
后方演播間則提前請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航空宇航推進理論與工程博士陳亮、遠望7號船副船長陶華堂、中國航空學會《航空知識》主編王亞男、北京天文館副研究員劉茜等嘉賓做客直播間,多維度討論火星探測計劃以及未來“天問一號”成功登陸火星的過程。整場直播可謂是一套密集的群體組合拳。
當然,此處不得不說到一些可能看起來時新,但是更像“繡花枕頭”,實戰用處有限的裝備,比如:VR眼鏡、谷歌眼鏡、直播眼鏡等等。相比之下,在垂直領域上,可能翻譯筆、運動相機(Go Pro)、全景相機(Insta 360)、海事衛星、無線對講機此類的裝備更有自己的用武之地。
但不得不說,時下對移動直播和短視頻的質量要求在不斷提升,不少時候記者為了考慮直播的信號穩定,還需要TVU設備和聚合器,甚至有時候手機也不太夠用,要帶上攝像機。
不過,我最喜歡的新聞邏輯依然是:先到現場就是王道。哪怕你用過氣的低像素手機,拍出了一段質量堪憂的畫面,采訪了核心當事人,這對于尚處于一片空白的資訊市場來說,依然具有極大的吸引力。
互聯網帶來的無限可能性
前面說的大多都是硬件,新時期,“軟裝備”在采編過程中,也大有用武之地。對于大部分新聞從業人員來說,互聯網檢索能力、各色軟件的運用能力,是新時代賦予這個職業的更高挑戰。
以百度地圖為例,同樣一款軟件在有的用戶手里只能導航,而在有的用戶手里,卻能成為找到目擊者的工具。
舉個很簡單的案例:9月8日,石家莊某區某兩條大街的交叉口出現大量油污,由于是早高峰時間,致使多名路人經過此處時滑倒。事發早高峰,街面上大多數又都是隨處移動的上班族,我們在千里之外怎么找到目擊者?
這里我給出幾個比較常規的采訪路徑:①通過微博、快手等能夠實現精準定位的社交平臺,以發布位置和發布時間為限,迅速鎖定范圍;②使用百度或者高德等地圖軟件,確認位置,聯系附近商戶,必要時可以打開街景畫面,從畫面中找到場景契合點,確認事發地;③大眾點評和美團外賣能聯系上不少附近的商家,他們也可能目睹到了事發經過;④找個跑腿小哥,去現場看一看,雖然不如記者自己親臨現場方便,也比在千里之外干著急來得強;⑤也是最常規的一種,直接聯系相關部門,如交通、環衛、醫療等多個部門,獲取權威消息。
這只是一種常規的新聞連線采訪操作手法。相比之下,一些精準的檢索模式,如通過百度搜索引擎檢索時,一個簡單的雙引號可能也能為工作節省下大量時間:雙引號可以強制檢索引號內部的內容,而不會將查詢詞拆分,引起過于寬泛的聯想,從而混入其他的邊緣檢索結果。
再舉個可能不太容易想到的方法:按現在微信的普及程度,在邊遠地區找人,可能你只需要一個修改坐標軟件,加上微信“附近的人”輔助即可。如果擔心微信找人不太靠譜,你甚至可以試試注冊一個新的用戶賬號,然后用陌陌和事發地附近的用戶聊聊,可能對于尋求采訪線索都有很大的幫助。
一定要列一個對于采訪有所助益的軟件清單的話,我可能能列出長長一串:微信、微博、支付寶、QQ、抖音、快手、珍愛網、陌陌、知乎、人人、秒拍、網易云音樂、天眼查、餓了么、美團外賣、大眾點評、百度地圖、兩步路、我愛我家等等。
具體的用法就不一一展開了,大部分軟件為了擴寬社交功能,都煞費苦心。即使我們沒有辦法進入到它們的中臺和后臺,但是只要把軟件常規功能挖掘到極致,利用互聯網,我們也能夠實現原本需要花費很大力氣,跋涉很遠路途才能尋求到的“真相”。
裝備什么都不如裝備大腦
雖然花了很大的篇幅介紹新聞采訪中可能會用到的硬件和軟件,但是我仍然執著地認為,對于時下的新聞業來說,更多的從業人員需要的依然是經驗,干活時候帶上腦子,用心做好工作,多專情于職業化技法學習,比帶上五花八門、種類繁多的工具更重要。
埃及記者Ali Sotouhi曾經制作過一個調查紀錄片叫做《東方之門》,講述了敘利亞難民的故事,他主要的道具就是普通的智能手機。實際上,移動報道的本質是數字敘事和工具的結合,采編裝備未必需要迭代到極致,反而如何用好這些工具,把它們用得恰到好處,值得我們去反思。
聊天的時候,我經常會說起“器”和“術”的區別:裝備常見常新,是為“器”,船堅炮利固然可以衛土守疆,但器總有跟不上的時候,最重要的不在于此,而在于新聞技法、經驗、判斷,甚至是知識的儲備上,在于對新聞的熱情、對事實的追問、對海量信息的甄選、對社會正義的追尋之上。
在人類不能完全依賴AI,實現生活完全托管之前,人,才是這個世界的主體和本源。

2019年新京報記者上全國兩會攜帶的設備
用更好的工具的初衷,是為了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主旋律。我們國家在歷史長卷里面留下的許許多多腳印,幾代人的篳路藍縷,目標和初心從沒有變過。尤其是時下,經濟、司法等改革均已踏入深水區,人們在變軌期留下的故事,在當下叫做新聞,在明天就應該叫做歷史。
時至今日,各色“中央廚房”、“融媒體”、“采訪神器”、5G采訪車等設備層出不窮,一件比一件先進,一代比一代造價高昂。看起來媒體配置的裝備越來越齊備了,但有多少人坐下來仔細反思,這些時代和資本的潮水退去以后,沙灘上到底還留下多少能給受眾帶來深刻印象的新聞產品?這些產品,又能否真正從多個維度,充分揭示各類新聞背后的基礎事實?
在信息爆炸的時代,低端工種很可能會被迅速取代。一方面,我們當然不能放棄對于新科技的追逐,要把全新的工具發揮到極致,結合采編技法,改善工作效率,再造生產流程;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考慮,在四肢裝備齊整了之后,到底要用什么來填充我們的大腦?我們對世界的認識論、對生活的經驗主義、對新聞價值的再判斷,到底能不能跟上時代滾滾向前的車輪?
清代方苞26歲的時候,與友人書,坦言自己“誠恐神智滑昏,學殖荒落,抱無窮之志而卒事不成也”,擔心“無所得于身,無所得于后,是將與眾人同其蔑蔑也”。可見,十年一日,保持學習和向上的動力,是君子卓爾不群的力量本源。
再年輕一點的時候,我一度是個技術狂熱者,相信時代必由技術推動。直到工作了這么些年,再回過頭來看看,感悟卻開始返璞歸真:裝備什么,還是不如裝備自己的大腦有價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