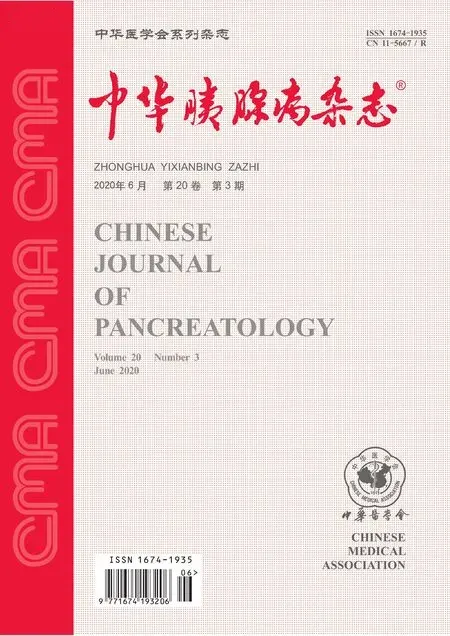高三酰甘油血癥性急性胰腺炎的基因學研究進展
楊鑫敏 黃偉,2
1四川大學華西醫院中西醫結合科,成都 610041;2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臨床研究管理部生物樣本庫,成都 610041
【提要】 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飲食結構的改變,高三酰甘油血癥性急性胰腺炎(hypertriglyceridemic acute pancreatitis,HTG-AP)的發病率逐年升高。HTG-AP患者具有年輕化、重癥化、預后差、易復發等特點,造成巨大的衛生經濟負擔。HTG-AP的發生機制尚不明確,基因多態性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已鑒定出的高三酰甘油血癥易感基因有LPL、APOC2、APOA5、LMF1、GPIHBP1和GPD1,胰腺炎易感基因有PRSS1、PRSS2、SPINK1、CTRC、CFTR、CASR、CLDN2、CPA1、CEL、CTRB和PNLIP。近年來,HTG-AP患者的基因檢測不斷發現新的易感基因和突變位點。遺傳基因異常、遺傳易感性與環境危險因素的相互作用影響HTG-AP的發生、病程和結局,基因評估正變得越來越重要,對分子機制、預后評估、藥物開發和基因治療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AP是最常見的消化疾病之一[1],重癥者常出現胰腺壞死、多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征和膿毒血癥,病死率>30%[2-3]。AP的發病率逐年增高,病因以膽源性和酒精性為主[4-5],近年來隨著我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飲食結構的改變,中心性肥胖[6]和代謝綜合征[7]普遍存在,高三酰甘油血癥(hypertriglyceridemia,HTG)成為AP最重要的病因之一[8],在新近的大型隊列中占1/3及以上的構成比[9-12]。目前用于診斷高三酰甘油血癥性急性胰腺炎(hypertriglyceridemic acute pancreatitis,HTG-AP)的三酰甘油(triglyceride,TG)水平尚無統一標準[13]。東部戰區總醫院李維勤教授團隊[14]和南昌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呂農華教授團隊[15]以TG≥11.3 mmol/L作為診斷標準。四川大學華西醫院以入院24 h內TG最高水平≥5.65 mmol/L作為診斷標準[11],HTG-AP占比32.8%,而TG水平≥11.3 mmol/L占比22.2%。HTG-AP在病程上與其他病因導致AP相似,但患者呈年輕化、重癥化態勢,其持續性器官功能衰竭[11,16]、多器官功能衰竭[11,17]、胰腺壞死[11,18]、新發糖尿病[11]發生率及病死率[11,18]均高于非HTG-AP患者,約1/3的HTG-AP患者為復發性AP(recurrent AP,RAP),部分進展為CP[18]。HTG-AP的基礎治療與其他病因相似,包括禁食、胃腸減壓、液體復蘇、止痛、營養支持等,急性期特異治療方案以迅速降低循環TG水平為主,包括血漿置換、胰島素、低分子肝素以及降脂藥物等的使用[19-20]。后續治療為病因特異性靶向治療,包括調整生活方式、應用降脂藥物和基因治療等[19-20]。針對HTG-AP的隨訪研究發現,TG水平升高與復發風險顯著相關[21-22],患者應在治愈后盡早監測血脂并盡量維持其循環TG水平在5.65 mmol/L以下[23-24]。HTG-AP的發生機制尚不明確,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遺傳易感性、遺傳與環境的相互作用影響HTG-AP的臨床發病、病程和結局。隨著測序技術的不斷發展,陸續有新的易感基因被報道,從基因多態性溯源,結合環境暴露進行風險分析,對HTG-AP的發生風險、預后評估、改進治療、早期干預和預防復發將具有重要臨床指導意義。
一、HTG的流行病學、分類及分子機制
HTG是常見臨床綜合征,主要表現為血TG水平超過正常值1.7 mmol/L,成人患病率為10%~20%[25-26],我國數據為20%~40%[27]。輕度到中度的HTG是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險因素[28],重度HTG增加AP的發病風險[25]。重度HTG的定義在不同的指南之間有一定差異,中國和美國的指南均以11.3 mmol/L為閾值,而歐洲指南為10 mmol/L[25,29]。傳統的Fredrickson分類(即WHO分類)根據脂蛋白定量分析將高脂蛋白血癥(hyperlipoproteinemia,HLP)分為6型(1型、2A型、2B型、3型、4型和5型)。而臨床醫師更傾向于根據脂質異常類型分類,分為高膽固醇血癥、HTG和混合型高脂血癥,并進一步根據病因將HTG分為原發性和繼發性[29]。原發性為原因不明或遺傳所致,繼發性的病因主要包括肥胖、糖尿病、大量飲酒和藥物(雌激素、第二代抗精神病藥、抗抑郁藥、異維甲酸、羅格列酮、類固醇、噻嗪類、β受體阻滯劑等)[29]。
HTG的發生與TG代謝密切相關,即TG合成異常、降解障礙或兩者兼有,反映了TG利用和供應之間的不平衡。小腸黏膜上皮細胞吸收食物中脂肪合成TG,并組裝成富含TG的乳糜微粒(chylomicrons,CMs)經淋巴入血,即外源性TG;肝臟以游離脂肪酸為原料合成TG,并組裝成極低密度脂蛋白(very low density lipoprotein,VLDL)入血,即內源性TG;CMs和VLDL統稱富含三酰甘油的脂蛋白(triglyceride-rich lipoprotein,TRL)[30]。血中TG是機體恒定的能量來源,在脂蛋白脂肪酶(lipoprotein lipase,LPL)作用下分解為游離脂肪酸供機體利用供能和進入脂肪細胞合成TG儲存。LPL作為脂質代謝的關鍵酶(圖1),在實質細胞中以非活性的單體形式合成,在特定分子伴侶脂肪酶成熟因子1(lipase maturation factor 1,LMF1)的作用下形成有活性的二聚體形式,后者通過糖基磷脂酰肌醇錨定高密度脂蛋白結合蛋白1(glycosylphosphatidylinositol-anchored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binding protein 1,GPIHBP1)結合到血管內皮細胞表面,形成TRL的“結合脂解位點”。此外,LPL發揮正常的水解作用還需載脂蛋白(apolipoprotein, APO)A5穩定該“結合脂解位點”結構,以及特定的輔助因子APOC2進行活化[31]。另一方面,LPL二聚體不穩定,可自發或通過與血管生成素樣蛋白3(angiopoietin-like protein 3,ANGPTL3)相互作用而解離成非活性單體。LPL還受到APOC3的抑制,后者與LPL競爭脂蛋白表面的空間[31]。在糖異生過程中,3-磷酸甘油脫氫酶(glycerol-3-phosphate dehydrogenase,GPD1)催化三磷酸甘油(glycerol-3-phosphate,G3P)到二羥基磷酸丙酮(dihydroxyacetone phosphate,DHAP),而G3P是TG合成的重要底物。
二、HTG的基因背景及易感基因
基因檢測被廣泛用于鑒定HTG的基因變異,包括Sanger測序(Sanger sequencing)、第二代測序(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NGS)、全外顯子組測序(whole exome sequencing,WES)、全基因組測序(whole genome sequencing, WGS)、基因分型(genotyping)和多基因風險評分(polygenic risk score,PRS)[32-33]。全基因組關聯分析(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GWAS)是在全基因組范圍內找出存在的序列變異,即單核苷酸多態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也被用于HTG遺傳位點的分析[34-38]。以基因為中心的GWAS的薈萃分析進一步擴展和闡明不同形式的HTG遺傳基礎,標志著HTG的基因學研究已經進入后GWAS時代[38-40]。環境暴露因素,如吸煙、酗酒等,和基因在HTG的相互作用也被證實[41-42]。
總的來說,HTG表型受多種基因變異(常見和罕見)累積以及繼發性因素的復雜網絡調控[29,43]。具體來說,重度HTG,特別是發生在兒童和青少年階段,更可能與單基因變異相關;而輕度至中度的HTG則更有可能以多基因變異為基礎,并與繼發性因素相關。家族性乳糜微粒血癥綜合征(familial chylomicronemia syndrome, FCS;HLP 1型),又稱LPL缺乏癥,即單基因變異,表現為罕見的典型常染色體隱性遺傳,人群患病率為1~10/100萬,即其基因通常是純合或復合雜合的,由6個調節TRL分解代謝的基因(LPL、APOC2、APOA5、LMF1、GPIHBP1和GPD1)發生大范圍的導致嚴重功能缺失的突變引起,其中LPL缺失占80%的病例。但是傳統的家族性HTG不再被認為是單基因變異,而表現為多基因變異的累積效應。大部分重度HTG具有復雜的多基因易感性,盡管沒有表現為上述影響顯著的單基因變異引起的孟德爾遺傳,但往往在家族中聚集。其基因基礎除了上述6個典型FCS基因中具有大效應的罕見雜合變異外,還包括具有小效應的常見變異的累積作用。常見的輕度至中度HTG也是典型的多基因型,由30多個基因中常見和罕見變異的累積負擔引起。然而,致病突變的雜合攜帶者具有非常廣泛的TG表型,從正常水平到嚴重HTG,可能是由于不同數量的常見變異的隨機共遺傳,這種復雜的多基因易感性可通過PRS量化。

注:LPL為脂蛋白脂肪酶;LMF1為脂肪酶成熟因子1;GPIHBP1為糖基磷脂酰肌醇錨定高密度脂蛋白結合蛋白1;APOA5為載脂蛋白A5;APOC2為載脂蛋白C2;ANGPTL3為血管生成素樣蛋白3;APOC3為載脂蛋白C3;TRL為富含三酰甘油的脂蛋白; GPD1為3-磷酸甘油脫氫酶;G3P為三磷酸甘油;DHAP為二羥基磷酸丙酮;TG為三酰甘油
圖1 三酰甘油代謝示意圖
HTG的繼發性因素,如肥胖、糖尿病等,可進一步促使重度HTG的發生。值得注意的是,某些繼發性因素除了本身引起HTG發生以外,常與多基因易感性相互作用,最終導致的HTG表型與潛在遺傳風險因素的累積效應和繼發性因素的強度有關。
三、基因組學在HTG-AP中的應用
基因突變也是驅動AP、RAP和CP在自然病程上形成一種疾病連續狀態的重要因素。2012年Whitcomb等[44]開展了第一個CP的GWAS研究,報道了酒精性和特發性CP風險增加的常見基因突變之后,針對特殊人群CP的GWAS研究也有陸續報道[45-48]。CP基因研究表明,大多數風險基因編碼消化蛋白酶、胰蛋白酶抑制劑以及其他在胰腺高表達的蛋白質,主要有絲氨酸蛋白酶1(serine protease 1,PRSS1)、絲氨酸肽酶抑制因子Kazal型1(serine protease inhibitor kazal-type 1,SPINK1)、糜蛋白酶C(chymotrypsin C,CTRC)和囊性纖維跨膜轉導調節子(cystic fibrosis transmembrane conductance regulator,CFTR)。功能學研究根據CP發生發展的病理通路進一步將各種基因變異分類(圖2),其中PRSS1、SPINK1和CTRC與胰蛋白酶依賴通路相關,PRSS1、胰腺脂肪酶(pancreatic lipase,PNLIP)、羧肽酶A1(carboxypeptidase A1,CPA1)和羧基酯脂肪酶(carboxylester lipase,CEL)與蛋白錯誤折疊依賴通路相關,CFTR、鈣敏感受體(calcium sensing receptor,CASR)和緊密連接蛋白2(claudin 2,CLDN2)與導管相關途徑有關[49-50]。海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李兆申、廖專教授團隊的一系列研究證實遺傳因素與CP密切相關,并發現中西方人群變異類型差異較大[51-58]。SPINK1是中國CP的主要致病基因,約占60%,其中c.194+2T>C突變顯著增加CP患病風險,該突變在亞洲人群和特發性CP患者中作用更為顯著[51-53]。他們進一步在動物模型證實攜帶該突變的純合小鼠致死,而雜合小鼠發生自發性CP[59]。此外,他們在亞洲人群中并未發現歐洲人群中的CEL-HYB1等位基因而是存在一種新類型(CEL-HYB2)[54],且德國人群中的CPA1功能缺失型突變和歐洲人群中CTRBl-CTRB2基因倒置變異在我國人群無顯著差異[55-56]。該團隊新進發現鈣信號通路相關瞬時受體電位陽離子通道蛋白Ⅴ型亞家族成員6(transient receptor potential cation channel,subfamily Ⅴ,member 6;TRPV6)突變與CP易感性相關[58]。此外,炎癥(白介素、腫瘤壞死因子、Toll樣受體等)、氧化應激(環氧化酶、血紅素加氧酶等)、凋亡(含半胱氨酸的天冬氨酸蛋白水解酶等)、血管生成、緊密連接等相關的修飾基因也參與CP發生發展的調控。

注:PRSS1為絲氨酸蛋白酶1;PRSS2為絲氨酸蛋白酶2;CTRC為糜蛋白酶C;SPINK1為絲氨酸肽酶抑制因子Kazal型1;Ca2+為鈣離子;CASR為鈣敏感受體;H2O為水;Na+為鈉離子;CLDN2為緊密連接蛋白2;Cl-為氯離子;HCO3-為碳酸氫根離子;CFTR為囊性纖維跨膜轉導調節子;CPA1為羧肽酶A1;CEL為羧基酯脂肪酶
圖2 胰腺炎風險基因及相關病理通路
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流行病學研究發現重度HTG可以在無其他因素并存時發生HTG-AP,罕見的FCS患者發生HTG-AP的風險最高;HTG-AP通常發生在TG異常且伴有其他繼發性HTG病因的患者中,如肥胖、糖尿病等;大部分AP患者的TG水平相對較低,還存在其他能導致HTG、也可能直接導致HTG-AP的因素,如飲酒、膽結石疾病或某些藥物治療。在病理生理學上,雖然“脂毒性”和“微循環障礙”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HTG-AP的發生機制,但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導致針對性預防及治療難有突破性進展。與此同時,基因多態性在HTG-AP中的致病作用日漸顯著。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李建軍教授團隊[60]檢測了103例原發性重度HTG患者和46例配對健康人群的15個TG相關的基因序列,并進一步納入AP病史進行分析,發現重度HTG患者罕見基因變異檢出率顯著增高,且具有AP病史的患者LPL基因及所有LPL調控基因罕見變型頻率較高。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翁昭旼教授團隊[61]對46例HTG-AP患者和80例HTG患者的基因檢測分析發現,CFTR突變及腫瘤壞死因子啟動子多態性和HTG-AP發生相關。東部戰區總醫院李維勤教授團隊[62-64]對HTG-AP患者進行測序發現了LMF1、LPL基因新的突變位點。載脂蛋白E等位基因多態性也被報道與HTG-AP相關[65]。總的來說,HTG-AP的基因學現狀有如下幾點:(1)基因學的研究報道以個案報告為主,人群隊列研究較少,目前尚無針對HTG-AP的GWAS研究。(2)研究報道的HTG致病基因和新突變位點明顯多于AP基因;修飾基因及其功能在HTG-AP發生中有一定作用。(3)基因多態性和環境暴露因素存在相互作用。
已經鑒定出的HTG和胰腺炎相關基因為探討HTG-AP發生機制提供了分子基礎,有助于提高對其病理生理學的理解,進而開發新的更有效的藥物治療或管理策略。Wang等[66]運用具有重度HTG表型的Lpl基因缺陷小鼠,發現其對于雨蛙素誘導的急性壞死性胰腺炎小鼠具有更強的易感性,在其他研究中也得到了一致結果[67-69]。Liu等[70]和Wu等[71]分別運用ApoC3過表達小鼠誘導AP模型,發現其較野生型小鼠具有更嚴重的胰腺病理損傷和腎損傷。Yang等[72]運用Gpihbp1基因敲除小鼠發現HTG延遲了雨蛙素誘導AP模型的胰腺損傷恢復和胰腺再生,且早期使用降脂藥物非諾貝特具有改善作用。Zhang等[73]聯合運用Gpihbp1基因敲除小鼠和ApoC3過表達小鼠,發現前者的TRL顆粒更大,并與HTG-AP的嚴重程度相關。越來越多的基因模型被用于HTG-AP研究,將為明確其病理機制并發現潛在的治療靶點提供更多的思路和證據。
另一方面,HTG基因治療已經邁出重要一步。阿利潑金(alipogene tiparvovec)是歐洲首個被推薦上市的基因治療藥物,通過肌肉注射攜帶LPL的腺病毒介導局部LPL表達,已被批準用于FCS的治療[74]。其他基因治療HTG新療法,如微粒體三酰甘油轉運蛋白抑制劑洛美他派(lomitapide)、靶向APOB的米泊美生(mipomersen)、針對APOC3和ANGPTL的生物制劑,也在相繼開發中[75-77]。
四、對HTG-AP基因組學研究的思考及展望
對于臨床疾病治療和管理而言,盡管有研究認為脂質水平本身就足以指導臨床實踐,但是一個明確的基因診斷可以協助醫師針對個別患者提供個性化管理,針對單基因型突變提供新治療手段,以及減少治療延誤,早期預防延遲并發癥。對于個體而言,遺傳風險信息也可能有助于提高依從性,加強患者對疾病的認識,允許提前規劃,在心理及情緒準備方面也有一定作用。對家庭成員也有影響,可幫助評估計劃生育潛在風險。然而,基因檢測實際上面臨諸多困境,如檢測的假陰性和假陽性、倫理問題、費用昂貴和缺乏相關政策等。盡管如此,筆者仍然建議對合適的HTG-AP患者行基因檢測。例如對遺傳風險評分較高的HTG-AP患者家庭,可對已知的致病基因進行測序,以鑒定這些位點與HTG-AP相關的所有變異;對遺傳風險評分較低的HTG-AP患者家庭,可在WES和WGS水平進行測序,以確定新的變異位點。操作要點如下:(1)對所有AP病例,哪怕已有其他明顯病因,都應檢測血脂水平,并盡可能檢測APO水平。(2)詢問并整體評估HTG-AP患者的既往史、家族史、個人史特別是生活方式,以獲得更多遺傳和環境危險暴露因素相關信息。(3)目前尚無統一的對HTG-AP患者及家庭成員行基因檢測的指征,推薦指征為:早期發病、無其他明顯繼發性病因、明確家族史、臨床表現異常嚴重、其他高脂血癥綜合征表現,有助于申請新藥、改變治療策略、早期提供干預指導以及患者要求等。(4)對于HTG-AP基因檢測獲取的信息,可與WES和WGS測序研究整合,有助于發現新的候選基因。
綜上所述,基因學研究增加了HTG-AP患者進行精準醫療的可能,臨床醫師可根據個體基因組成和分子表型進行評估、診斷和治療。表觀遺傳學整合基因組學、轉錄組學、蛋白質組學、代謝組學和臨床表型數據,可能為HTG-AP等復雜性疾病提供新的研究方向和診治策略。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