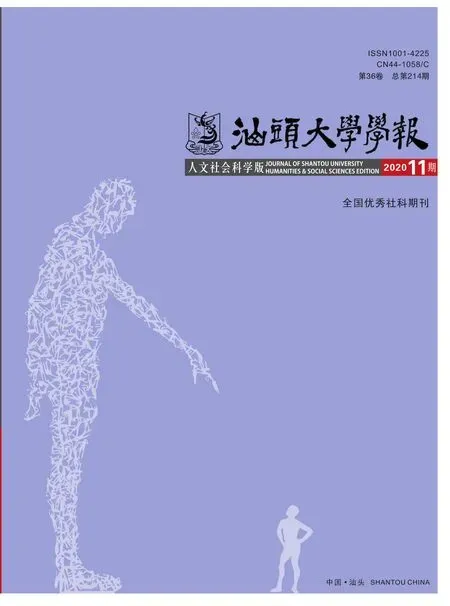基于微博段子的公眾危機情感調適
鄔心云,陶 章
(廣州體育學院體育傳媒學院,廣東 廣州 510075)
公共危機發生以后,正常的社會運轉秩序往往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公眾的日常生活也發生不同程度的變化。公眾面對和處理危機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調適自己適應危機的過程。
新冠肺炎疫情初期,隔離生活大大壓縮了公眾的線下活動范圍,公眾紛紛轉至線上空間滿足信息獲取、人際交往、娛樂等需求,以廣場型討論、鼓勵陌生人交往為特征的微博再度獲得公眾的青睞,出現了各種與疫情有關的話題討論、情感傾訴和分享的內容。其中,段子在眾多內容中尤為凸顯,其娛樂的內容和呈現方式與嚴峻的疫情相違背,段子中隱藏的平靜、友好,甚至輕快的情感與當時恐懼、悲愴的社會氛圍形成鮮明對比。段子的出現和傳播,對于疫情期間的公眾接受危機事實、適應危機生活有何影響?本文將從危機時期公眾情感適應的角度探討新冠肺炎微博段子的現實意義。
一、相關研究綜述
本研究探討的是危機應對和情感產生及進化相關領域的問題,上述領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應對(Coping)這一概念最早萌發于19 世紀Freud 對防御機制理論的描述中,[1]后續的研究中有學者認為這是一種對環境刺激的反應,[2]或認為是對環境變化的適應過程。[3]目前對學界定義“應對”有三種取向,分別是心理特質論、過程論和交互作用論。其中,過程論認為應對是一個涉及情境評價的多維多變的動態信息加工,包括應激源(發生了什么)、認知評價(對個體的影響)、應對策略(實驗性后效假設)、應對行為(應該怎么做)、后效(適應與否)等過程,強調由于實際個體活動的不斷改變,個體與應激情境的關系、個體對應激源性質的評價也不斷改變,繼而應對也會有相應調整。[4]2在應對策略和方式上,Folkman 和Lazarus從功能主義出發區分了兩種:問題聚焦模式和情感聚焦模式,前者涉及處理壓力的來源,后者是試圖處理和壓力有關的想法和情感。[4]171-184Carver等人認為應對策略應該包含更多不同的模式,[5]把個體的應對方式分為14 種,分屬于四大類。[6]研究表明,個體應對方式的選擇受到個體因素和情境因素的影響。[7-10]在應對的影響上,研究普遍認為應對在緩沖壓力事件對個體的消極影響中的作用明顯。在壓力情境和適應之間應對起著重要作用,[11]能夠直接影響心理和軀體困擾,[12]也能通過自我效能感、心理彈性、自尊而間接影響心理健康。[13]基于此,本研究將從危機應對的角度對新冠疫情期間公眾的社交媒體使用行為進行分析,具體探討新冠肺炎微博段子傳播的危機應對意義。
情感(emotion)在20 世紀70 年代開始受到社會學家們的關注和系統研究,[14]1學者們曾用情操、心境、感情、情感體驗等有關的詞語來表述這一心理現象,[14]2人類在形成社會紐帶和建構復雜社會結構時對情感有明顯的依賴。[14]220從社會學的角度看,情感的組成成分包括:身體系統的生理激活、社會建構的文化定義和限制、語言標簽的內部感受、外顯的非語言表達以及對情境中客體或事件的知覺和評價。而認知取向是近年來情感研究的主要取向,該取向逐漸發展成情感認知評價理論,該理論的核心觀念是:情感直到主體對情境中的客體或事件給予評價后才產生。[14]3而評價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它們對行為者所追求的目標具有的利害作用的引導。在人類情感的種類上,學者們認為盡管在情感如何表達和解釋上具有文化差異,但有些情感具有普遍性,這些基本的情感是固化在人類神經自主系統之中的,具有提高適應的價值。關于情感的分類上,學者們區分了基本情感及其強度,以及情感進化出的次級情感,還從情感進化的角度解釋了情感如何使復雜的社會組織模式成為可能。[14]13,214-232本研究將以情感認知評價理論、特納的情感進化理論為依據,分析新冠疫情時期公眾應對危機時情感的產生和變化。
二、微博段子對危機事實的認知
(一)公眾的危機初級認知
疫情初期,由于對病毒、疫情防控等方面缺乏科學統一的認識,公眾對這一突發公共危機事實的認知是模糊的、不確定的,在眾多不確定因素的推動下,一些似是而非的表述在社交媒體上流傳。據中國互聯網聯合辟謠平臺的統計,2020年1 月下旬開始,公眾間開始流傳和新冠肺炎相關的各種謠言,在一個月之內相關謠言迅速攀升到幾百條,主要涉及疫情及防控、病毒預防和治療這兩方面。其中預防/救治方法的主題由于與公眾日常生活距離最近,往往能在短時間內迅速吸引觀眾的注意力,并引發公眾相應的非理性行為,例如搶購“雙黃連”的風潮。
(二)微博社交場景對公眾危機認知的影響
個體在形成對刺激情境和事物的認知和評價過程中,受到自身心理結構(如信仰、態度、人格特征等)和社會文化情境的影響。其中,社會文化情境對個體情感表現的影響主要途徑為:情感刺激的理解、表情、確定的社會關系和判斷以及高度禮儀化的行為。[15]
經過多年的發展,微博營造了一個相對匿名、開放的社交場景以及去中心化的用戶網絡結構,形成了娛樂化的認知框架,常常為各類話題注入娛樂化的成分。對于新冠肺炎疫情,亦是如此。疫情期間,微博上出現了以非中心的邊緣視角,圍繞新冠肺炎疾病、疫情發展、疫情導致的影響等主題進行現象描述、觀點分享的相關內容,反映了非疫情風暴中心的一般公眾對此次危機的認知和評價,此類表達以段子的形式出現,帶有鮮明的“娛樂化”微博基因。
(三)微博段子的危機次級認知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后,疫情區域相對集中,絕大多數的公眾處于危機的非核心區域,病毒的危險性、疫情的嚴峻性等對個體情感的刺激性較小,在對危機事實的“再認知-再評價”過程中,公眾再次篩選有關危機的信息,其中有關疾病、疫情事實的信息多是間接、二手的,而疫情的社會影響和隔離生活的信息卻可以隨手獲得,對個體情感的刺激也更加直接。本研究選取了2020 年2月29 日之前微博上出現和流傳較廣的65 個與新冠肺炎有關的段子,發現其中有40%段子的主題是隔離生活,23.08%和疫情影響有關,對疾病、疫情的關注度相對較少(見表1)。

表1 段子的內容主題
同時,段子娛樂化的認知框架賦予了隔離生活更多的趣味性,如:“大家應該每天中午起來,花一兩個小時化妝打扮,晚上再卸掉,又不會無聊,化妝技術突飛猛進。”“今年春節不串門,串門只串自家門,臥室門、廚房門、廁所門……”此外,娛樂化的表現手法也增加了平靜、友好等積極情感的成分。如:用喜劇化的場景、夸張的情節描述居家隔離的生活場景:“今天天氣很好,在房間呆久了,準備去客廳散散心。”又或用幽默的態度調侃隔離居家生活的現狀:“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一直在家,出現渾身乏力和頭暈,不要過分緊張。因為這是長時間躺床上刷手機造成的,建議去客廳散散心。再提醒一下,如果在家里出現喉嚨癢,持續咳嗽的情況也不要太緊張,說明你瓜子、山核桃等炒貨吃太多了。”
三、作為危機情感應對方式的微博段子
(一)應對理論
關于人類適應過程的研究始于19 世紀,Freud 的防御機制理論認為個體在應對消極的感覺,尤其是焦慮時會有意的扭曲事實。20 世紀30年代,Selye 認為應激是人或動物對于環境刺激的一種反應。認知革命的到來使人們意識到,刺激和反應之間會受到內在的心理過程的干預,并且強調有意識的、看得見的適應性的一個演變過程。[2]Lazarus 提出了應對過程理論,并于1966 年出版了《心理應激與應對發展過程》,強調情境特征對應對方式的影響,個體的應激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對環境的評價。后來Lazarus 和Folkman 關于應對的概念被學者們普遍認可:應對就是個體不斷改變認知和行為、管理內部和外部的緊張狀態來對付心理壓力。這一概念強調個體面對壓力時的認知和行為,認為應對是一個動力過程,同時也是一個有目的的反應,以此解決自身與壓力刺激的關系,可以說,應對是用來處理壓力的一組的認知和行為的策略,而有效的應對策略能幫助個體重新獲得平衡感,適應壓力條件下的情境。
(二)壓力應對策略
在具體的壓力應對策略上,Folkman 和Lazarus區分的兩種模式(問題聚焦模式和情感聚焦模式)都可用于分析各種壓力情境。Carver 等人認為應對策略應該包含更多不同的模式,例如更小用處策略等,[5]其編制的COPE 問卷認為個體的應對方式有14 種,分別屬于問題聚焦型(積極應對、計劃和自責)、社會支持型(尋找工具性社會支持、尋找情感性社會支持和發泄)、情感聚焦型(積極重構、忍受/ 接受、幽默、尋求宗教信仰)以及回避型(否認、轉移行為、逃避、物質濫用)四種策略。[6]
面對壓力,個體應對策略的選擇主要受確定性和可控性的影響,比如,個體面臨的情境處于低確定性和低可控性的狀態,其產生了恐懼的情緒,這將導致悲觀的判斷和風險厭惡的選擇,繼而會尋求情感支持、發泄;而所處的情境是高確定性和高可控性時,個體的憤怒情緒則會導致樂觀的風險評估和風險追求,傾向于采取行動、尋求指導。[10]由此可見,前者采取的是情感聚焦策略,后者采取的則是問題聚焦策略。
(三)微博段子的情感聚焦應對方式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尤其是疫情初期,正常的社會生活秩序被打亂,普通公眾普遍處于低確定性和低可控性的情境中,因此他們面對疫情的壓力更有可能采取情感聚焦應對策略。本研究對65 個段子的內容進行分析,根據段子的語義和目標指向,發現段子面對疫情時采取的應對方式有:發泄、接受、幽默和積極重構(見表2)。

表2 段子應對方式和內容主題
段子中發泄的對象主要是新冠肺炎疾病本身:如“2003 年,非典易感人群是青壯年,2020年,冠狀病毒易感人群是中老年。這xx 不就是同一批人嘛?多大仇啊!一路升級追殺了17 年!”除此之外還涉及疫情的擴散和疫情造成的各種負面影響。
對于不能改變的客觀事實,如疾病本身,段子采取主觀上接受的應對方式。如“祝大家雙肺紋理走形、分布正常,肺內未見實質性病灶,肺門不大,縱膈居中,心影不大,膈面光整肋膈角銳利。血尿常規正常,CRP 正常,核酸檢測陰性,鼠年吉祥,數一數二,心有所屬,屬你最棒!”同時接受的還有疫情造成的影響和隔離生活狀態。
面對無聊、煩悶、無所事事等的隔離生活,段子采取幽默的應對方式,如“提醒大家一下,如果在家出現胸悶,渾身乏力和酸痛,不要過分緊張。因為這可能是長時間躺床上玩手機造成的!!!(奸笑)請翻個身,再繼續。”
同時,提出以積極的角度看待隔離生活,對隔離生活進行積極重構,想象讓隔離生活變得有趣的方式,挖掘隔離生活的好處:如“愛打麻將的人終于可以坐在一起連打14 天!”。還有的段子挖掘疫情擴散、社會停擺的好處,例如平時不好拒絕的活動(過年拜訪親友)、難以禁止的行為(學生補課)。有的段子中希望重構當前的社交媒體信息傳播分布,消解被疫情信息包圍的恐懼氛圍,還有的則在疫情擴散中發現區域差別,尋找積極信號。
四、微博段子呈現的危機情感傾向
(一)情感的產生
人類的情感是具有普遍性的,這些具有普遍性的情感被稱為基本情感(primary emotions),盡管學者們對存在有幾種基本情感上存在分歧,但普遍認同高興、恐懼、憤怒和悲傷是普遍的,同時這些基本情感具有高、中、低三種強度狀態,形成滿意-高興,厭惡-恐懼,苦惱-憤怒,失望-悲傷的情感變化。[14]13
關于人類情感的產生,情感認知評價理論(cognitive evaluation theory of emotion)認為,只要事物被評價為與個人生活的重要方面有聯系,個體就會有情感體驗。人類的情感產生于對刺激情境或對事物的認知和評價。該理論于20 世紀50年代由美國心理學家Arnold 提出,其認為人們總是直接地、自動地并且幾乎是不由自主地評價著遇到的任何事物,情感就是一種朝向評價為好(喜歡)的東西或離開評價為壞(不喜歡)的東西的感受傾向。其中,記憶是評價的基礎。任何新的事物都是按照過去的體驗來進行評價的。想象是評價的重要環節。在開始行動之前,當前的情境和有關的感情記憶使我們推測未來。整個評價的復雜過程幾乎是在瞬間發生的,情感產生的過程是“刺激情境-評價-情感”。
Lazarus 進一步把上述的評價擴展為評價、再評價過程。這一過程包括篩選信息、評價、應對沖動、交替活動、身體反應的反饋、對活動后果的知覺等成分,他建議對個人所處情境進行評價,也包括對可能采取什么行動進行評價,也就說情感是人和環境相互作用的產物,在情感活動中,人不僅接受環境中的刺激事件對自己的影響,同時要調節自己對于刺激的反應。[16]
(二)公眾的危機初級情感
公共危機時期,公眾持有的情感類型、情感強度的狀態與其對危機事實的認知和評價密切相關,危機事實的發展和變化以及公眾對危機事實的認知和評價的變化,都將影響著公眾的情感走向。作為一起公共衛生危機事件,新冠疫情對社會秩序的穩定、社會成員的生命安全構成了極大威脅,全面影響了個體的生活和工作。疫情初期,社會對疫情的發展和防控、疾病的治療仍未形成統一的科學措施,公眾對于危機事實的認知和評價普遍處于“無知、無能”的狀態,加之絕大多數公眾對2003 年SARS 危機時期仍保有恐慌、悲愴等負面的情感記憶,因此產生了公眾產生了較高強度的消極情感,具體表現為對病毒的恐懼,面對病毒擴散奪取生命的悲傷,對疫情防控負面事件的憤怒等。
由于公共衛生危機時期往往伴隨著大量的不確定性,例如新冠肺炎病毒的傳染路徑不明確、無特效藥、缺疫苗等,這些特征給普通公眾帶來了極大的無助感,處于危機中的個體很難進行冷靜的思考和科學的判斷,更易被情感所支配,極容易受到外來情感的影響,因此,危機來臨之時某種情感,尤其是消極情感易以暗示、傳染的形式在人群中迅速擴散。另一方面,由于危機發生時常出現局勢不明朗、信息傳播不夠及時公開等現象,導致個體缺乏充足的、客觀的信息作為情感的依據,從眾成為決策成本最低的一種選擇,消極情感一旦在人群中產生,就能在短時間內迅速成為群體的共同情感。同時,多渠道、多手段、多形式的融合傳播技術引領我們進入沉浸傳播時代,傳播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無所不能,[17]這種沉浸式傳播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也為普通公眾提供了眾多“身臨其境”的場景,相應情感的擴散也搭上了快車道,社交媒體上的隨手轉發不僅傳播了相關信息,相關情感也在一次次的轉發過程中不斷累積和擴散,每一次的微博熱搜、微信朋友圈刷屏都使個體處于某種情感的包圍之中,情感的彌漫性影響越來越大。此外,情感牌是社交平臺上眾多自媒體的獲取流量的重要手段,經過自媒體的傳播,各種消極情感的強度不斷升級,對公眾消極情感的極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三)微博段子的積極情感傾向
特納在基本情感的分類的基礎上區分了低、中、高三種強度水平,某種情感狀態對應不同強度的情感類型,由此把人類的基本情感分為75 種具體情感形式。其中“高興”有17 種,“恐懼”有14種,“憤怒”有27 種,“悲傷”有17 種。例如“平靜”“輕快”“喜悅”分別是低、中、高強度水平的基本情感之“高興”,而低強度的“高興”還有“滿意”“滿懷希望”和“感激”。依據特納對基本情感的上述分類,本研究在語義分析的基礎上對每條段子所反映的情感類型進行定位,結果顯示53.85%的段子反映的是積極情感,消極情感中約70%是低強度的(見表3)。

表3 段子的情感類型及強度
五、經由段子傳播實現的危機情感轉換
(一)生產段子削弱了消極情感
在人類的基本情感中,恐懼、憤怒、悲傷這三種都是消極情感,由于基本情感間的聯合可以產生不同的次級情感,消極情感可以通過與積極性情感的融合產生新的次級情感,從而削減消極因素。例如:厭惡-恐懼+滿意-高興=期望,失望-悲傷+滿意-高興=接受,強硬-憤怒+滿意-高興=平息。[14]16如上所述,段子反映了個體對危機事實的次級認知和評價,而個體在次級評價(secondary appraisal)這一階段會通過回避、疏遠和否認應激源,或是轉移對應激源的注意力、重新理解應激源等具體方式,達到擺脫由應激源引發的消極情感這一應對的根本目的[18-19]。作為公眾應對新冠肺炎危機的情感聚焦策略,段子通過對隔離生活的聚焦,減少了對疾病、疫情的關注度,從而改變了個體情感的應激源,為積極情感產生提供了認知基礎,并通過接受、幽默和積極重構的應對策略,表現出平靜、滿懷希望等低強度的高興情感,以及輕快、友好、享受等中強度的高興情感(見表4)。具體表現為:輕快地描述隔離生活,友好地表達對隔離生活的建議,并建議要享受隔離生活帶來的好處,同時平靜地描繪疾病,對控制疫情滿懷希望。同時,提出以積極的角度看待隔離生活,對隔離生活進行積極重構,想象讓隔離生活變得有趣的方式,挖掘隔離生活的好處;從正面角度調侃疫情的擴散、疫情導致社會停擺,有的段子中希望重構當前的社交媒體信息傳播分布,消解被疫情信息包圍的恐懼氛圍,還有的則在疫情擴散中發現區域差別,尋找積極信號。
表4 還可看出,段子表達的消極情感中悲傷較少,不涉及疾病和疫情的內容主題;三種消極情感中恐懼占比最多,四類主題內容均有涉及,但和疫情相關數量明顯少于其他三種;段子中的憤怒情感主要和疾病有關,對隔離生活表示憤怒的很少。從情感的強度水平上看,段子中的消極情感強度處于中、低程度,例如對疫情影響的沮喪、對疾病的不安、感受到疫情影響的利害等。

表4 段子的內容主題和情感類型、強度
(二)關注段子構建積極情感聯系網絡
已有的研究表明,對于形成社會紐帶和團結來說,消極情感是一種障礙,因此自然選擇需要促成大腦能夠產生新的情感類型,以削弱消極情感的力量,或把消極情感轉換為能夠促進社會控制的復雜情感。[14]220人類的行為也受到體驗盡可能多的積極情感,以及盡可能少的消極情感的動機引導。在日常生活中,人們會采用多種策略來確保積極情感的發生和持續,包括建立多樣性的情感聯系,建構積極情感聯系網絡;形成強度不同的情感聯系,為特定情境和關系排序等。[14]220新冠肺炎疫情初期,隔離的居家生活打亂了個體原有的社交活動及情感聯系網絡,線下的情感交往被抑制,伴隨著線上交往活躍度的提高,網絡空間也成為個體獲取情感能量的主要來源地。而微博廣場式的社交場景、偶遇的匿名交往對象、暫時的交往關系對個體的時間和能量成本要求較低,這都激勵著個體積極構建以弱關系為基礎的積極情感聯系網絡。以情感分享為主要功能的新冠肺炎段子,為網絡上分散的個體提供了相互連結的橋梁。個體也在關注段子的過程中,獲得了與他人共享注意力的體驗,產生了和其他微博用戶一起面對疫情危機的感受,由此建構一個以微博用戶為主要成員的積極情感聯系網絡。
(三)評論、轉發段子提升微博互動關系的排序
除了建構積極情感聯系網絡,為了獲得更多的積極情感體驗,個體還會調整關系網絡的位置,把產生積極情感較多的關系放置于層級較高的位置上,把產生積極情感較少的關系放置于較低的位置上,通過這種方式,個體知曉特定情境或關系能產生多少積極情感,進而調節行為使積極情感最大化[14]226-227。因此,當個體在關注段子過程中體驗到更多的積極情感,可能積極留言評論表達意見觀點,或是轉發分享擴大段子的傳播范圍,自身的卷入程度也進一步加深。隨著與段子相關的行為逐步展開,個體對微博積極情感聯系網絡的卷入程度逐漸提升,該情感聯系網絡也被個體置于更高的層級位置,“上微博”成為個體進行線上社交活動的優先行為,從而能以持續的積極情感應對新冠疫情這一危機。
結論
基于對公共危機時期相關微博段子的傳播和公眾危機情感的變化分析,可構建出公眾危機情感調適模型(如下圖)。

圖1 基于微博段子的公眾危機情感調適過程
早期和疫情相關的信息多為負面,一時間消極情感在公眾間蔓延,而微博段子的出現,喚醒了網民的娛樂情感,宣泄了消極情緒,在閱讀段子過程中與段子生產者建立了傾聽和傾訴的情感聯結關系,由此打開了微博場域的互動儀式鏈,個體也加入了正向情感能量的生產和傳播過程。隨著段子的傳播,其所包含的話題成為微博用戶共同的關注點,強化了用戶相似的心境,發表評論、參與轉發等活動演變成一種互動儀式,個體之間實現了節奏型同步,共享了心境,強化了微博用戶這一身份認同,進一步激發形成了情感共同體。同時這一系列的參與式傳播行為作為微博用戶群體的共同行為,推動著他們達到了集體興奮和情感愉悅。可以說,微博段子的出現和傳播,是公眾面對危機時積極主動進行情感調適的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