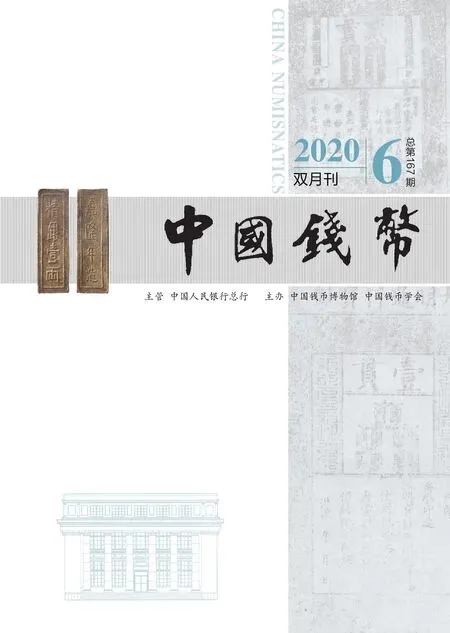魯西銀行民國31 年魯西南一元加蓋“照常通用”券之考辨
李天聰(連云港農業發展銀行) 李 銀(山東交通技師學院)
魯西銀行民國31 年(1942)魯西南一元券(以下簡稱“魯西南一元券”)系魯西銀行第四印刷所(以下簡稱“四所”)1943 年開始印制的。該券深綠色,正面是割稻、鋤地圖景,兩邊邊框各印“魯西南”三字;背面為亭閣圖景(圖1)。目前僅見A、B 兩種冠字。筆者至今先后見過該票近二十張。其中有兩張正面加蓋了“照常通用”戳(圖2、圖3)。通過觀察實物,“照常通用”戳是在紙幣印好后手工加蓋的。由于兩張紙幣加蓋的戳不完全一樣,可以肯定當時制作了不止一枚。

圖1 楊錦昌藏品

圖2 李慶鎖藏品

圖3 鄭延林藏品
四所是在冀魯豫行署財政處長華夫、魯西銀行行長張廉方的指導下,魯西南地委、專署的大力支持下,由專署財政科于1942年秋季開始籌建,對外稱冀魯豫行署第七專署轉運站。籌辦人員先后有王子平、張海涵。首任所長楊明義(來自地委),管理員張光遠(來自地委),指導員王凌霄(魯西銀行委派)。魯西南專署(七專署)時轄曹縣、菏澤、考城、定陶、曹東等縣[1]。
魯西南一元券存世量就不多,加蓋“照常通用”者更屬鳳毛麟角。很少有人論及加蓋的目的。筆者僅見一位研究魯西銀行的專家做過相關探討,認為加蓋“照常通用”四個字,主要原因是1943年9月敵人“掃蕩”時,不允許老百姓使用共產黨的票子。掃蕩過后,部分群眾仍然心有余悸。為打消群眾的疑慮,魯西銀行把部分1 元的票子收回,加蓋“照常通用”戳記并發出去,目的是讓群眾放心使用。
筆者認為該說法缺乏有力的支撐。首先,日偽不僅在掃蕩魯西南時禁用過抗幣,掃蕩其它根據地時亦禁用過抗幣。未聞其它根據地有此做法的。一般情況下,掃蕩過后抗幣自然就恢復了流通,根本沒有必要在票面上加印幾個宣傳字;其次,在票面上加蓋“照常通用”向群眾宣傳魯西南一元券照常流通,非但不能達到宣傳的目的,反倒會引起誤解:人們會認為有加蓋的能流通,沒有加蓋的就不能流通。
在票面上加蓋“照常通用”戳的目的何在?筆者注意到四所籌建人之一的張海涵在《魯西銀行第四印刷所的簡單情況》中說的一段話:“在發行一元票的時候,曾發現假票,重改版面后繼續發行。”[2]查看《魯西銀行歷年發行券別金額統計表》,1943 年,魯西銀行僅發行過一種一元券,發行量是1066964 元[3],之后未再發行一元券。因此,有理由認為張海涵所說的“重改版面后繼續發行”,就是在魯西南一元券正面加蓋“照常通用”戳后繼續發行。也就是說,加蓋“照常通用”戳的目的是為了反假。
由于飽受自然災害及戰爭的摧殘,以及1942 年冬西北局高干會議后,魯西銀行加快了發行步伐,十元、五十元券相繼問世,魯西幣連續貶值。二百元及五百元臨時流通券的發行,更加速了魯西幣貶值的步伐。一元券早已成為找零的輔幣了。估計在當時,加蓋和不加蓋戳的魯西南一元券可能都照常流通,人們基本上不會太在意它的真假。目前加蓋“照常通用”戳的魯西南一元券的存世量遠遠少于未加蓋的現狀,也支持這一論點。
當時根據地發現假票,一般情況下是銀行或相關部門先研究真假票特點,然后對外宣傳識別真假辦法,掀起群眾性的反假運動,基本上不會通過在紙幣上加蓋戳記達到識別真假的目的。假幣情況十分嚴重的,甚或是鈔版被敵人繳獲的情況下,會發行新版紙幣替換舊幣。魯西南根據地發現一元假票后,通過在票面加蓋來反假,說明假票情況比較嚴重,已經達到真假難辨的程度。
雖然四所初期印制的魯西幣最高面額就是一元券,但是,魯西南一元券并非魯西南根據地的主流貨幣,而應是找零用的輔幣。通常敵人制假的重點是主流貨幣。魯西南一元券即非主幣,怎么會被敵人仿制得真假難辨?張海涵在《魯西銀行第四印刷所的簡單情況》中的一段話有助于破解此問題。文中說到:“一九四三年敵人掃蕩時,所部住在曹縣韓集區馬莊,地下室設在大楊湖和附近兩個村莊,已擁有石印機三部、鉛印機一部.有職工干部三十多人,印刷的是一元綠色票面。……這是敵人所謂‘鐵壁合圍帶蓋’,規模最大,摧毀最慘的一次掃蕩。我大楊湖地下印刷廠遭到破壞,票版被掠走,但敵人掃蕩過后,全所人員很快又集合起來,恢復了生產[4]”。根據該段文字,足以認定敵人在掃蕩中繳獲的票版就是魯西南一元券的票版。
1943 年敵人對魯西南根據地的掃蕩大小有數十次,但是規模最大最慘烈的一次,則發生在秋季。據《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大事記》載:9 月21 日至10 月12 日,日軍為摧毀冀魯豫抗日根據地……對冀魯豫根據地進行大“掃蕩”。敵人由南至北,先合圍湖西地區,繼“掃蕩”魯西南、運東、沙區,后全力合圍蹼范觀中心區,回兵時再“掃蕩”沙區、運東地區。可以認為魯西南一元票版被敵人繳獲的時間大致是1943 年9 至10 月。
當時根據地印鈔的油墨、鈔紙等器材大多是從敵占區購買的,有了鈔版,敵人自然不會放過這個難得的用假幣入侵根據地的機會。如果此說成立,敵人用繳獲的鈔版印制假魯西南一元券的時間當在9 月21 日以后,根據地在發行的魯西南一元券上加蓋“照常通用”戳的時間當在10 月12 日以后。
為了驗證上述論點,筆者從四位藏家和三家拍賣公司網站上采集了他們所有的魯西南一元券樣本圖片(共13 枚)進行分析。將這13 枚一元券按流水編碼順序排列,分別是:A0072667、A0172117、A02052639、A0237950、A0260562、A0318210、A0574325、A0581288、A0581300、A0602885、A0859694(加蓋“照常通用”)、B0184343(加蓋“照常通用”)、B0212303。由于B0212303 樣本圖片模糊,冠字A 中的最大流水號加上其流水號等于1071997,超過了魯西南一元券的總發行量,慎重起見,將其從樣本中剔除。
一般來說,不同條件下,鈔票的冠字(當時又稱字頭)可能代表不同的意義。有的代表鈔票的投放地區;有的代表鈔票的生產單位;有的是區分不同的面值(如中央銀行青島分行銀元券);有的是按序數排列,每印一定數量的鈔票后更換冠字,等等。由于魯西南專署就領導幾個縣,下面僅有一個印刷所,因此魯西南一元券的冠字當屬于第四種情況。
上述冠字A 的樣本中,未加蓋戳的最大號碼是A0602885,加蓋戳的僅有一個A0859694,且是冠字A 樣本中最大的號碼。按理說,通過在某一種票子上加蓋戳記進行反假,無論新發行的還是回籠的舊幣,只要再投放,均應當加蓋,以示為真幣。本次采集的冠字A 的樣本點中,僅大號碼樣本有加蓋戳,其余均無。說明當時一元輔幣券在外流通的時間比較長,回籠的多為破舊幣,已無再投放的必要,故未加蓋。由此可以假設A0859694 樣本是在發行前加蓋“照常通用”的,而非回籠后加蓋。如果此假設成立,則假票應當出現在A0602885 券發行之后,A0859694 券發行之前。
根據張海涵《魯西銀行第四印刷所的簡單情況》介紹:四所1943 年初正式開始生產成品,至大“掃蕩”前仍在印一元券,掃蕩過后很快又恢復了生產,開始只有三部石印機工作,其中一部是破舊的石印機,隨后又增加了二部石印機和一部鉛印機。假設四所年初就開始印制魯西南一元券,并延續到年底,扣除日偽掃蕩的那21 天,四所11.3 個月共印制了1066964 元魯西南一元券,平均每月印制約9.4 萬元。以此簡單的計算,印到A0602885券時。大約歷時6 個半月。考慮到工人由不熟練到熟練的進程以及后來印鈔能力提高了近一倍,可以認為A0602885 大約印制于7 至8 月份。也就是說至7、8 月份,可能尚未出現魯西南一元的加蓋票。印制到A0859694 券,大約歷時9 個多月。同樣情況,可以認為該券印制于大“掃蕩”后。B0184343 樣本印制于A0859694 樣本之后,自然也印制于大“掃蕩”之后。
綜上所述,沒有加蓋戳記的魯西南一元均印制于大“掃蕩”前,加蓋戳記的魯西南一元均印制于大“掃蕩”后。“照常通用”的戳加蓋與與秋季日偽大“掃蕩”密切相關。
鑒于魯西南根據地在日偽大“掃蕩”之后發現了十分逼真的“假票”,且日偽在大“掃蕩”中繳獲了四所一元券鈔版,有理由認為日偽用大“掃蕩”中繳獲的四所鈔版印制了魯西南一元假票入侵魯西南根據地,導致了魯西南根據地為了反假在魯西南一元券上加蓋“照常通用”戳。
注釋:
[1]《解放日報》1942 年3 月23 日。
[2][3][4]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中國人民銀行山東省分行金融研究所編:《冀魯豫邊區金融史料選編》下冊,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89 年12 月,第658 頁,第110 頁,第659 至660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