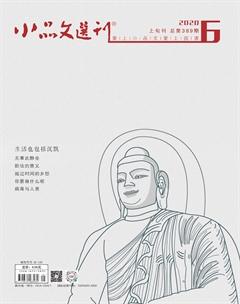一件暖心的小事
陸天明
那天深夜,大雪紛飛。改日轉晴,天空居然藍得那么透徹。上午接到快遞小哥通知,讓到小區大門外取件。北京城疫情漸緊后,所有小區管理加急加嚴。凡是有幾個出入口的都只留下一個口子供住戶進出。其余的全封閉。外賣、快遞人員更是一律不許進小區。物件只能存放在小區大門外,由業主去自取。業主本人也只能憑蓋了紅章子的出入證才得以進出。
已經記不得那天到底是誰寄了什么來———那一陣,小區里家家戶戶幾乎都靠快遞、外賣過日子。大門外的人行道上,特設的木架上整日地堆積著大大小小的郵包、快件和食品盒。它們真的像波浪一樣,一波剛靜靜退去,一波又會“喧囂”涌上。
北京的雪后,照例風大,降溫厲害。從我家去小區大門口,來回少說也有兩三里地。放下電話,我急忙裹上件大衣,扣上那頂早已舊得沒了樣子的鴨舌帽,踩著嘎吱嘎吱作響的濕雪,沒走出多遠,就聽見有人喝斥我:“大叔,您怎么不戴口罩?!”我一愣。自問,我沒戴口罩?不至于吧?再摸臉頰,果然冰涼。真裸露著哩!正在責備自己一時間居然慌亂如此!那人卻已經走近了我。我一看,是小區物業的一位工作人員,三四十歲。我剛想道歉,對方已經下車———自行車,手伸向制服大衣里邊的一個口袋掏出一把雜七雜八的東西,又從這些“雜七雜八”里揀出一片物件遞給我。我再看,是個沒拆封的口罩,新口罩。“快戴上。眼下像您這個年紀的真大意不得。”說著,沒等我謝過,他已跨上車走了。
口罩上還帶著這位粗壯漢子的體溫。外加一點煙味兒。
一片口罩真真正正不值幾個錢。但在當時的北京,誰都知道口罩的“金貴”和“難得”。幾乎所有藥店和超市,無一不貼著這么個小小的告示:“口罩和消毒用品暫時缺貨。”誰要不戴口罩,誰都躲你遠遠的。這一片口罩應該是物業領導發給他本人值班用的。值一天班,才會發他一片。這片帶著他煙味兒的口罩絕對是他省下來備用的,居然給了我。我也不能說,這么一片東西在整個防疫期間對于我起了多么關鍵的作用。我相信,他也沒覺得自己做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我還是久久忘不了這個粗壯漢子的這一遞,總覺得這片口罩上不只帶著他的體溫,帶著那點煙味兒,真真正正地還帶著這漢子的心跳。我跟他無親無故。物業的許多工作人員可能還不是北京籍人士。他們北漂,漂一兩年的,也有漂了十來年的,每月收入也就在兩三千元或三四千元之間……以后的日子,政府對小區的管理要求更加嚴格,他們必須二十四小時在小區大門口值班。北京嚴冬的深夜,在零下多少度的大風天里,即便裹著再厚的棉大衣,即便后來給他們配備了值班帳篷,我想也絕對不是一般人能忍受的。但他們就是這樣一夜一夜地堅守著———用他們那種帶著點煙味兒的體溫抗御著,為小區里的男女老少們把那無孔不入的病毒阻截在小區大門外。
于是,有業主自發在小區的微信群倡議為這些粗壯漢子們眾籌,給一點補貼,稍稍改善一下他們的生活。以往小區這個微信群,不管誰在哪方面提出些什么見地和倡議,總有異議。唯有這一回的這個眾籌倡議沒遭半點異議。一兩天里就籌得數萬元。有不少業主,“捐”了一回又再“捐”。他們是交了物業費的,不“捐”不籌,似乎也沒人會說什么。籌了那么一點點錢,無非也就是給這些粗壯漢子們深夜的加班餐里添幾片肉一兩個雞蛋,天亮時能喝上一杯熱牛奶而已。這些粗壯漢子們吃不吃得上幾片肉,喝不喝得上一杯熱牛奶,跟這些已然交了物業費的業主們有一毛錢關系嗎?他們這點眾籌在中國這場空前的命運決戰中真能起多大作用?當然不是。
我遇到的這些人和事,在今天的中國絕對得算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事。它們絕對無法和那些英勇的逆行者、數以萬計直接面對個人生死存亡日夜奮戰在醫治一線的白衣天使和科技工作者們相比,無法和日夜用淚水和微笑激勵這些白衣天使的父母丈夫妻子們巨大的付出相比。但有一點是可以確信的,這些不起眼的小事,點點滴滴地發生在中國每個角落、每個中國人身上。這十四億民眾各盡其力、各守其責、各堵其漏,一起來關注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命運,都在把自己這點體溫投注到這個無比嚴酷的寒冬里。我們終于融解了寒冬,迎來了肯定屬于我們的這個春天。盡管寒冬以后還會有暴風驟雨,還會有驚濤駭浪,但無論如何,“滿園深淺色”之際,“不信東風喚不回”。
選自《文匯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