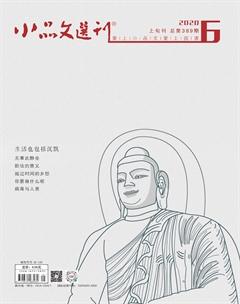金圣嘆評點“六才子書”
沈鴻鑫
金圣嘆是明末清初著名文學批評家。他出生于明萬歷三十六年(1608年),江蘇人。他本姓張,名采,字若采;后改姓金,名喟,圣嘆是他的別號和評書時用的筆名。金圣嘆幼年生活比較優裕,“拈書弄筆三時懶,撲蝶尋蟲百事宜”。然而父母去世早,家道中落。他10歲入塾,少有才名,“為人倜儻高奇,俯視一切,好飲酒,善衡文評書,議論發前人所未發”。清兵南下時,曾遭喪亂困頓之苦,明亡,絕意仕進,直到晚年境況無多改善。他喜歡批書,著作有評點“六才子書”和《沉吟樓詩選》等。
金圣嘆不滿于清廷官吏的暴政和黑暗的現實。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順治帝駕崩的哀詔傳到蘇州,巡撫以下的官吏設幕哭靈。金圣嘆等幾個秀才卻組織多人寫了“揭帖”,到哭靈場所控告縣官貪污倉糧、打死鄉民的行徑,揭露貪污縣官乃受巡撫朱國治之指使。此事轟動全城,群情激憤。朱國治先發制人,立即逮捕了5名秀才。次日,金圣嘆又組織群眾前去哭廟,以示抗議。一時鳴鐘擊鼓,震動四方。清廷嚴加鎮壓,以抗糧哭廟案坐“謀反”罪,判金圣嘆等人斬刑。
臨刑前,金圣嘆泰然自若,他向監斬官索酒暢飲,飲罷大笑道:“割頭,痛事也;飲酒,快事也;割頭而先飲酒,痛快!痛快!”漫天飄起雪花,金圣嘆仰天高呼:“天悲悼我地亦憂,萬里河山帶白頭。明日太陽來吊唁,千家萬戶淚長流。”這一年,金圣嘆53歲。
金圣嘆的文學成就主要在文藝批評方面。他從小就喜歡批書,他說:“吾既喜讀《水滸》,12歲便得貫華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鈔,謬自評釋,歷四五六七八月,而其事方竣,即今此本是已。”明末清初,隨著經濟的發展,小說、戲劇等新興文學樣式空前繁榮,在文藝批評界,李贄、葉晝等人開小說評點、戲曲評點風氣之先,其后風靡文壇。金圣嘆則是集小說與戲曲評點之大成,而成為最具理論價值的一位文藝批評家。
金圣嘆受李贄影響頗深,畢生反抗傳統,“六才子書”的觀念也是受李贄的啟發。他認為天下有六大奇書,它們寫得雅馴、透脫、精妙。他一律用才子書加以命名,第一為《離騷》,第二為《莊子》,第三為《史記》,第四為《杜詩》,第五為《水滸》,第六為《西廂記》,并對各書評批,合稱《六才子書》。完成的有第五才子書《水滸》及第六才子書《西廂記》的評點,他對這兩部書頗多刪改之處,著稱于世,影響尤大。所評杜詩,見《圣嘆集》,還有天下才子必讀書,節評《左傳》《國語》《國策》《史記》等,共百余篇。他寫的絕命詞中有“且喜唐詩略分解,莊騷馬杜待何如”之語句,可見對未批完的四部書還念念不忘。
歷代正統文學家一般都輕視民間文學,文學批評中也沒有小說、戲曲的地位,而金圣嘆將向來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說《水滸》與戲曲《西廂記》提高到與《離騷》《史記》相提并論的崇高地位。他明確提出《水滸》可與《論語》媲美,《西廂記》可作為童蒙課本而取代當時固定的“四書”。金圣嘆這些主張是對傳統文學觀的大膽挑戰,并被視為“異端”。
在藝術分析方面,金圣嘆有其獨到的地方,他的藝術分析細致、嚴密、精辟。李漁曾說:“圣嘆之評《西廂》,其長在密。”他評《水滸》亦然,如評卷二十七“打虎”一節,原作對武松手中的哨棒前后描寫18次之多,金圣嘆一次次詳加批注,分析了反復描寫哨棒的藝術作用,十分精到。他不僅注意作品的各個細節,而且把細部與整體聯系起來考察。比如,他把《水滸》當成一本大書,析為林沖傳、武松傳、宋江傳及其他諸傳,有的互相穿插,大傳中有小傳,每一傳有一主角,這種崇尚整體美的結構論是不同凡響的。
前人評論作品較多注意文辭音律,而金圣嘆把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問題提到突出的位置,并加以深入研究。金圣嘆主張作家要刻畫人物的獨特性格,他說:《水滸傳》“敘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他又細致地分析道:《水滸傳》只是寫人粗魯處,便有許多寫法,如魯達粗魯是少年任氣,李逵粗魯是蠻,武松粗魯是豪爽不受羈絆,阮小七粗魯是悲憤無說處,焦挺粗魯是氣質不好。并論述了人物性格與景物、環境描寫的關系。他評《西廂記》“賴簡”時,指出尊貴、矜持的鶯鶯在一個靜夜里,面對張生突然來臨,張生又過分直率,近乎粗魯,因此必不能耐,賴簡是鶯鶯性格在特定環境中的必然表現。
點評一般比較瑣碎,然而金圣嘆卻注意通過點評從理論上總結藝術創作的規律和技法。他說:“《史記》是以文運事,《水滸》是因文生事。”這就區分了史書與小說的不同特點。他還通過作品分析總結了一套藝術表現手法,如《水滸》中的倒插法、夾敘法、草蛇灰線法、綿針泥刺法、弄引法、獺尾法等;《西廂記》中的大落墨法、烘云托月法、獅子滾球法、月度回廊法等。如此細致、系統地總結藝術技法在批評史上并不多見。當然,金圣嘆把評論家的觀點強加于原作者頭上那種妄加刪改以及形式主義傾向都是不足取的。魯迅在《談金圣嘆》中曾指出:“原作的誠實之處,往往化為笑談,行文布局,也都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關于金圣嘆的評價,歷代有所爭議,其著作中確實也有糟粕的成分,然而總的來看,他不失為生活在封建時代的一位正直的文人,在文學評論方面更是一位很有建樹的批評家。
選自《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