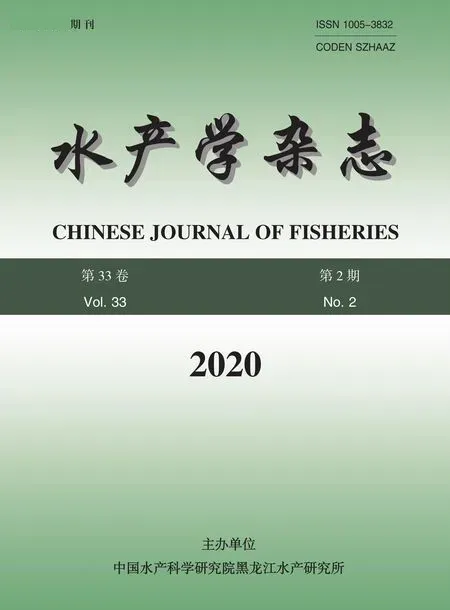饑餓和恢復投喂不同時間對西伯利亞鱘消化酶活性的影響
王常安,劉紅柏,陸紹霞,姜海波,劉洋,韓世成
(1.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黑龍江水產研究所,黑龍江 哈爾濱 150070;2.貴州大學動物科學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饑餓是動物生長的不利因素之一,但在動物中普遍存在繼饑餓或營養不足一段時間后恢復喂食,將出現超過正常生長速度的補償生長。為了適應饑餓等環境的變化,魚體消化酶活性會發生適應性變化[1]。這種變化在花鱸Lateolabrax maculatus[2]、虎鯊Herterodontus japonicus[3]、施氏鱘Acipenser schrenckii[4]、黑鯛Sparus macrocephalus[5]、許氏平鲉Sebastes schlegelii[6]、翹嘴鲌Culter alburnus[7]和鯉Cyprinus carpio[8]等已有報道。但是,魚類饑餓和恢復投喂期間,消化系統的代謝調節過程的研究有限[9]。與肉食性魚類相比,雜食性魚類對饑餓的代謝調節策略資料仍然匱乏[9-11]。饑餓和恢復投喂對西伯利亞鱘Acipenser baerii 消化酶活性的影響至今未見報道。本文研究了饑餓期間及恢復投喂后西伯利亞鱘消化系統的蛋白酶、脂肪酶、淀粉酶活性的變化,旨在闡明饑餓和恢復投喂對西伯利亞鱘消化酶活性的影響,以期為鱘補償生長效應提供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材料
試驗飼料用魚粉和豆粕為蛋白源,魚油和磷脂為脂肪源。飼料的配方及營養水平見表1。原料均過80 目篩后用鼓型混合機混合,制粒(直徑為2.0m),然后置于-20℃冰箱中保存待用。
試驗用西伯利亞鱘初始體質量為(64.43±1.06)g。選取體質健康、規格一致的個體放入室內流水系統。用基礎飼料馴養14 d 后開始養殖試驗。
1.2 方法
本試驗采用各組饑餓時間不同而恢復投喂時間相同的試驗設計。試驗魚飼養在室內500L 流水水族箱中。對照組(S0)持續投喂35d,試驗組S5、S10、S15 分別饑餓5d、10d、15d,然后均恢復投喂20d。每組設3 個重復,每重復50 尾。水源為河水,水溫18.2~21.3℃,溶氧>6.0mg/L。日飽食投喂2 次(9:00 和16:00)。養殖試驗結束后,魚體饑餓24h,用苯氧乙醇(0.5mL/L)麻醉,稱重,采集樣品?
試驗開始、饑餓結束以及恢復投喂的5d、10d、15d、20d 時,均測量各組魚的體質量。在試驗開始、饑餓結束及恢復投喂的第5d、10d、15d、20d 時,每組隨機取3 尾魚,在冰盤上,取其腸和肝。剔除內含物和脂肪后,用冰浴生理鹽水(0.86%)沖洗干凈,然后用濾紙吸干,稱重,裝在自封袋中,放入超低溫冰箱(-80℃)中保存待測。肝和中腸的蛋白酶、淀粉酶和脂肪酶活性分別以福林-酚法、淀粉-碘比色法和聚乙烯醇橄欖油乳化液水解法測定;組織蛋白含量采用考馬斯亮藍法測定[12]。
1.3 統計分析
數據以平均值±標準差(Mean±SD)表示。用軟件SPSS for Windows 23.0 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和Duncan’s 多重比較,顯著性水平P=0.05。
2 結果與分析
2.1 不同饑餓和恢復投喂時間對西伯利亞鱘體質量的影響
由表2 可知,饑餓結束時,S5 組、S10 組、S15 組西伯利亞鱘的體質量均顯著低于對照組水平(P<0.05)。恢復投喂20d 后,S5 組、S10 組和S15 組體質量均快速增長。除S5 組與對照組水平差異不顯著(P>0.05)外,S10 組、S15 組的體質量仍然顯著低于對照組(P<0.05)。

表1 基礎飼料配方及營養水平(風干基礎)Tab.1 Ingredients and approximate composition of the test diets(air-dry basis)
2.2 不同饑餓和恢復投喂時間對西伯利亞鱘腸道和肝蛋白酶活性的影響
由表3 可知,饑餓結束時,S15 組西伯利亞鱘腸道和肝蛋白酶活性顯著低于對照組(P<0.05),而S5組和S10 組與對照組差異不顯著(P>0.05)。恢復投喂后,各組魚腸道和肝蛋白酶呈上升趨勢。恢復投喂10d 后,各組腸道蛋白酶活性與對照組差異不顯著(P>0.05)。恢復投喂5d 后,S5 組和S10 組肝蛋白酶活性與對照組差異不顯著(P>0.05),恢復投喂20d 后,S15 組肝蛋白酶活性仍顯著低于對照組(P<0.05)。
2.3 不同饑餓和恢復投喂時間對西伯利亞鱘腸道和肝脂肪酶活性的影響
饑餓結束時,各組西伯利亞鱘腸道和肝脂肪酶活性均顯著低于對照組(P<0.05),恢復投喂過程中,S5 組、S10 組、S15 組腸道和肝脂肪酶活性均平穩上升。然而,恢復投喂結束后,S10 組、S15 組腸道和肝脂肪酶活性仍顯著低于對照組(P<0.05)(表4)。
表2 試驗前后各組西伯利亞鱘體質量的變化Tab.2 The changes in body weight(g)of Siberian sturgeon Acipenser baerii in various groups during the experiment(n=3;±s±SD)

表2 試驗前后各組西伯利亞鱘體質量的變化Tab.2 The changes in body weight(g)of Siberian sturgeon Acipenser baerii in various groups during the experiment(n=3;±s±SD)
注:同列中標有*表示組間差異顯著(P <0.05)
表3 饑餓和恢復投喂不同時間對各組西伯利亞鱘蛋白酶活性的影響(IU/prot)Tab.3 Effects of starvation and refeeding on protease activities (IU/prot)in Siberian sturgeon Acipenser baerii in various groups(n=3;±s±SD)

表3 饑餓和恢復投喂不同時間對各組西伯利亞鱘蛋白酶活性的影響(IU/prot)Tab.3 Effects of starvation and refeeding on protease activities (IU/prot)in Siberian sturgeon Acipenser baerii in various groups(n=3;±s±SD)
注:同列中標有不同母者表示組間差異顯著(P <0.05);標有相同字母者表示組間差異不顯著(P >0.05).下表同
表4 饑餓和恢復投喂對各組西伯利亞鱘脂肪酶活性的影響(IU/prot)Tab.4 Effects of starvation and refeeding on lipase activities(IU/prot)in Siberian sturgeon Acipenser baerii in various groups(n=3;±s±SD)

表4 饑餓和恢復投喂對各組西伯利亞鱘脂肪酶活性的影響(IU/prot)Tab.4 Effects of starvation and refeeding on lipase activities(IU/prot)in Siberian sturgeon Acipenser baerii in various groups(n=3;±s±SD)
表5 饑餓和恢復投喂對西伯利亞鱘淀粉酶活性的影響(IU/prot)Tab.5 Effects of starvation and refeeding on amylase activities (IU/prot)in Siberian sturgeon Acipenser baerii in various groups(n=3;±s±SD)

表5 饑餓和恢復投喂對西伯利亞鱘淀粉酶活性的影響(IU/prot)Tab.5 Effects of starvation and refeeding on amylase activities (IU/prot)in Siberian sturgeon Acipenser baerii in various groups(n=3;±s±SD)
2.4 饑餓和恢復投喂對西伯利亞鱘道和肝淀粉酶活性的影響
饑餓結束時,S10 組、S15 組腸和肝淀粉酶活性顯著低于對照組(P <0.05),S5 組腸道淀粉酶活性顯著高于對照組(P<0.05)。恢復投喂后,饑餓組腸和肝淀粉酶活性恢復至對照組水平,與對照組差異不顯著(P>0.05)(表5)。
3 討論
3.1 饑餓對魚類消化酶活性的影響
魚類為適應饑餓狀態,需調整自身各種酶的活性來合理利用體內的貯存物質以維持生命。饑餓對魚體消化酶活性的影響因魚的種類、酶的種類、饑餓時間等不同呈不同變化。短期饑餓時,麥瑞加拉鯪Cirrhina mrigola 幼魚淀粉酶活性的損失量均高于蛋白酶和脂肪酶[13]。錢云霞[2]研究了饑餓期間花鱸蛋白酶活性的變化,發現饑餓使魚體各部分蛋白酶活性均有所下降。在短時饑餓下虎鯊淀粉酶活性下降,持續饑餓則開始上升[3]。饑餓期間,褐菖鲉Sebastiscus marmoratus 的蛋白酶、淀粉酶活性呈先升后降趨勢,脂肪酶活性則緩慢降低[14]。饑餓明顯影響施氏鱘Acipenser schrenckii 幼魚消化酶的活性,饑餓7 d 時,所測的蛋白酶、脂肪酶和淀粉酶的活性均有明顯下降,但隨饑餓時間的延長,不同消化酶活性的變化不同[4]。
本研究中,饑餓5 d 時,西伯利亞鱘腸和肝淀粉酶活性均升高,其變化情況與所報道的結果類似[8];饑餓15 d 時,西伯利亞鱘蛋白酶、脂肪酶和淀粉酶活性均低于對照組。饑餓初期消化酶活性升高是魚體對饑餓做出的應激反應,通過調節消化酶活性,達到積極利用體內的貯存物質,得以維持生命的目的[15-17]。饑餓15 d 時,西伯利亞鱘腸和肝消化酶活性降低的原因可能是饑餓時間偏長,其消化腺組織結構受損最終導致酶活性的下降[9,18-20]。
3.2 恢復投喂對魚類消化酶活性的影響
魚類饑餓后恢復投喂消化酶活性變化因種類的不同而異。西伯利亞鱘繼饑餓后恢復攝食,淀粉酶活性有所下降,可能是魚類在重新獲得食物后,環境不再惡劣,淀粉酶活性便隨之下降[8]。錢云霞[2]認為,在恢復投喂時,由器官實質性變化引起蛋白酶活性下降的恢復會遲緩,具體饑餓多長時間花鱸會出現這些變化還需要結合組織變化進一步研究。虎鯊饑餓后恢復喂食期間淀粉酶活性增加較快,說明魚體消化能力和能量轉化效率得到增強,以保證其獲得補償生長[3]。
本試驗中,恢復投喂后,S5 組西伯利亞鱘腸和肝的淀粉酶活性開始下降,然后逐漸接近對照組水平;其余各組消化酶活性呈上升趨勢。這與有關報道的結果一致[2,8,10]。本研究認為,短期饑餓(5d)后恢復投喂,西伯利亞鱘淀粉酶活性下降是由于應激反應過后消化酶活性逐漸恢復到初始水平的結果。饑餓10d 和15d 后恢復投喂,西伯利亞鱘消化酶活性上升,可能是環境改善,食物刺激消化酶的分泌,導致消化酶活性的升高;也可能恢復投喂后,饑餓引起的消化腺損傷得到修復,器官功能恢復正常,使消化酶分泌量增加的結果[9]。
3.3 西伯利亞鱘幼魚的補償生長效應
魚類補償生長一般分為部分補償生長、完全補償生長、超補償生長[21,22]。補償生長的有無及補償程度要由相同時間內持續飽食投喂的對照組與恢復生長期間內的特定生長率和體質量相比較而判定[23]。本研究采用“恢復喂食時間+饑餓處理時間為一定值,對照組持續投喂”的方法研究西伯利亞鱘幼魚的補償生長。從體質量來看,饑餓5 d 恢復投喂20 d 后,與對照組不存在顯著性差異(P>0.05),表明經饑餓處理5d 的幼魚具有完全補償生長效應。然而,饑餓10d 或15d 恢復投喂20d 時,體質量仍顯著低于對照組(P<0.05),說明較長時間饑餓的幼魚僅具有部分補償生長效應。
補償生長效應的解釋目前主要有2 種:①代謝水平降低。饑餓導致魚類代謝水平降低,當恢復攝食后,較低的代謝水平可以持續一段時間,這種低代謝支出使魚類用于生長的能量增多,從而提高了食物轉化率。②食欲增強。魚類饑餓后恢復喂食時,食欲明顯增強,通過提高攝食率來實現補償生長[18]。本試驗結果顯示,魚體的消化酶活性變化總體上與其補償生長相對應,而且消化酶活性的補償效應隨著恢復投喂時間的延長而不斷減弱。因此,西伯利亞鱘幼魚的補償生長效應更傾向于食欲增強的解釋。恢復投喂后魚體的代謝水平是否仍保持較低的代謝水平,需要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