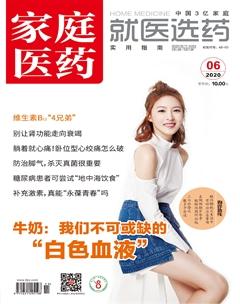心急如焚,全球目光盯向新冠疫苗
董長喜
“心急如焚。”中華預防醫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梁曉峰在談到新冠疫苗時,用這個成語形容他的心情,“但疫苗的開發既要快,又要穩,絕不能有半點疏忽。”當前,全球新冠肺炎確診人數每日劇增,在尚無特效藥物的情況下,有效預防是關鍵,因此研制新冠疫苗成為當下抗擊疫情極其重要的工作之一。“長期來看,唯有開發出有效的疫苗,才是戰勝新冠肺炎的最佳法寶。”梁曉峰說。但任何一款疫苗從研發到上市都不是短短幾個月就能完成的。
我國4款疫苗進入臨床試驗
疫情發生以來,各國都在積極研發新冠疫苗,其中進展最快的是我國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院陳薇院士團隊。4月25日,陳薇院士透露,目前腺病毒載體重組新冠病毒疫苗二期臨床試驗的508個志愿者已注射完畢,正處于觀察期,如果順利將在今年5月揭盲。“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疫苗可能是有力的武器之一。”陳薇院士說。
此外,4月14日,中國生物武漢生物制品研究所申報的新型冠狀病毒滅活疫苗開啟了臨床試驗;4月28日,中國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發的新冠滅活疫苗,在河南正式啟動臨床試驗;再加上北京科興中維生物研發的新冠滅活疫苗,我國已有4款新冠疫苗獲批進入臨床試驗階段。
全球范圍內,截至4月8日,已有115個針對新冠病毒的候選疫苗研發項目,其中78個項目研發狀態為活躍,37個項目研發狀態尚不確定。截至4月28日,有8款新冠疫苗處于研發前列,除中國的4款,還有美國2款(美國制藥商莫德納公司的mRNA疫苗和伊諾維奧制藥公司的DNA疫苗),英國1款(英國牛津大學研發,4月23日開始人體試驗),德國1款(德國聯邦疫苗所研發,4月22日開始人體試驗)。在研發速度上,美國莫德納公司與陳薇院士團隊領銜的中國康希諾生物公司齊頭并進。“我國腺病毒載體疫苗比美國稍快半步。如果5月順利揭盲,我們將繼續領先。”武漢大學醫學部基礎醫學院病毒研究所教授楊占秋說。
問世要先闖過4關
“疫苗研發有一個相對固定的程序,通常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傳統的疫苗研發平均需要10年以上。” 楊占秋解釋說,這是因為,疫苗要大規模在健康人群中接種,其安全性、有效性需要經過嚴格驗證。“疫苗研發不能在任何一個環節留下一絲隱患。”梁曉峰說。
按照通行慣例,疫苗上市前要通過4個階段。先是動物實驗階段,通常需要兩個重要步驟:在適當的動物模型中檢測疫苗是否具有保護作用;在動物身上進行毒性測試。目前國內獲批臨床試驗的新冠疫苗,都經過了上述動物模型實驗。美國莫德納公司的mRNA疫苗則未進行動物攻毒保護實驗,直接進入了臨床試驗,這也讓諸多業內人士對其有效性產生一絲憂慮。全球權威分析公司科睿唯安估計,該疫苗的成功可能性僅為5%。動物實驗后就是歷時三期的臨床試驗:一期初步考察安全性,受試者一般為幾十至上百例;二期主要進行疫苗的劑量探索研究,初步評價有效性并考察進一步擴大人群后的安全性,受試者一般為幾百到上千例;三期則是全面評價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受試者一般為幾千到幾萬例。
“一般情況下,走完全部程序少則三五年,多則十多年,一些疫苗甚至幾十年都沒做出來。”楊占秋說。不過,在當前特殊情況下,研發方案可能被壓縮,并使用加速的監管審批流程。
這次疫情可能等不到疫苗
不少科學家樂觀估計,12~18個月后,新冠疫苗有望獲批上市。這相比非應急狀態下,動輒10年的開發周期來說,已經相當快了。“飽和式的科研投入,全方位的資源傾斜,多條線工作的同時開展,科研人員夜以繼日的努力付出,評審機構無間歇滾動式的審評審批,都是新冠疫苗快速研發的基礎。” 楊占秋說。即便如此,對于這一波新冠肺炎疫情,疫苗還是可能來不及了,如果晚些時候出現第二波大規模疫情,或者在大流行后新冠病毒作為季節性病毒傳播,疫苗就會成為抗疫的關鍵因素。
“以2003年暴發的非典為例,當時我國SARS疫苗研發走到了一期臨床試驗階段,但到夏天后,病毒消失了,缺少感染人群支撐后續臨床試驗,成為疫苗研發工作中斷的原因之一。”楊占秋說,即便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控制,新冠疫苗研發計劃也不宜半途而廢,應為將來做好必要的技術和產品儲備。“這次我國開展滅活疫苗技術路線的團隊,都有過2003年應急研發SARS疫苗的成熟經驗。”
考慮到嚴峻的疫情形勢下,人們對疫苗的迫切需求,2021年初,疫苗可能根據緊急使用或類似協議提供。4月20日,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中國科學院院士高福稱,如果按正常流程,新冠疫苗可能要到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才能研發出來。但如果疫情走勢加劇,可能會在應急的情況下,先給一部分人使用。4月23日,高福院士表示,新冠疫苗有望在今年9月緊急投入使用,如果疫情再次暴發,仍處于第二或第三階段臨床試驗的疫苗可能會用到醫療工作者等特定人群上。
值得強調的是,只寄希望于用疫苗控制疫情是不夠的。美國馬薩諸塞大學醫學院終身教授、國際疫苗協會前任主席盧山指出:“目前的防疫主要還是靠隔離等方式。”即使疫苗研制成功,也要科學看待疫苗,其免疫效果并非持續一輩子,因此不要完全依賴它,應繼續保持良好的防病習慣。
【時評】器官轉運綠色通道文件要“早學習”
5月1日,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胸外科醫生方澤民坐高鐵前往北京西站取愛心捐獻供肺,準備護送回來為該院一位重癥患者做肺移植手術。不料,返程出現意外,方澤民沒能趕上原定的高鐵。在請求開通綠色通道未果的情況下,方澤民多方求助,甚至“逼”著自己在候車廳大聲求助,詢問有沒有乘客愿意幫忙帶運輸箱。
盡管此事最后得到了妥善處理,肺移植手術如期開展,但卻暴露出人體器官轉運工作仍然存在一些問題,急需改進。
2016年4月,國家衛生計生委、公安部、交通運輸部、中國民用航空局、中國鐵路總公司、中國紅十字會總會聯合印發通知,要求建立人體捐獻器官轉運綠色通道。具體到鐵路方面,如出現誤點情況,鐵路部門可優先安排臨近車次,必要時可登車后補票。如列車座位不足,可在鐵路部門聯系人協助下先登車后補票,盡量縮短人體捐獻器官運輸時間。然而,當攜帶救命肺源的方醫生因為錯過原定高鐵而向鐵路部門求助時,卻三番五次被拒絕,理由是疫情防控期間不允許先上車再補票,因為這樣無法追查到個人行蹤。
疫情防控雖然重要,但既然對方已經出具了單位介紹信和器官接收確認書等證明材料,鐵路方面理應特事特辦,而不是刻板地執行防疫要求。事后,北京西站方面說,他們要認真學習器官轉運綠色通道的相關文件,支持綠色通道工作。器官轉運事關生命,我們期待所有相關鏈條、環節上的工作人員,在入職學習時都能補上這一課,并在實際工作中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