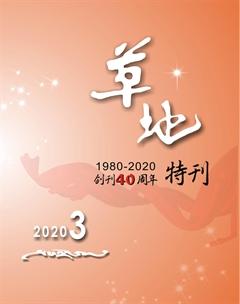這是一塊文學的草地
2020-07-04 02:07:42白林
草地
2020年3期
馬爾康崇列街65號是《草地》編輯部的所在地,也是我常會去拜訪的地方。
當年,我還是一名在校生的時候,在圖書館就曾閱讀過這本在全國公開發行的文學雜志的創刊號,當時叫《新草地》。參加工作后,也曾訂閱過這本雜志。
光陰荏苒,歲月如歌。轉眼《草地》雜志已經走過40年風風雨雨的歷程了,要道一聲可喜可賀。
回顧時間里的過往,不禁讓人感慨萬千。我不僅是《草地》忠實的讀者,還是伴隨著她一起成長的作者。每當我想起《草地》時,絲毫不吝惜內心那份對文學的執著和感激說:我是《草地》培養的作者。
1984年,我大學畢業分配來到了九寨溝工作。除了從事教師職業,心中還揣著一個年輕人的文學夢。
1986年《草地》第2期發表了我的短篇小說處女作,責編就是阿來。我也因此成為了這塊文學草地上一名年輕的作者。
就是這樣的緣由,我也就開始了與《草地》編輯部和編輯們長達三十多年的交往。
1985年的暑假,阿來、江漫兩位編輯來九寨溝組稿并舉辦文學講座,在縣城十字街口張貼了海報,我到郵局辦事路過,無意間看見了海報,就開始向人打聽來到了縣文化館二樓的閱覽室門口,當時文化館的負責人一臉緊張和嚴肅問我說,“你來做啥子?”我說,“來聽文學講座呀。”他又接著說,“這些都是作者們在開會。”言外之意,我不是作者,不能參加。
當年,我二十剛出頭,不修邊幅,零亂的長發,牛仔褲,嘴里叼著香煙,一看就不像是單位上的人。因此,也就難怪人家把我誤認為是社會上的閑雜人員。……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