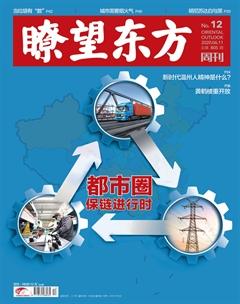沙溪:山間鈴響馬幫來
荊方
如果說大理和麗江是彩云之南胸襟上耀目的玫瑰,沙溪古鎮(zhèn)則是藏在發(fā)髻里的一朵幽蘭。同樣是茶馬古道上的重鎮(zhèn),它的身影在大山的縫隙里若隱若現(xiàn),跟艷光四射的大理和麗江無法相提并論。
沙溪古鎮(zhèn)是一個青山環(huán)抱的小壩子,處于大理和麗江之間,距離兩者都是一百多公里。鎮(zhèn)上四分之三的居民是白族,它被稱為“茶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千年古鎮(zhèn)”。
沙溪雖小,歷史卻長,可以追溯到戰(zhàn)國時期。
早在 2400多年前,沙溪先民便已擁有青銅冶煉技術(shù),是滇中青銅文化的發(fā)祥地之一。
從唐朝到民國的一千多年間,馬幫馱隊浩浩蕩蕩走過沙溪,用財富和文明一遍遍淘洗這個深山里的邊陲小鎮(zhèn),沙溪逐漸展示出令人沉醉的美麗和舒適。
唐代以后,沙溪周圍陸續(xù)建成了四大鹽井――彌沙鹽井、喬后鹵成井、云龍諾鄧鹽井、蘭州啦雞鹽井。
沙溪的地位發(fā)生質(zhì)變,不再是單純的驛站式居所,它在茶馬古道上財富傳遞者的身份上,多加了一層財富生產(chǎn)者的身份。舉足輕重的鹽都,一顰一笑都影響著周圍地區(qū)的經(jīng)濟。元代開始,沙溪古鎮(zhèn)就成為滇西北炙手可熱的重鎮(zhèn),這種繁華一直持續(xù)到民國。
大江大河的遠方和大風(fēng)大雨的未來都已不屬于沙溪,一種鄉(xiāng)愁似的安寧和寂寞代替了往昔的熱鬧,很像我們遠離的故鄉(xiāng)——在那斑駁暗淡的孤單里,藏著我們多愁善感的成長。
寺登街的鮮花
沙溪古鎮(zhèn)的靈魂是寺登街。寺登街以四方街廣場為中心,由東巷和南北古宗巷為主干,加上若干曲徑通幽的小巷子,羅致成大型居民區(qū)。整個居民區(qū)幾乎全是百年老屋,朱漆梁柱,粉墻黑瓦,站在東巷口望向寺登街,燦爛的艷陽透過路旁的依依楊柳,把街道掩映得半明半暗,街道分為主干道和行人甬道。
兩條小水渠在斑駁的樹影下水光閃爍,就像馬隊里一路響起的銀鈴鐺。小水渠的另一側(cè)是臨街的商鋪以及人行甬道,人車分流就用小水渠和路邊的楊柳隔開。
這種街區(qū)布局,很像《東京夢華錄》里記載的宋代汴梁城的大街:主干道和人行道被路兩邊的兩條水渠隔開,沿著水渠兩邊是桃樹、杏樹組成的綠化帶,春夏之際漫天彩云,花瓣落滿清澈的水面。
寺登街的鮮花比汴梁城還多,除了間雜在楊柳里的花樹,每個商家門前都有各色小花壇,有的院落外墻上還會垂掛下一簇瀑布樣的粉薔薇。間或從墻里飄出一段古老的曲調(diào),可能是流傳千年的劍川古樂《浪淘沙》。這些誕生于唐宋之間的古曲已經(jīng)失傳,但是在寺登街還有老人會彈奏完整的曲調(diào)。走在這樣的街頭,腳步自然會放慢、說話自然會放輕——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
四方街的古戲臺
四方街是一個南北長約300米、東西寬約100米的小廣場。因為常年接待馬隊,沙溪古鎮(zhèn)的布局比別的古鎮(zhèn)多了一層疏朗的氣象,四方街比麗江古鎮(zhèn)的要大很多,開闊的格局令人精神一振。
廣場以整齊的紅砂石鋪地,圍繞廣場是保持著百年原貌的各色店鋪,朱漆的隔扇門上雕著古老的木雕圖案,幽暗的花窗里坐著白族女人,正在一針一線地刺繡著千年不變的紋樣。
廣場中部,坐東朝西是一座魁星閣古戲臺,這是一座建成于清代的古建筑,但是風(fēng)格俏麗明快,第一層是梁柱支撐的穩(wěn)穩(wěn)基座,第二層是有頂無墻的大舞臺,第三層是精巧的小閣樓,每一層都有細高的飛檐指向遠方。
戲臺正對四方街廣場,讓人遐思那萬頭攢動的觀看場景。事實上,現(xiàn)在每年二月初八“太子會”,沙溪人依然會組織盛大的慶祝活動,全鎮(zhèn)人盛裝出現(xiàn)在四方街廣場,還有人登臺表演,一切遵循古制。沙溪人個個能歌善舞,據(jù)說沒有上過這個古戲臺表演的,不算合格的沙溪人。

沙溪古鎮(zhèn)玉津橋
戲臺對面是沙溪古鎮(zhèn)的另一個標志性建筑——興教寺。寺院建于明代,現(xiàn)在大殿里的某塊瓦片上還有“永樂十三年乙未年四月初四”的字樣。寺院大門前有兩棵參天古槐,距今已有三百年歷史。
沙溪古鎮(zhèn)的興教寺,是全國唯一遺存的白族密宗佛教寺院。寺登街在古時被稱為“南壇”,意為南面的佛壇,興教寺擴建后,“南壇”便改名為“寺登”。興教寺的建筑是三教合一的樣式,儒釋道在這里輪流執(zhí)政,體現(xiàn)了沙溪人海納百川的生活狀態(tài)。白族話的“登”就是“地方”的意思,寺登街這個漢白交織的地名,彰顯它奇特的身世。
優(yōu)雅奢華溫柔鄉(xiāng)
但凡富庶殷實之地,經(jīng)過幾代人的滋養(yǎng)后,往往催生出優(yōu)雅、奢華的生活方式。撥開寺登街今天平淡的生活,總能發(fā)現(xiàn)昔日的鳳毛麟角。
四方街的周圍民居街巷交錯,庭院深深。這些散落在街巷深處的宅院,飛檐高翹、磚雕層層,都有著白墻灰瓦、規(guī)格嚴整的建筑風(fēng)格。這些院子的規(guī)格或是“三坊一照壁”;或是 “四合五天井”,最奢華的是“走馬轉(zhuǎn)角樓”,庭院里樓宇環(huán)抱、花木扶疏,那寬闊的奢華不像民居,倒像是王公貴族的后花園。
從興教寺出來,沿著東巷慢慢走,經(jīng)過一個手工木雕小店,再路過一個掛著小燈籠的客棧,石板小路突然到了頭,眼前是東寨門,東寨門外一條緩緩流淌的大河赫然攔住去路,仿佛一場清夢未醒,船卻已靠岸。
寺登街完好地保存著三道寨門——東寨門通往大理、洱源;南寨門通往漾濞、喬后鹽井;北寨門通往西藏。東寨門外黑惠江平穩(wěn)浩蕩,百年玉津橋連接兩岸。
馬幫鈴聲漸行漸遠
2001年,一群瑞典人驚訝地發(fā)現(xiàn)了這個寶藏古鎮(zhèn),世界紀念性建筑遺產(chǎn)基金會宣布寺登街入選2002年101個世界瀕危建筑保護名錄,沙溪寺登街被稱為“茶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這個連接西藏和東南亞的古集市保留著當年的全部面貌,令世界驚嘆。
沙溪的富貴湮滅于20世紀,隨著機械化的到來,馬幫的鈴聲漸行漸遠,幸運轉(zhuǎn)盤的指針在20世紀50年代悄然劃過了沙溪。1952年云南省修建214省道,繞開了沙溪這條古老的路線另辟蹊徑。失去了交通的護佑和鹽都的加持,沙溪漸漸淡出人們的視線。如果不是自駕,無論你用什么交通工具,都必須在劍川縣城轉(zhuǎn)乘長途汽車,45分鐘才能抵達古鎮(zhèn)。
當最后一隊馬幫叮叮當當走過四方街寬闊的廣場,古鎮(zhèn)人過起了波瀾不驚的小日子。大江大河的遠方和大風(fēng)大雨的未來都已不屬于沙溪,一種鄉(xiāng)愁似的安寧和寂寞代替了往昔的熱鬧,很像我們遠離的故鄉(xiāng)——在那斑駁暗淡的孤單里,藏著我們多愁善感的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