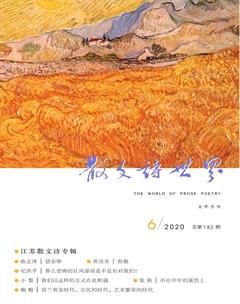往來的光陰(組章)
鋤禾日當午
草如同光陰,永無休止。
但必須除,像艱苦的生活,挨著也要過。
扛著命運的用具,吃力不一定討好。除去黑發中最年輕的部分,劃定脊背上遼闊的版圖,讓汗水放肆地奔跑,比野馬還要無所顧忌,比春風勝過千里仍不如你。
而汗水能永葆青春,不會累,不會病,只是它們透明的身體不適宜久居人間。但至今我沒明白,它們都去哪了?如果咸味是對青春的認同,那么,父親用力甩下鋤頭時,翻墾起來的,為什么是他日漸枯黃的模樣?
再長的根須也抵不過一把鐵器帶來的悶雷。也庇護不了陽光熱辣的心跳,在一雙疲憊的眼睛里成為記憶中微弱的嘆息。
鋤禾日當午,需要躬背,無需屈膝,涼帽在田野里摁下指紋,默認著一個黑影托起的前半生,有多么地光亮如新。
汗,滴落了,仿若父親被菜刀割傷的手指,血正在微笑中靜靜滑落……
夕陽西下
老牛哞叫時,不小心把夕陽掉了出來。他羞澀、慚愧,低著頭默默地嚼起了偷來的部分浮閑。
蚊蠅在他龐大的身軀之上吸食,而他不理不睬,因為他知道,它們吸食的,只能是漫天黑夜了。
偶爾抬一下頭,嘴邊白沫一再表露著:揮汗如雨的溫情里無須牽繩懸掛,也會“咄咄”向前,給大地一個沉重的歉意。
向前,不緊不慢,他不愿更快地走進黑夜,成為月亮的一個把手。
牛角已安靜地勾住東西兩端,不經意地甩一甩耳朵,天就被勾破了一些,漏出微曦的第一聲呢喃。而牛角暫時無法吹響,光陰之鋸還未磨礪出齒痕。
是的,都不容易。
想起年老而瘦弱的父親黃昏時燒開的第一爐水,沸騰的水泡急不可待地來到人間,似乎有著某種無法說出的緣由,需要它們趕在黑夜之前吐納翻新。
而他,不緊不慢地倒入窄小的瓶口,然后再次安逸地等待木柴拿出另一半的浮閑。
梯 子
竹子被換一種方式生長,人在換一種方式搖曳。
這些都被光陰默認,但均無知覺。
節節攀升的欲念在它空心的身體內“嘎吱”作響,似乎在提示:不要轉身,不要使光滑的竹竿變成懸崖。
因為,懸崖看不見自己有一只驚叫的腸胃,也無功名利祿的悲歡小心思,靜默地倚斜于時間粗重的喘息中。
也可用“擺布”稀釋混沌的高高在上。鏤空的方塊里,重量得到種植,并收獲贊譽。
而昂首是讓梯子接受一個清醒的自己,如同它郁郁蔥蔥時甩出去的秀發。而如今,它只能借助堅實的墻,與人間達成某種認知。
那天,看見父親在梯子上尋找屋瓦被光陰咬破的傷口,他沉重的呼吸,使一段風看見了瘦弱的自己,而成為黑夜里某種咳嗽拿出來的協議。
我們頃刻間,畏懼于時光退潮后裸露的錯覺之中。
作者簡介:夏杰,江蘇作協會員,有詩歌作品發表于《詩刊》《星星》《揚子江》等刊物,獲獎、入選若干,著有詩集《靜靜地述說》《恩澤》兩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