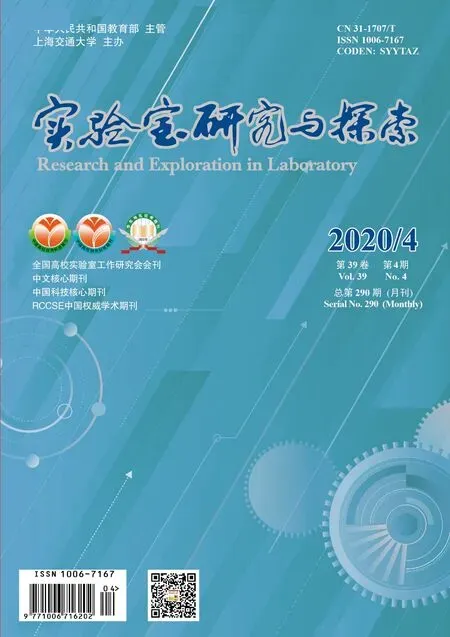高校R&D投入與多維度創新績效關系研究
李 佳,韓軍輝
(太原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山西晉中030600)
0 引 言
近年來,國家經濟轉型升級的持續加速對創新的需求與日俱增。高校作為社會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擁有大量的科研人員、完備的知識體系和輕松的創新環境,在社會創新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引領角色。如何提升高校創新能力直接關系到國家的創新建設。同時,合理分配有限的社會資源能夠最大限度地提升高校的創新能力。因此,研究高校R&D投入與其創新績效的關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 文獻綜述
目前,有關R&D投入與創新的研究,可以根據研究對象的不同將其分為兩種。以企業為研究對象。Wakelin[1]認為企業的生產率增長與R&D支出密切相關。Scherer[2]以美國企業為研究對象,得出企業R&D投入可以促進創新績效。Griliches等[3]通過控制行業變量驗證了上述結論。嚴焰等[4]以問卷數據為研究樣本進行實證分析,R&D投入的增加會促進企業創新產出。高楠[5]通過計算灰色關聯度,得出兩者存在正相關關系。李鵬等[6]將企業的創新績效分為創新科技績效和創新經濟績效,并采用面板數據模型得出企業R&D投入對創新科技績效的促進作用優于創新經濟績效。此外,Hausman等[7-9]均認為企業R&D人員的投入對其專利申請有顯著的促進效應。另一種是以高校為研究對象。付曄等[10]以57所教育部直屬高校為研究對象,從微觀層面出發系統地分析了R&D資源投入對不同類型高校專利產出影響的差異性。趙慶年等[11]通過將高校的面板數據劃分科類得出R&D全時人員可以促進綜合大學、農林院校及醫藥院校的授權專利,但對工科院校和師范院校的授權專利沒有影響的結論。楊靜等[12]認為R&D經費的增加可以增加高校的專利申請量,而R&D人員的投入對此卻沒有顯著影響。周風華等[13]在探討資源對大學技術轉移的作用時也發現R&D人員數對高校專利申請量沒有影響。張曉月等[14]發現R&D人員投入對北京地區高校的專利產出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對非北京地區高校沒有影響,但能增加后者的科技論文產出數量。
根據以上文獻回顧可知,研究中大部分學者已將R&D投入側重于人員投入或經費投入的某一方面,同時將高校的創新產出聚焦于科技創新,實證分析了R&D投入與專利產出的關系。但高校R&D投入并不只有人員和經費兩方面的投入,還包括R&D項目的數量。R&D項目是指研究與開發項目,具有一定的鉆研性、創造性和冒險性,這些特點決定了R&D項目在開發過程中一定伴隨著大量的創新產出。為了更加準確、全面地反映高校R&D的投入情況,本文選取了R&D基本人員、R&D全時人員、R&D經費和R&D項目數量4個指標共同衡量高校的R&D投入。另外,考慮到數據處理和實證分析的便利性,本研究還采用多指標面板數據因子分析對R&D投入“降維”。高校作為社會創新體系中的中流砥柱,培養人才、科研創新、傳播知識等均是其主要職能,專利產出也僅僅是其創新的一部分。為提升自身學術水平和競爭地位,學術創新在高校創新產出中至關重要。此外,高校在追求科技創新和學術創新的同時,在經濟上尋求突破必定會為其進行科技和學術創新提供一定的經濟基礎進而促進其總的創新績效。因此,為了進一步明確高校R&D投入對不同維度創新績效的影響差異,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采用更為綜合的R&D投入指標(R&D基本人員、R&D全時人員、R&D經費和R&D項目數)研究高校R&D投入與創新績效的關系;將高校創新績效定義為科技創新、學術創新和經濟創新3個維度,采用2008~2017年的省際平衡面板數據實證分析了不同區域高校的R&D投入對其創新績效的影響;同時根據結果分析造成差異的可能原因并據此提出建議以進一步釋放我國高校創新的潛力。
2 研究方案設計
2.1 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高校的主要創新產出有論文、專著、發明及專利等。論文和專著更側重于學術創新,而發明、專利更側重于技術創新,技術轉讓收入則更側重于經濟創新。為了進一步明確高校R&D投入對創新績效的影響,將高校的創新績效分為學術創新績效(Y1)、科技創新績效(Y2)和經濟創新績效(Y3),分別選擇發表學術論文數、專利授權數和技術轉讓收入作為衡量指標。其中,學術論文不僅能夠表征高校的知識轉移,也是衡量其科研水平的重要指標,可用來反映學術創新績效[15];專利授權數是高校進行科學研究的實際成果,可用于衡量科技創新績效,技術轉讓收入則是從經濟效用角度反映創新成果,能夠代表經濟創新績效[6]。這3個指標的數值越高,意味著高校的創新績效越好。此外,為了消除價格變動帶來的誤差,上述技術轉讓收入需用當年各省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對初始數據折算(以2007年為基期)[16]。
(2)解釋變量。R&D投入一般包括R&D基本人員投入(x1)、R&D 全時人員投入(x2)、R&D 經費投入(x3)以及R&D項目投入(x4)。通過對2008~2017年30個省份的面板數據進行多指標面板數據因子分析將R&D投入的多個指標降維成一個變量。具體步驟如下:先用計算出來的R&D價格指數對R&D經費投入進行折算(以2007年為基期)[17],然后將得到的數據和另外3個變量的初始數據標準化以降低數據間單位差異所帶來的誤差。將處理過后的面板數據按時間順序平鋪成一個大的截面數據,通過SPSS進行因子分析適用性檢驗。得到的KMO值為0.770,Bartlett檢驗的概率值為0.000,說明可以進行因子分析。運用主成分分析法可以進一步確定所取的4個指標可以縮減為一個綜合指標,其因子得分系數分別為0.261、0.261、0.254 和0.258。所以,高校的R&D 投入為:X1=0.261x1+0.261x2+0.254x3+0.258x4。這里的x1、x2和x4均為初始數據,x3為平減后的R&D經費投入。
(3)控制變量。參考張曉月等[14]對高校R&D人員投入與專利產出關系研究中的變量測度,選取高校所在省份的科技環境、經濟環境以及國際交流程度等環境變量作為控制變量取對數計入回歸模型。其具體衡量指標如表1所示。

表1 控制變量測度表
其中,高校所在省份的GDP需用各省份當年的GDP指數進行平減(以2007年為基期)。
2.2 模型構建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是發表學術論文數、專利授權數以及技術轉讓收入,前兩者只能取非負整數。對于這類計數型數據,通常可以采用“泊松回歸”和“負二項回歸”兩種回歸模型。但“泊松回歸”要求被解釋變量的觀察值的期望與方差必須相等,而當被解釋變量的觀察值呈現出方差大于均值的過離散特征時,可以考慮使用“負二項回歸”。通過對本文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發現被解釋變量——論文數量和專利授權數的期望遠小于其方差,如表2所示。所以,當被解釋變量是學術創新績效和科技創新績效時,采用負二項回歸進行實證分析。

表2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此外,技術轉讓收入是非計數型數據,將初始數據標準化后計入多元線性回歸模型進行實證分析。考慮到高校創新產出的滯后性,本文將解釋變量的滯后期設定為1年。
當被解釋變量為學術創新績效時,模型的具體設定如下:

當被解釋變量為科技創新績效時,模型的具體設定如下:

當被解釋變量為經濟創新績效時,模型的具體設定如下:

上述模型中,s代表高校,t指的是年份。其中,為了消除量綱以及變量本身帶來的影響,模型3在進行回歸分析前需將所有數據標準化。
2.3 數據來源
為了確保數據的真實性和可靠性,本研究數據主要來源于2008~2017年《中國高等學校科技統計資料匯編》和《中國統計年鑒》。參考梁樹廣對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效率的研究中對區域的劃分,將30個省份劃分為東、中、西三大區域[18]。
3 實證結果分析
本例中,聚類穩健標準誤(68.72)與普通標準誤(211.98)相差較大,傳統的豪斯曼檢驗不適用。因此,本研究采用輔助回歸檢驗使用固定效應還是隨機效應模型。3個模型匯報的χ2(4)統計量分別為51.602、24.352、104.372,p值分別為0.000 0、0.000 1、0.000 0,所以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分析高校R&D投入對創新績效的影響,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從全國總體水平出發,高校R&D投入對其創新績效有高度顯著的促進效應。高校R&D投入對其學術創新績效的影響彈性系數為0.124,對科技創新績效的影響彈性系數為0.292,對經濟創新績效的影響彈性系數為0.463,且均為高度顯著。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不同地區高校的R&D投入對其創新績效的影響有著顯著性差異。對于東部地區而言,高校R&D投入對學術創新績效有顯著的促進效應,彈性系數為0.136;對科技創新績效和經濟創新績效的促進效應均高度顯著,彈性系數分別為0.808、0.444。可見,東部地區的R&D投入對創新績效的影響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中部地區高校R&D投入對學術創新績效和科技創新績效的促進作用均不顯著,卻對經濟創新績效有顯著的促進效應。西部地區高校R&D投入對學術創新績效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但對科技和經濟創新績效的影響彈性系數分別為-0.061、0.460,且不顯著。顯然,中西部地區高校R&D投入對創新績效的影響明顯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原因可能在于中西部地區高校的質量遠低于東部地區,這直接導致其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均落后于東部地區;同時,中西部相對落后的經濟環境、較為閉塞的交流環境在某種程度上會導致其創新環境不如東部地區輕松,這些都限制了高校創新。而東部地區不僅受到自身高水平經濟、科技環境的影響,還受到周邊高水平經濟、科技環境的牽引,不同省域之間可以便利地共享對方的創新資源,進而促進整個地區的創新績效。

表3 R&D投入與創新績效之間的回歸結果
此外,從總體水平來看,高校R&D投入對經濟創新績效的促進作用最為明顯,科技創新績效次之,對學術創新績效的影響最弱。但東部地區高校R&D投入對科技創新績效的促進效應最強,經濟創新績效次之,學術創新績效受其影響最小。中部地區的經濟創新績效和西部地區的學術創新績效受高校R&D投入的影響波動較為明顯。說明我國東、中、西部的高校創新發展嚴重失衡,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經濟發展不平衡的限制,也受到政策環境的制約。東部地區的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經濟繁榮,高新技術產業的飛速發展使得其創新資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進而導致其科技創新績效和經濟創新績效受R&D投入的影響更為明顯。
4 結論與建議
基于全國30個省份2008~2017年的創新產出,從學術、科技和經濟3個維度探討了高校R&D投入與其創新績效間的關系,得出以下結論:從全國總體水平來看,高校R&D投入對其創新績效有高度顯著促進效應,其中,對經濟創新績效促進作用最為明顯,科技創新績效次之,對學術創新績效的影響最弱;從區域水平來看,東部地區的高校R&D投入對其創新績效的促進作用較為顯著,且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而中西部高校的創新績效受R&D投入的影響不明顯,且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說明我國區域間高校的創新發展嚴重不平衡。
基于以上結論及分析,建議如下:對于政府而言,應該重視東部與中西部發展嚴重失衡的現象,加大對中西部創新的政策扶持,并通過控制和優化創新資源的配置引導協同創新,充分發揮政府在企業、高校和研究院所協同合作中的協調作用。對于東西部高校而言,在重視、優化要素配置的同時,還要建立合理的薪酬獎勵制度。對參與人員有足夠的吸引力、誘惑力的創新目標是創新得以順利實現的先決條件,參與方的收益是高校創新系統形成的強勁動力[19]。此外,高校也可以對教師、科研人員采用更為靈活的任用制度,構建更有競爭力的薪酬獎勵制度,優勝劣汰,進而調動工作人員對創新的積極性和熱情,提高創新績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