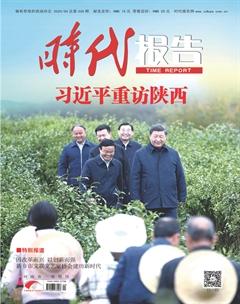口罩戰疫
董傳軍

一
早晨,太陽懸掛著寒霜,從豫北黃河灘地平線冉冉升起。人們忙碌著掛燈籠、貼對聯,準備過年。
田書增眉頭緊鎖,凝視著手機屏,武漢新冠肺炎感染數字跳躍式的攀升使他意識到:“武漢疫情越來越嚴重,并且快速向全國各地蔓延,像當年的那場非典……”
此事,事關重大,容不得猶豫,他火急火燎地趕到廠里。
這天是2020年1月20日,農歷臘月二十五。
農歷臘月二十四,長垣健琪衛材公司召開了年會,開啟了放假“模式”,職工們踏上了回家的路程,準備過個輕松愉快的春節。
當天,鐘南山院士的“鐘聲”響起,武漢新冠病毒出現了人傳人現象,建議人們出門要戴上口罩……
深夜,田書增緊急召開企業高層會議,心情沉重地說:“憑我的經驗,這次新冠病毒疫情可能是場硬仗。武漢乃至湖北需要大量的口罩、防護服,全國各地防疫防控,十幾億人一夜之間就會戴起口罩,肯定會出現‘口罩荒‘一罩難求的現象,趕快通知職工復工,越快越好,越多越好。”
1月21日,8點,長垣市丁欒鎮健琪衛材公司辦公樓前,200多名職工,32名黨員,齊刷刷地站在國旗下。
疫情就是命令,復產就是戰斗。
昨天放假今天復工。作為口罩、防護服、隔離衣生產企業,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復工,支援武漢、支援湖北;復工,為了全國人民的生命健康。
職工們個個熱血沸騰,摩拳擦掌,蓄勢待發。
除夕之夜,華燈璀璨。
一場瑞雪簌簌而降,這原本是一家人一年中最溫馨、最溫暖的時刻,萬家團圓,情暖融融。
然而,在廠區內的無菌生產車間,紫光燈下,伴隨著機器噠噠噠的聲音,口罩機急速運轉,流水線上的女工們,從頭到腳全副武裝,全神貫注,屏氣凝神地忙碌著。
晚上10點,車間主任侯明明接到復工通知,她從許昌趕回廠里,已經是凌晨2點多,她直接到車間報到。她說:“口罩是疫情的第一道防線,關鍵時刻我不能掉鏈子。”
“流水線上的工人,兩天一夜都沒合眼了,她們爭分奪秒,加班加點。為了保障武漢前線醫用物資充足,靠一股精神在支撐,24小時日夜不舍,與疫情賽跑、與病毒爭奪時間。”總經理田書增體內虛火浮躁,滿嘴起泡,眼睛布滿了血絲,卻時刻關注著生產動態。
飄安、華西、亞都、駝人等衛材企業的職工們也接到返崗復工通知,有的剛到家端起飯碗,有的剛登上回家的高鐵,有的還在機場等待著飛機安檢……他們沒有任何猶豫,義無反顧地迅速返回企業,當天就生產出一批新的口罩、防護服。
疫情之下,一些交通“停擺”,公路被堵,村莊被封,開封、新鄉、安陽等地的職工不能上班,企業出現了“用工荒”,招工難。
長垣號召全市婦女參加“口罩會戰”,鄉鎮領導逐村動員,村干部通過大喇叭、微信群,從早到晚一遍遍地號召:“口罩企業需要用工,只要會縫紉、做窗簾、做衣服的,趕快報名,都來為國家做貢獻。”
機器日夜轟鳴“連軸轉”,企業圍墻外面,政府緊急動員,1000多名放假在家的公務員、教師、餐廳服務員、賓館經理和經商人員,主動報名當起“志愿工”“臨時工”。
第二天、第三天……長垣44家口罩、防護服生產企業全部復工,大家開足馬力,快馬加鞭地生產。
二
口罩告急,防護服告罄。
1月24日,武漢市第一醫院、武漢市中心醫院、同仁醫院等,發布第一批物資告急公告,醫用外科口罩、防護口罩、隔離衣等成為主要短缺物資。
緊接著,武漢協和醫院、武漢兒童醫院、金銀潭醫院、孝感中醫院、黃岡中心醫院等定點治療醫院的求助信息如潮水般噴涌。
1月27日,武漢市一家醫院的醫生,向采訪的記者哭訴:醫院最缺的是口罩,一天消耗約3000個,如今儲備“零庫存”。N95防護口罩、防護服一件也沒有了,只能戴著兩層醫用外科口罩,穿著反復消毒的隔離衣,再加一層手術衣……
醫護人員沒有醫用口罩、沒有防護服、沒有隔離衣,無疑是在病毒世界里“裸奔”,如在死亡線上走鋼絲,一旦失守,就會被病毒吞噬。
口罩,為人們筑起一道生命的安全屏障。
口罩嚴重短缺,注定成為這個春節最揪心的記憶。
一夜之間,“一罩難求”成為全國普通老百姓的“熱詞”,很多人從除夕開始到大年初七,沒能搶購到一只口罩。
戰疫主戰場在武漢。口罩主戰場在長垣。
長垣市是中國最大的衛生材料生產基地。擁有44家口罩、防護服等生產企業,2000多家經營衛材的企業,產品平時占據全國市場銷量的50%以上。
2003年“非典”時期,長垣的衛材企業成為全國醫療防護物資供應的“主力軍”。
曾有“長垣打噴嚏,全國衛材市場得感冒”之說。這句玩笑話,道出長垣在全國衛材市場的重要地位。
疫情籠罩,我多次到口罩生產重鎮——長垣市丁欒鎮、張三寨鎮采訪,大大小小的企業門口車水馬龍,人聲鼎沸,掛著全國各地牌照的救護車、面包車、商務車和大貨車,或排隊,或穿梭于并不寬敞的街道上。
湖南、甘肅、四川、河北、遼寧等一些地方的商家、醫院、衛健部門和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領導,直接把救護車開到廠門口,焦急等待著廠里生產線上剛剛下來的口罩、防護服、隔離衣。
此時,除萬眾矚目的武漢和湖北的醫院外,長垣的衛材企業門口,是全國人員和車輛最集中、最擁擠的地方,是一道“風景線”。
“每天來自全國的訂單像雪片一樣飄來,到廠提貨的人幾乎能站滿兩公里長的大街,口罩出廠一箱就拉走一箱。”河南飄安集團黨委書記陳廣法說。
顯然,口罩巨大的市場需求,像“井噴”一般,爆發了出來。
1月24日,除夕。晚上11點30分。
長垣第一批捐贈武漢的口罩、防護服等醫療物資,裝載了滿滿一車,從河南亞都醫療公司緩緩駛出。其中,有20萬只醫用外科口罩、200萬只一次性醫用口罩、50萬只醫用帽、20萬只醫用手套共290萬只急需醫用防護類物資,緊急馳援武漢……
三
一邊是應接不暇的訂單,一邊是原材料嚴重短缺。
站在口罩流水線旁,企業家們如熱鍋上的螞蟻,心急如焚。
熔噴布告急,輔助膠條告罄,無紡布缺貨……企業原本就儲存有限的原材料,短短的幾天,夜以繼日的生產已將其消耗殆盡。
原材料短缺,企業“無米下鍋”,產量上不去……
村莊被封,交通管制,車進不來,貨運不走……
人如潮涌,蜂擁而至,客戶帶著公函求口罩……
長垣,這個后方保障的另一場戰“疫”,全國防疫防控的生命與希望的主戰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長垣停產,全國缺貨。”
1月30日,長垣市衛材生產重點企業,直接收到了國家發改委的“軍令”:在防疫關鍵時期,希望你們能夠克服困難,盡快實現滿負荷生產,想盡一切辦法,千方百計擴大產能,為堅決打贏疫情阻擊戰,做出更大貢獻……
國家發改委、國家工信部派出特派員進駐企業,他們說:“原材料短缺、資金困難,國家調配,國家協調……一切為了疫情,一切為了防控。”
河南省省長來了,一次性頒發了999個交通特別通行證。
新鄉市、長垣市委政府決定:“墻內”的事企業管,“墻外”的事政府辦,企業實行封閉式管理,吃住行由政府統一保障供應。
各大銀行紛紛表態,授信“綠色通道”,貸款啟動“抗疫貸”。
長垣衛材企業家們表示:“疫情緊急,不停產、不漲價,保證質量,個人企業就是國家企業,一切歸國家,全力為了人民生命。”
1月30日,凌晨2點20分。一架由深圳飛往鄭州的航班,緩緩降落在新鄭機場,這架航班比原計劃推遲了25分鐘,他們在等待著5000米的醫用防護服上的密封膠條。
晚上11點,飄安集團的防護服密封膠條即將用盡,第二天將面臨斷貨停產,黨委書記陳廣法火急火燎地給國家發改委領導打電話:“企業原材料沒了,東莞的防護服密封膠條運不過來……”
“讓深圳飛往鄭州的最后一個航班捎過來。”
東莞廠方驗貨、裝貨,快速運往深圳機場。
飄安集團的拉貨車輛,也直奔新鄭機場停機坪。
飛機落地后,汽車拉著防護服密封膠條向長垣方向急駛……
與時間賽跑,讓生命接力。
天還未亮,5點30分。汽車到達廠區,在車間等候的工人們,又快馬加鞭地重新開機生產。
長垣,這場沒有硝煙戰爭的后方戰場,是一場分秒必爭的保障戰,是一場國家意志與疫情較量的總體戰。
流水線上的工人們一次次吹響了沖鋒號,一天天殫精竭慮地在拼搏,精神與精力“拼殺”,時間與產量“廝殺”。
50萬,300萬……800萬,口罩、防護服產量一天天在跳躍式地上升,一天天成幾何倍數增長。其中,50%的口罩、防護服馳援武漢。
陽春三月,隨著全球疫情快速蔓延,幾十個國家出現了疫情,長垣的口罩、防護服龍頭企業開始生產“外貿”,支援全世界。
3月1日,長垣捐贈的第一批12000個醫用口罩、500套防護服,發往疫情嚴重的伊朗,第二批,第三批運往韓國、日本、歐洲等地。
口罩,與前線白衣衛士一起,融入到世界前線“戰斗”,融入到保衛人類生命和健康戰疫之中,為世界人民贏得了生命保證。
四
這是一個特別的會議。
1月25日,大年初一。
長垣市醫療器械同業公會會長李明忠,召集44家口罩、防護衣等醫療物資生產企業開“商討會”。
“口罩原材料瘋狂漲價,我們長垣的企業漲不漲價?”李明忠開場白直奔主題。
“熔噴布、無紡布原材料價格暴漲。一天少則賠幾萬,多則賠幾十萬,真有點招架不住了。”
“不停產、不漲價,保證質量,這是我們企業對國家和人民做出的承諾。”
“國家危難中,我的企業屬于國家,絕不能發‘國難財。”
“長垣企業家知道哪頭重,哪頭輕,春節前那次會議,不是討論過了嗎?還是那句話:不停產,不漲價!”
……
企業家們你一言我一語地議論著,并一致達成共識:絕不漲價,絕不停產。
李明忠直言告訴我:“口罩看似生產量很大,其實利潤很薄。平時只有5厘錢的利潤,面對這場疫情,大多數生產口罩和防護服的企業,不僅不向經銷商漲價,也不允許經銷商向醫院漲價。為此,長垣衛材企業基本是生產一個虧一個。”
2月3日,健琪公司熔噴布告急,無紡布也所剩無幾,企業家底被掏空賠光了。田書增召集中高層管理人員共商辦法。
“從臘月二十六到現在,半個月時間,已經賠進去300多萬元,主要是原材料漲價,物流開支,人員工資還沒結算,財務資金已經空空……”財務總監含淚通報資金情況。
“停產吧!”有人提議。
“原材料蹭蹭往上漲,一天賠幾十萬。你說咋辦?”
“錢從哪里來?原材料從哪里購買?”
“不能漲價,不能停產,做企業太難了。”
面對著資金困難做賠本的生意,田書增壓力巨大,他眼噙熱淚說:“疫情面前,口罩對于中國人來說就是一根救命稻草……錢的事,我來想辦法。絕對不能停產,而且還得增加產量。”
聽到這話,全廠10多名高管委屈地哭了起來,那種酸楚、無奈、焦慮,無以言表,只有用哭聲來宣泄……
王國勝是駝人集團的董事長。這位身高僅有一米五,背部背著 “羅鍋”的殘疾企業家,疫情之初,在電視上看到武漢前線醫務人員長時間“戰斗”,面部被護目鏡、口罩壓出深深傷痕,有的甚至已經潰爛、臉部變形。他心如針刺,傷痛不已,當即決定成立一個由70人組成的抗“疫”攻關部,主攻防護類醫療產品研究。
他和同事們不曉晨夜,不知疲倦,經過三天三夜,研究出一款頭盔式“隔離帽”,經有關部門檢測合格后,立即投入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