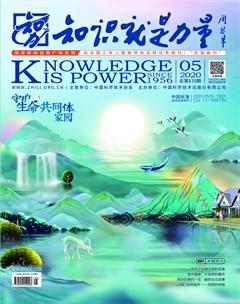消失在餐桌上的它
周晉峰 張思遠 宋琪鈺 王啟楠
作為食物鏈的頂點,人類對很多生物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僅僅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就使無數物種消失在了餐桌上。吃不是錯,但為了吃使動物種群數量越來越少卻值得我們反思——我們該學會為菜單做“減法”,口下留情了。
沒能長大的藍鰭金槍魚
藍鰭金槍魚是金槍魚類中最大型的魚種,也是幾種生活在不同水域的具有藍色魚鰭的金槍魚類統稱。它們分布于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的溫帶及熱帶海域,是海洋食物鏈頂層物種,除了大白鯊之外,在海洋中罕有敵手。
然而藍鰭金槍魚并沒有稱霸海洋。這些大魚的自然壽命約為50年,其自身生長繁殖卻非常緩慢,半數以上的藍鰭金槍魚自出生4年以后才能成熟,成熟后才能繁育后代,其中大西洋和南方藍鰭金槍魚甚至需要8~12年才能成熟。而慘痛的現實是:因為人類,97%以上的藍鰭金槍魚在3歲前便被捕撈,進而被端上餐桌,成為人類追捧的美食。
如果草原沒有狼,許多食草動物便失去了天敵,進而大量繁殖啃食植被,海洋也是如此。一方面,藍鰭金槍魚憑借速度和體型優勢,可以捕食小魚還有甲殼類的動物,避免這些底層物種繁殖過快,危及海洋生態平衡;另一方面,這種頂端物種的滅絕不僅會讓一些魚類無休止的災害性增長,還會進一步引起海洋酸化,進而可能形成海洋荒漠化。

藍鰭金槍魚
延伸閱讀:
海中的 “熱血魚雷”
藍鰭金槍魚為大洋性洄游魚類。它們體型精悍,尾鰭呈交叉狀,如同一個長了跑車尾翼的魚雷,此外還擁有“體溫自動恒定功能”——由于身體兩側有著豐富的血管網,因此它們可以保持自身體溫高于周圍水溫。這些優勢讓它們在榮獲海洋中不同水層“游速冠軍”同時,可以不懼“高能耗”,保持各項生命體征正常運轉,大白鯊要想捕獵它們,也需做好接受耐力和速度雙重考驗的準備。
小小禾花雀奪命“四級跳”
禾花雀的學名叫做黃胸鹀(wù),胸前一小片鮮艷的黃色羽毛,讓它們雖然體型與麻雀相近,但更具辨識度。它們喜歡棲息于低山丘陵和開闊平原地帶。在非繁殖季的遷徙期間和冬季,好熱鬧的它們也喜歡聚群,甚至可以形成3500~7000只的“大部隊”。它們主要以小蟲子和植物果實為食,性格警惕而膽小。
不過,這些體型小巧的家伙,卻是農田小衛士。它們的活動和棲息環境與農田密不可分,作為國家“三有”(有益、有經濟價值、有科研價值)野生動物,它們對于保障農作物安全,也發揮著不小的作用。據觀察統計,1只禾花雀1年覓食的害蟲數量等于5個農民1年滅蟲數量的總和。然而,曾經像麻雀一樣遍布各地的它們,如今已經蹤跡難尋。是什么原因導致這一巨大改變?
一個字:吃。
因為“食野”陋習的影響,以及被強行套上的“天上人參”的噱頭,使得禾花雀成為人類大量補殺食用的對象。據報道,僅2001年就有逾百萬只禾花雀成為餐桌上的佳肴。
不過十幾年間,人類的大量捕食使禾花雀的種群數量下降了99%,在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的紅色物種名錄中,其瀕危等級從無危到易危,再到瀕危,現在變成了極危,以罕見的速度完成了奪命“四級跳”,震驚世界,而這種情況如果繼續惡化下去,下一步等待它們的就是野外滅絕和最終的全面滅絕。
生態網上的你我它
地球曾經歷五次生物大滅絕,稱霸一時的恐龍在第五次生物大滅絕中徹底消失。現在,人類正處于第六次生物大滅絕進程之中,大量物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與前五次不同的是,第六次生物大滅絕不是因為“天災”,而是因為“人禍”。
根據聯合國2019年公布的一項數據顯示,在科學家們所評估的動植物組別中,平均約有25%的物種受到威脅,這意味著有大約100萬種物種已經瀕臨滅絕,如果不采取行動來降低生物多樣性喪失驅動因素的強度,其中許多物種將在幾十年內滅絕。
豐富多彩的動植物種類,構成了我們所說的生物多樣性。正是因為地球生物多樣性的存在,人類的吃穿住用行,甚至生命健康才能有所保障。比如說蜜蜂,占全球糧食總量90%以上的100余種農作物中,有70種左右需要蜜蜂傳粉,所以蜜蜂的存在,不僅僅能為人類提供香甜蜂蜜,更關系到人類賴以生存的糧食安全生產。
此外還有穿山甲,它們的鱗片被作為藥材使用,而有人認為其肉質亦有大補功效,藥用+食用的雙重需求,使得穿山甲面臨全球大圍剿。據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穿山甲工作組不完全統計,僅2019年,國內各海關已罰沒123.477噸非法走私的穿山甲鱗片。但在利益驅動下,人們已然忽略了穿山甲是白蟻的天敵,有它們存在的森林,可以免受白蟻之禍,從而也保障了其他物種在森林的安全棲息環境,避免了因森林被毀而引發的水土流失、飛沙揚塵。
自然界中,萬物相連,彼此共生,構成了生態系統健康且微妙的平衡。只要其中一環被打破,則勢必牽一發而動全身,影響生態系統整體的穩定性。人類同樣是生態系統中的一環,大量不加限制的食用其他動物,最終也必將禍及人類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