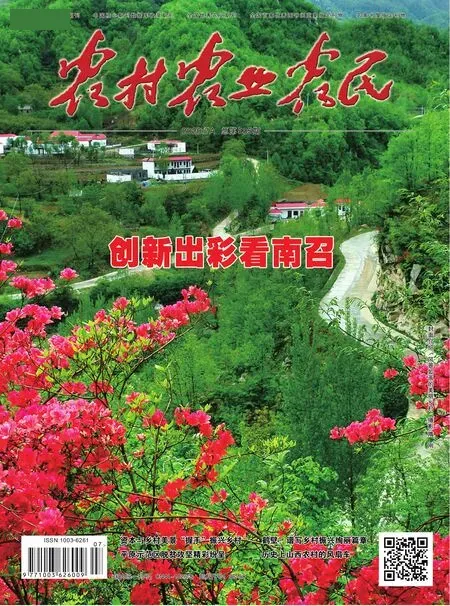七里崗上的歷史回望
朱國明
七里崗,這個地名在中國版圖上太過普通平凡而又欠乏詩意。位于伏牛山東麓的河南省方城縣獨樹鎮七里崗,慣看了千年的秋月春風,靜靜地躺在黃石山前,臥聽側畔南去的硯河水流不息和穿越其間的許(昌)南(陽)公路上的車馬喧囂。
85年前的那個嚴冬,在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山岡上,槍炮聲淹沒了呼嘯的北風,冷兵器揮去了刺骨的雨雪。高舉“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旗幟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五軍,在這里遇到了數十倍于己、裝備精良的國民黨軍隊伏擊,戰斗慘烈程度可謂“驚天地,泣鬼神”。紅二十五軍在付出沉重代價之后,勝利跳出敵人重圍,獵獵紅旗下的一支鐵流,挺進伏牛山深處,走向更大的勝利和輝煌。
60年后,江澤民同志將這次戰役稱為“血戰獨樹鎮”,并與紅軍長征中的其他6個著名戰役相并列。
80年后,習近平總書記更把紅二十五軍的這場戰役重命名為“鏖戰獨樹鎮”,與血戰湘江、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勇克包座、轉戰烏蒙山等一起并列為長征八大著名戰役。
如今,站在昔日戰場七里崗上舉目眺望,遠山如黛、阡陌縱橫,蘭(考)南(陽)高速和G234國道車流如織,南水北調中線干渠深水靜流,腳下這片曾經灑滿烈士鮮血的土地,已經成為“方城縣烈士陵園”。這里掩埋著從那時到現在有名或無名的438位烈士,蒼松翠柏間,立于1997年11月的“紅二十五軍獨樹鎮戰斗遺址”紀念碑橫空屹立。這里已成為河南省及南陽市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并正在申報國家級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這里還是河南省國防教育基地、河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每年清明,來自不同方向的人們潮涌般聚集于此,一束鮮花祭英烈,一瓣心香傳真情。即便平時,也會看到三三兩兩的人群,來到這里參觀憑吊,或仰望凝視,或駐足沉思……
1994年初春,我到獨樹鎮擔任黨委副書記,在一個乍暖還寒的日子,懷著無比崇敬的心情,第一次來到心儀已久的七里崗。從那時到現在,25年時光回轉,能夠記憶的,只有芳草萋萋的荒崗和似有似無的墳塋,還有當地一位老人對我說的話:“那可都是站那沒槍高的娃娃啊!天凍得連槍栓都拉不開了。”
那位老人肯定已不在人世,但他的話讓我記憶猶新,終生難忘。今天想起,仍然禁不住淚濕眼角,仿佛回到了那個血肉橫飛的時空。
時至今日,研究并著述那場戰役的作品已經很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于2016年10月出版《紅二十五軍卷》三卷,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叢書《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五軍戰史》也于2017年7月出版,都對七里崗戰役進行了詳盡的描述。其中《軍卷》有篇戰役親歷者陳先瑞的回憶文章叫《激戰獨樹鎮》,《戰史》記載的題目是《惡戰獨樹鎮,進入伏牛山區》,不難看出,無論從“激戰”到“惡戰”,還是從“血戰”到“鏖戰”,那場戰役是多么慘烈,她在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史上的地位和意義是多么重要。我不想贅述那些激昂的文字,但我還是要直描關于七里崗戰役的濃墨點,抑或是“滴血點”:
地點:方城縣獨樹鎮七里崗;
時間:1934年11月26日13時至16時;
天氣:氣溫驟降,雨雪交加;
地形:平坦荒崗,道路泥濘;
紅軍服裝:衣服單薄,草鞋粘掉;
軍力對比:紅二十五軍共計2980余人(其中傷病員眾多),當面之敵為國民黨龐炳勛部第四十軍一一五旅及炮兵團2966人(含圍追堵截兵力),且提前2小時進入陣地準備伏擊;
裝備對比:紅二十五軍彈藥缺乏,敵一一五旅馬匹305匹,輕武器1819支,重機槍22挺,子彈30余萬發,迫擊炮6門。
這些數字和境況,如果僅有一個或兩個單體存在,那絕對難不倒英勇頑強的紅二十五軍將士們。但是,把所有的也包括那些沒有記錄的數字和境況疊加起來,我們就可以想像紅二十五軍面臨的是何其嚴峻的形勢,正所謂“極為險惡”“生死存亡”。
今天,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光大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與85年前相比,盡管沒有窮兇極惡而且強大的當面之敵,沒有異常艱苦兇險的環境,沒有血與火交織的場面,但是我們黨仍然面臨著“四大危險”的考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路還會艱難曲折,每個人的人生之路也會有坎坷荊棘。但是,只要有紅二十五軍那種信念堅定、英勇頑強、不屈不撓的戰斗精神,我們的黨、國家、民族,乃至我們每個人都將無往而不勝!
還是把時光拉回到85年前的11月26日下午,北風凜冽,雨雪交加,在面對氣勢洶洶猛撲而來的敵軍、戰場形勢于我極其不利的情況下,軍政委吳煥先抽出一把大刀,大聲疾呼:“共產黨員跟我來!”紅二十五軍將士們士氣大振,殺聲連片,壓制了敵人的猛烈攻勢。這聲“共產黨員跟我來”凝聚了共產黨人的英雄豪氣,迸發了紅軍戰士的拼命精神,至今回想起來,仍覺振聾發聵!
吳煥先,這位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和紅四方面軍創始人之一,紅二十五軍的締造者之一,從大別山走來,七里崗戰役后,帶領隊伍進入伏牛山,轉戰于陜南的崇山峻嶺中,1935年8月21日,在甘肅涇縣的渡河戰斗中,在人生最后一句“沖啊”的吶喊聲中,不幸中彈犧牲,血水與雨水凝入了隴東的那片土地。那一年,他才28歲!
吳煥先,這是一個不朽的名字!在紅二十五軍官兵心中,他永遠是軍魂,永遠是一面大旗,他們在這面大旗下懂得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光榮、什么是身先士卒、什么是官兵一致、什么是中國工農紅軍。今天,我們的各級黨員領導干部,應當從吳煥先的光輝事跡和七里崗上一聲“共產黨員跟我來”中,悟出什么是初心、什么是使命、什么是責任、什么是擔當。
我又想起那位老人“娃娃兵”的話,是的,紅二十五軍是一支奇特的隊伍,當年的《共產國際》雜志登載的《中國紅軍第二十五軍的遠征》這樣寫道:“最堪注意的,就是這支隊伍差不多沒有年逾十八歲以上的戰斗員”。這支紅軍武裝除軍長程子華29歲,政委吳煥先27歲,副軍長徐海東34歲以外,團營干部很少有超20歲的,精心挑選的最精干的軍部交通隊戰士清一色都是十六七歲的少年,隊伍里不少是十二三歲的小紅軍,甚至還有八九歲的兒童,還有7位十六七歲的“七仙女”女紅軍……平均年齡只有十五六歲的紅二十五軍,以大無畏的革命氣概孤軍北上,以稚嫩的雙手高高擎起了一面中國革命的戰旗。這些紅軍少年在殘酷的戰爭年代,為了救國救民的夢想,為了共產主義的信仰,經歷了這個年齡幾乎不可能承受的挫折和苦難。
今天,在這個年齡段的孩子們,正在窗明幾凈的教室接受著現代教育,生活無虞,條件優越。他們承受的只是家長、學校和社會的升學壓力。雖然不能拿當年的境況與今天簡單對比,但確實要讓我們的下一代知道:他們的今天是怎樣來的,他們的明天該怎樣創造!
那么,面對當年的“娃娃兵”,作為當代的成年人,我們除了感嘆,又該作何理性的思考?這是一道人生測試題。

對于今天的大多數人來說,肯定知道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五軍,也會對紅二十五軍“鏖戰獨樹鎮”耳熟能詳,也曾到七里崗“方城縣烈士陵園”獻過心祭,但是,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紅二十五軍的前世今生呢?
20世紀二三十年代是一個狂飆突進的年代,那時的中國大地上,風云翻滾,激流涌蕩。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在黑暗中探索、抗爭。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從1926年10月起,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處的大別山區,農民革命運動轟轟烈烈,如火如荼,誕生了后來對中國革命產生重大影響的鄂豫皖革命根據地。
1931年10月25日,安徽金寨麻埠,紅二十五軍成立,隸屬紅四方面軍,軍長曠繼勛,政委王平章;1932年秋,迫于國民黨軍隊的“圍剿”,紅四方面軍主力撤離鄂豫皖根據地,奉命留守的紅二十五軍一部于11月30日重新改編,軍長徐海東,政委吳煥先;1934年11月11日花山寨會議后,在紅二十五軍開始長征前進行整編,軍長程子華,政委吳煥先,副軍長徐海東。紅二十五軍除軍直屬隊外,另轄二二三、二二四、二二五團和手槍團共近3000人。
羅山縣何家沖,這是一個和七里崗一樣不起眼的地方,但因為是紅二十五軍長征的出發地,而鐫刻在中國革命和紅二十五軍的史冊上。
1934年11月16日,這是一個值得永遠銘記的日子,紅二十五軍的將士們告別了鄂豫皖革命根據地,踏上了艱苦而曲折的長征之路。
出發之后整整10天,這支英雄的隊伍來到了七里崗……于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史上增添了慘烈而光榮的一頁,紅二十五軍軍史上寫下了悲壯而輝煌的篇章!
1935年9月15日,陜西延川永坪鎮,一支3400多人的隊伍來到這里,至此,歷時10個月,途經5個省,行程萬余里的紅二十五軍長征畫上了句號。
人民解放軍首次實行軍銜制度的10年間(1955-1965年),共授予1631位開國將帥,出自紅二十五軍的共有97位,其中:大將徐海東,上將劉震、韓先楚,中將6位,少將88位。還有初為少將、后為上將的中央軍委原副主席劉華清,以及數十名轉業到地方不能授銜的省部級以上領導干部。他們的卓著功勛將彪炳千秋,永垂青史!
《人類1000年》記述了從公元1000年到2000年人類歷史進程中所發生的100件重要事件,千年間的中國只有三件列入,而紅軍長征位列其中。參加并完成萬里長征的紅軍共有四路,紅二十五軍是其中之一,其偉大意義早有定論。我只引用當時《共產國際》雜志的評價:“中國紅軍第二十五軍的榮譽猶如一顆新出現的明星,燦爛閃耀,光被四表!就好像做毛澤東部隊的先鋒一樣,幫助毛澤東部隊打開往陜北的途徑。”
至于“鏖戰獨樹鎮”之后的紅二十五軍,限于手中資料,只能簡要描述:到陜北后與劉志丹的紅二十六、二十七軍會合,編入第十五軍團,1935年9月、10月參加了勞山戰役和榆林橋戰役,11月參加了史稱“奠基禮”的直羅鎮戰役;抗日戰爭時期,于1937年8月25日改編為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四旅,挺進華北抗日前線,1941年2月又劃入新四軍編制;1945年9月,這支部隊奉命調往東北,解放戰爭時期,歸入東北野戰軍即后來的第四野戰軍第二縱隊,在東北戰場屢立戰功,后整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十九軍,從東北松花江一直打到了廣西鎮南關;在抗美援朝戰場上,幾乎參加了所有戰役,從出國第一仗的云山戰役,直到停戰前返回祖國……還有在朝鮮戰場上被稱為“萬歲軍”的第三十八軍,也流淌著紅二十五軍的血脈……如今,承載著紅二十五軍紅色基因的第三十八集團軍歸建中部戰區,第三十九集團軍歸建北部戰區,戍守在祖國北疆的燕山深處,筑起一道新的萬里長城!
光榮的紅二十五軍,從大別山一路走來,風雨兼程,苦難輝煌,戰功卓著,精神永存!
著名作家王樹增在《長征》一書中這樣寫道:“那些犧牲在征途中的紅二十五軍的官兵,他們的鮮血日復一日地潤澤著中國遼闊的國土腹地,使那里的山巒得以蔥蘢,河水得以奔涌,使那里的每一塊田野得以豐饒。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五軍將永遠分享著人類最壯麗的史詩———長征——的光榮。”
黃石山蔥蘢,硯河水奔涌,獨樹鎮豐饒。七里崗,紅二十五軍在這里創造了歷史奇跡,創造了苦難輝煌。今天,當我們站在這里駐足矚望,無論是走向歷史的深處,還是展望遠方的未來,都可以在心靈震顫的同時,獲得無盡的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