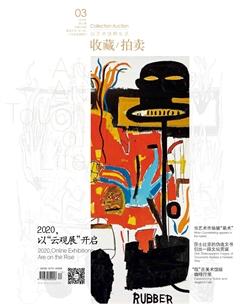柏林地堡,匿身防空洞的最潮私人藏館
峰之



在柏林市的中心地帶有一棟長相奇葩的建筑,它共有5層樓高,四面無窗,看上去非常笨重。該建筑通體由混凝土建成,沒有一絲外部裝飾,唯有一些炮彈留下的彈痕以及街頭青年噴上去的涂鴉,讓它灰白色的水泥外墻顯得稍稍有點生氣。然而這么一棟外表看上去讓人有點避之不及的建筑,每天卻接待著絡繹不絕的訪客,而且要想來此一探究竟,還得提前好幾周在網上預約。
這座建筑名叫“Bunker(地堡)”,修建于二戰時期。在地堡內部,卻存放著當下最重要的當代藝術收藏之一——博羅斯收藏(Sammlung Boros)。布滿彈孔的建筑墻身,以及滄桑古樸的室內空間,與光鮮前衛的當代藝術品形成非常強烈對比,歷史的厚重與沉淀與閃耀的當代思想在此時空匯聚交織。
赤裸混凝土變身最潮藝術空間
柏林地堡(Bunker Berlin)或許是這世界上最神秘的地標之
,即便已經站在它的門口,你依然不知道該如何正確地進入這座建筑。
生銹的鐵門、水泥抹砌的通道、昏暗的燈光……外墻面上斑駁可見,從透明電梯里可以看到外墻面厚達3米的水泥墻,建筑內部的墻也基本都有40公分厚,手機在里面完全沒有信號,這就是柏林地堡給筆者留下的第一印象。轉過拐角,挑高的門廳安置著登記臺,一間休息室攔住了所有參觀者——沒有人可以單獨在柏林地堡中行動,每一組來訪者都需要等待工作人員帶領進入展廳。而每個渴望來到柏林地堡的人都需要提前在網上預約,數量有限的參觀名額通常在一個月前就被訂滿。
在成為博羅斯藝術收藏館之前,Bunker曾有過許許多多的用途。1942年,德國納粹強迫一群勞工把它建好,作為防空工事供柏林市民躲避空難,該掩體空間巨大,可以同時容納2000人并提供空襲時的掩護。之后蘇聯紅軍占領了這棟建筑,用它來關押戰俘。再往后由于內部涼爽避光,Bunker又被用作倉庫儲存紡織品和瓜果蔬菜,直到柏林墻倒塌之后德國政府接管這個建筑,并把它改為劇場和夜總會供演出和娛樂用。
隨后又經歷了幾次關停和易主,Bunker終于在2003年被從事藝術品收藏的博羅斯(Boros)夫婦給買下,用來放大件藝術藏品,所以它如今被稱為博羅斯私人收藏館(Samrnlung Boros)。當博羅斯夫婦買下柏林地堡時,關于其是否能當作美術館使用的爭論一直在繼續:地堡墻體厚度近3米,完全由混凝土砌成;建筑內部缺乏足夠的自然光;逼仄的隔斷劃出了200個牢房般的房間。2007年,建筑改造完成,建筑師Jens Casper謹慎地改動了柏林地堡的內部結構,只有印個房間被留了下來,低矮的天花板選擇性地被移除以構造更開闊的空間。改造以一種保護的方式進行,不少原墻面上的涂鴉被保留,傳統的白盒子空間只謹慎地穿插分布在內。現在它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用在做私人現當代藝術展覽,另一部分用作私人住所。每四年更換一次展品。博羅斯及家人便居住在美術館最頂層的空間,與他們的藏品為伴。
交錯的走廊,赤裸的混凝土,防空洞獨特的建筑設計,留給了藝術作品足夠的伸展空間,伴隨著其承載的時光印記,柏林地堡自身帶有一種能量,陳列在內的藝術品被籠罩在這樣一種力量之下:色彩鮮艷的變得緘默,輕佻幽默的也多了一絲深意。來自裝置的聲音在樓層間回蕩;光束在水泥墻面上薄薄地延展;不可捉摸的氣味循著來者的腳步聲,盤旋在人們的頭頂。參觀者在進入展廳前被隔在墻的一側,展廳中作品制造出的聲響傳到每個人的耳朵里,所有人側耳傾聽建筑中的回音,期待被逐漸推向了高點……
“這建筑既不是為藝術而生,本身建得也不藝術,但用藝術來抗衡建筑本身的丑陋讓我覺得非常有意思。”收藏館館主博羅斯表示。同時他和妻子也認為大約一半的訪客對地堡的興趣大過對館藏藝術品的熱情。
博羅斯的“私人”收藏
作為全球私人藏家熱衷的聚集地之一,柏林的私人美術館數量位居世界城市第二。成長于戰后和更年輕一代的藏家也更傾向于開設自己的私人展示空間,所以柏林的私人博物館同時也是私人藏家的住所。Bunker的主人克里斯蒂安。博羅斯(Chisiion Boros)是BOROS德國廣告公司的創始人,同時也是藝術收藏家;而藝術史專業出身的凱倫。博羅斯(Karen Boros)則長期為瑞士巴塞爾藝術展工作。從2006年至今,博羅斯夫婦一直是全球頂級收藏家榜單上的常客。
博羅斯收藏藝術已超過20年,契機要追溯到1990年,他在倫敦遇到了攝影師沃爾夫岡。提爾曼斯(Wolfgang Tillmans),博羅斯從他那里購得了一些提爾曼斯本人及其他藝術家的作品。博羅斯這么評價提爾曼斯:“廣告和媒體行業光鮮亮麗,充斥著贏家。但一碰到提爾曼斯,真實的事物、尋常人中的英雄、日常生活才會出現。提爾曼斯也將街頭文化帶到了人們的視野中來。”
圍繞著博羅斯收藏建立的柏林地堡擁有一個年輕的團隊,對于博羅斯夫婦來說,美術館的工作人員需要對藝術有著絕對的熱忱。“當一個人充滿熱情時,這份感染力會帶領觀眾更快地走入當代藝術的世界。”而對藝術的熱忱,博羅斯夫婦兩人最有發言權。事實上,他們的私人居所就在美術館的樓頂。
私人收藏相較公立美術館,不存在尋找資金支持的壓力,展覽只對自己說話,不需要考慮太多公眾的想法。正是由于藏家長期專注于自己的收藏領域,他們因此所積累的知識對于機構。策展人和藝術家都有所裨益。柏林地堡凝聚了博羅斯夫婦所有的心血。十幾年來,柏林地堡一直保持著獨立運營,這意味著夫婦兩人承擔著美術館的所有開銷。這種經營模式為美術館提供了最大程度的自由,柏林地堡內的展品每四年更新一次,展覽中有博羅斯夫婦最早的收藏,也有他們近期購買的新作,博羅斯收藏的開放與多元是其最吸引人的特點之一。
布滿彈孔的建筑墻身,以及滄桑古樸的室內空間,與光鮮前衛的當代藝術品形成非常強烈對比,歷史的厚重與沉淀與閃耀的當代思想在此時空匯聚交織。此館藏品包括沃爾夫岡。提爾曼斯(WolfgangTillmons)、達米恩嚇斯特(DomienHirst)、崔西艾敏(TrocyEmin)、莎拉·盧卡斯(Sarah Lucas)、托馬斯·沙畢茲(Thomas Scheibitz)、安塞姆·雷爾(Anselm Reyle)、伊麗莎白佩頓(Elizabeth Peyton)和奧拉維爾埃利亞松(OlafurEliosson)等藝術家作品,數量多達700件,類型涵蓋雕塑、裝置、油畫、草圖、錄像、攝影等各種媒介。值得一提的是,博羅斯的裝置收藏中有很多聲音藝術作品,觀眾在經過每層樓時都有不同的聽覺體驗。這些作品都由藝術家根據空間環境特別制作。獨一無二的感官冒險
如果可以成功預約參觀,訪客們花上12歐元就可以進入Bunker。游走在地堡內部,強烈的對稱空間,仿佛行走在一個大型的迷宮之中,東西南北四部剪刀樓梯,加強了這種迷宮般的感覺,樓梯上來往的人,可以相見,卻無法相遇,奇妙而充滿詫異。
直頂天花板的高大枯樹,吊在空中由鐵絲搭成的抽象藝術創作、立在地上用幾十根日光燈管扎成的柱狀環燈、一只軸承連接在墻上的汽車輪子,甚至只是一條穿墻而過的銀白色金屬桿……博羅斯夫婦還精心放置了一些很有趣的室內裝飾物件,例如明代宮廷御用的茶幾、來自不丹寺廟里的老虎畫作、某位藝術家制作雕塑時用過的鏟子。實驗性項目用的10色光譜圖等,700多件有趣的展品錯落在地堡的各處,貫穿展覽的主線常常抽象而難以定義。
從2008年對外開放參觀到目前為止,柏林地堡累計迎來了40萬來訪者,而他們都是由12人一組的形式被帶入美術館的。這樣的觀展方式幾乎只能在這里找到,美術館知道每一位來訪者的名字,一些作品甚至開放給觀眾互動。人們來到地堡的原因不盡相同,但他們在美術館內獲得的體驗卻擁有同樣的質量。工作人員帶領來訪者走過每個房間,為重點的藏品提供背景信息,并講述收藏過程中的軼事。柏林地堡的展覽每四年更換一次,展覽從不做任何作品說明。懂的人都會會心一笑:藝術就是要讓你這樣慢下來,沉入孤寂、學會思考。
柏林地堡是藏家與藝術家之間保持聯絡的一段紐帶,有時它并不僅是一個存放藝術品的地方,還可以是藝術品本身。博羅斯夫婦鼓勵藝術家們利用地堡進行創作,并且給予他們在布展時完全的自由。2011年,藝術家組合Awst&Walther便在地堡內部墻體上打了幾個大洞,中空的金屬桿穿過漆成白色的走廊墻壁。這些作品打破了人們對于空間的預設,并且逼迫來訪者調整視角,重新思考在空間中的移動方式。
Bunker Berlin這座佇立在柏林市中心密不透風的地上堡壘,本身的身世可謂歷盡滄桑,無論是出自對當代藝術的喜愛,或是單純的獵奇心理,Sammlung Boros都是一場值得赴的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