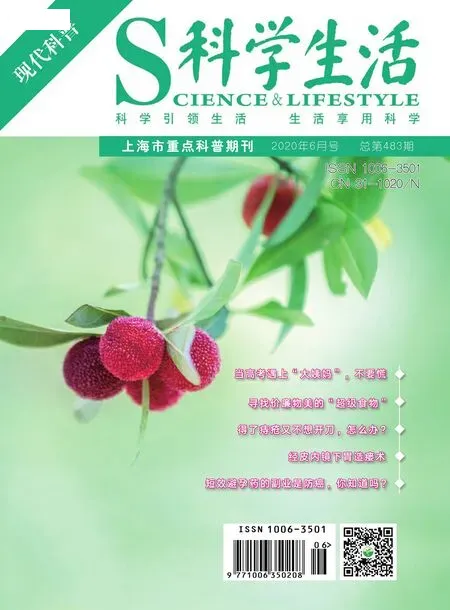婚姻在創傷中前行
文/陳露 編輯/南溪
受疫情的影響,最近幾個月的生活,對淑文(化名)來說是百般煎熬的。初二的兒子宅家上網課,不服管教,每天凌晨2點睡,次日下午一點起。先生抽煙、喝酒,天天在家不是和孩子嗆,就是做些令她看不順眼的事。
隨著咨詢的深入,你會發現這個家庭不斷有創傷性的生活史暴露出來。淑文幼年母親早亡,丈夫也是3歲喪母,前半生受盡欺凌。20年前,淑文結婚,丈夫只管掙錢養家,終日工作或者應酬,即便回家也是醉醺醺的,不理家務事。淑文柔弱的肩膀撐起了整個家。幾年前,丈夫去了外地工作,淑文也沒有反對,因為覺得丈夫人在與不在,區別不大。兩年前,淑文偶然發現丈夫不僅在外面有小三、小四,還有小五、小六。因為不常見到丈夫,也就隱忍至今。時值疫情,丈夫回家隔離,朝夕相處,新仇舊恨,忍無可忍,即將崩潰,于是淑文和丈夫兩人前來尋求幫助。
在此案中,淑文因為情緒問題前來咨詢,她覺得她的抑郁百分之九十與丈夫有關。丈夫也同意,妻子的抑郁與他多年對妻子的忽視分不開。但是,這只是一個開始。
丈夫即使認為自己是造成家里很多問題的主要原因,但還是覺得妻子需要看書,要有知識,有心結需要表達出來,不要那么隱忍。而且,在妻子還沒有怎么說話的情況下,就倒出了自己創傷性的成長史以及自己的艱苦奮斗如何不易。話里話外,都表達了自己的辛苦和委屈,覺得妻子需要體諒和改變。而妻子一直也在說“我盡量理解他,有些事,你問他,我不好說”等等,這種一觸即發的強烈情緒,以及欲言又止的克制令人印象深刻。
此時此刻,我們看到的是丈夫能言善辯,妻子只要說出一點什么,就會被丈夫打斷。于是,妻子表達愈加困難,丈夫也就愈會說“你需要表達,你需要學習”。

而對于幼年喪母的妻子來說,來不及享受童年,被迫提前成長,在最需要被擁抱照顧的時候就得收起心中的渴望和需要,成為代替媽媽照顧家人的小媽媽。對她而言,凡事都得靠自己,沒有人可以讓她依靠,養成了她不輕易抱怨的習慣,不是不想說,而是沒人可以訴說,也不相信自己重要到有人會愿意聽她的抱怨。她帶著幼年“不抱怨,靠自己”的信念進入了婚姻。從大婚前夜還在打掃房間,到婚后抱著孩子深夜看病,永遠是獨自一個人。當妻子被鼓勵著多說的時候,先生聽著,會插嘴說,“你要多說,我真的不知道你那么辛苦。”

然后,丈夫說,他一直以為家里很幸福,妻子善良賢惠,什么都搞得定。所以,他心無旁騖地去工作,去打拼。在當初一起出道的幾個人當中,他現在是最出類拔萃的。他可以通宵加班,為朋友的事赴湯蹈火。他的努力奮斗,更多的是想改變曾經被看不起的命運,為家族長臉。
妻子幽幽地接了一句:“你的工作很重要,外面的人很重要,唯獨我和孩子是最不重要的。”先生立即又說:“我知道你也很辛苦,我也一直很愛這個家。”
可惜,淑文聽完丈夫的話之后便又沉默了,她一點都不相信這個丈夫愛她。很多年,他們之間就是丈夫滔滔不絕地講、妻子默默聆聽的局面。妻子說:“他說得太多了,做得太少了。”
其間,先生聲淚俱下地表示,他很孤獨,5年前,空降到萬里之外的地方打拼,人生地不熟,同儕的排擠,下屬的不配合。晚上整夜、整夜睡不著,也沒辦法和妻子說,因為“她不懂”“說了沒用,心更煩”。于是,宣泄壓力的方式是煙、酒、性,所謂的外遇女人,他說只是為了發泄。同時,他承諾已經停止了這種混亂的、不道德的性關系。
淑文對丈夫懺悔式的表達也是無動于衷。她的焦慮、抑郁和不安的情緒被高度喚醒,她對這個家20年的忍辱負重背后的所有的價值和意義被丈夫的出軌全部給打沒了。
丈夫的出軌,他的解釋是因為他自己的問題,同時也隱含著某種需要沒被滿足:沒有在妻子身上得到想要的被理解,情緒壓力的被分擔。妻子的怨憤和對丈夫的拒絕是因為她的20年的付出,沒有被丈夫所看到、所珍惜,甚至被踐踏、被否定,內心最深的傷痛是她不值得被愛。
所以,對于淑文來說,丈夫的外遇事件,讓她淹沒在被拋棄的苦水中,她甚至覺得丈夫的外遇是指向她的,是她做得不夠好。咨詢師對這件事的解釋是丈夫用不合適的方式去處理他的情緒壓力,在這個案例里面,外遇(或者說是性)更有物化的、象征化的表達,如同酒和煙一樣,是一種壓力宣泄的工具。這樣的重構,也許能夠緩解妻子的自我貶低感,增強被否定的自我身份認同。

另外一個問題是,妻子總覺得自己是受壓抑的,但是對于丈夫來說,自小同樣有依戀創傷的他也是極度敏感的。妻子一個哀怨的眼神,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或者哪怕是一句中性的評價,都會令他有過激的反應,他說,這會令他想起苛責的繼母。另外,他總強調自己是粗放型的,對妻子有類似潔癖的生活習慣非常地不自在。即使是20年的夫妻,他們的婚姻生活還是需要重新磨合。
很多年來,這個家是由母親和孩子一起組織起來的,缺失了20年的父親,要重新加入這個緊密的母子系統,也是需要費一番周折的。小到生活習慣,比如不能穿外衣坐在床上;大到對初二兒子的管教。一個不被妻子接納的丈夫,是管不了和母親相依為命多年的兒子的。一對不合作的父母,是沒有辦法把孩子引導到正向的軌道上的。這對夫妻,在如何接納彼此,如何合作上面,是需要很多磨合的。但是如果都是各自強調我是如何辛苦,那么就不會從“我們”兩個人的角度思考問題。所以,如果需要改變,不是要求對方如何改變,而是更多地思考如何可以從“我”做起。而且,多想想,什么樣的言行對雙方才是有利的。因為,好的關系都是由“我”變成“我們”的過程。
人在一生中總會遭遇很多無法預見的不如意,但是我們生命之中依然有一種復原力,一種韌性,來抵抗歲月的刀劍風霜。所以,即使童年遭遇貧窮、饑餓、被遺棄、疾病等重大創傷,也有三分之一的人依然能頑強地活下來,靠的就是這種復原力的力量。這個家庭也是,雖然有很多的創傷,但值得欣賞的是夫妻倆具有高度的反思能力,和愿意去調整、愿意去接受彼此影響的意愿和能力。
最后,丈夫流著淚說:“在外晃蕩了20年,我想回家了。”妻子同樣流著淚說:“我還是愿意給你一個機會的。”
生活不是小說,他們有這樣的心愿,只是萬里長城的第一步;但不管怎么講,跨出第一步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