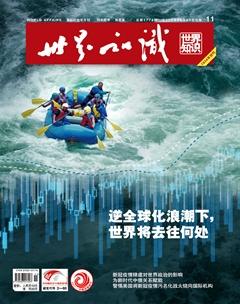警惕美國將新冠疫情污名化戰火燒向國際機構
葉強

位于瑞士日內瓦的萬國宮是歷屆世界衛生大會舉辦地。受新冠疫情影響,2020年的世衛大會以視頻會形式舉行。
今年上半年,面對新冠疫情這一嚴重的全球大流行病,美國一些反華政客相繼發表指責、詆毀中國的言論,拋出所謂疫情“中國責任論”。個別國家的媒體、律師和智庫隨之起舞,推波助瀾,開始炮制針對中國的“索賠訴訟”,甚至挑動更多國家調整對華政策。現在,這場由美國蓄意挑起的針對中國的輿論戰、外交戰、法律戰正在向國際機構蔓延。受美國唆使,澳大利亞挑頭推動拋開世界衛生組織發起所謂的“國際調查”,欲拉攏歐盟支持其“調查”草案付諸世衛大會表決。然而,歐盟對這一草案并不買賬。
在5月18至19日召開的第73屆世界衛生大會上,由中、俄、歐盟等共同參與的新冠疫情應對決議草案(A73/CONF./1 Rev.1)以協商一致方式獲得通過。中方倡導的在疫情得到控制后由世衛組織主導、堅持客觀公正原則全面評估全球應對疫情工作、總結經驗、彌補不足等主張在決議中得到充分體現,美、澳等國企圖綁架世衛大會的圖謀未能得逞。可以預料的是,一些國家不會就此善罷甘休,他們將以執行世衛決議為名,故意曲解決議精神,繼續把科學問題政治化,或者另起爐灶,利用其他國際機構和多邊場合對中國進行污名化指責,這些需引起我們的重視和嚴肅對待。
利用國際司法判決和仲裁裁決
至5月中旬,美國國內至少已有八起以疫情為由向聯邦法院起訴中國政府的案件。但美國國內法院受理以外國政府為被告的案件面臨著美《外國主權豁免法》所載明的、國際公認的主權豁免原則的規制,恐怕很難無視該原則、枉行管轄權。然而回顧歷史卻也可以發現,美國為實現其政治目的,存在繞過國內司法管轄權障礙的政治操作。1979年“伊朗人質事件”后,美國出現大量以伊朗政府為被告的案件,這些案件也面臨美國法院沒有管轄權的情況。但美國政府扣押了巨額伊朗資產。經阿爾及利亞調停,伊朗同意設立一個特別法庭解決賠償和債務問題;美國則同意撤銷所有在美國國內法院起訴伊朗的案子,解除對伊朗資產的凍結。截至1982年1月,“美—伊求償法庭”收到約4700起美國公民的求償起訴。顯然,“美—伊求償法庭”的“成功實踐”可能促使美國一些機構和人員試圖將國內訴訟轉化為國際求償。
此外,國際法院(ICJ)能否僅僅依據《世衛組織章程》(Constitution of the WHO,或譯《世衛組織法》)第75條作為唯一管轄權基礎受理會員國間訴訟案,是又一懸疑問題。中國作為世衛組織會員國,接受了《世衛組織章程》,但并未接受國際法院的任擇性強制管轄權。因此,對于第75條所稱的“涉及本章程解釋或適用的爭端”可“依照《國際法院規約》”提交法院解決的規定如何進行解釋,成為確定會員國在國際法院被訴風險的關鍵問題。而國際法院在這一條款解釋問題上尚無先例可循,因此我國仍需審慎對待。
值得注意的是,英國保守派外交政策智庫亨利·杰克遜學會(Henry Jackson Society)和一些國際律師提出利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項下的仲裁機制問題。近年來,公約項下爭端解決機構出現擴權傾向,對自身管轄權的界定有擴大化趨勢。因此,將疫情防控有關問題“包裝”成關于公約條款的解釋和適用爭議,從而訴諸公約《附件七》強制仲裁程序,并不困難。國際海事法學者米倫教授(Alina Miron)就指出,疫情期間某些港口的通航管制措施可能與國際法下的義務不符,公約第24、25條規定了沿岸國在領海范圍內對外國商船無害通過權及駛入港口的規制權和義務,并確立了對船舶國籍的“無歧視原則”。因此,一些國家政府主管部門為防控疫情頒布的臨時條例中若根據疫情高、中、低風險國家對外國船舶進行分類管理,針對不同船籍或船舶來源國施加不同的航行或入港管制措施,可能會被視為違背“無歧視原則”。
利用所謂國際調查委員會
中國主張和支持的全面“評估”(review)全球應對疫情工作,與部分西方國家觀念中的國際“調查”(inquiry)是不同的概念。在理論上,調查本身是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一種重要方法,在實踐中經常用于確定具有爭議的事實問題。《聯合國憲章》明確將調查列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作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支持符合《憲章》宗旨和原則、由聯合國主導的國際調查工作。
近年來,部分西方國家打著“人權”“正義”旗號發起的所謂國際“調查”,背后藏著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例如,一些國家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的“調查”提案經常是以“人權”為由干涉聯合國會員國內政,導致人權理事會在表決時陷入分裂。不僅如此,個別國家甚至習慣于繞過聯合國框架,以國際“調查”之名行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之實,美、英為入侵伊拉克就編造了所謂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證據”,從而要求伊拉克配合國際“調查”。諷刺的是,伊戰之后的事實表明,伊拉克早已停止研發和制造化學武器,并銷毀了大部分庫存,剩余庫存還是從歐美國家進口的,核武器和生物武器的證據則完全沒有找到。
在這個意義上,美、澳等國此前所鼓吹的所謂“國際調查”,就是先入為主地把疫情問題設定為中國與西方的“爭端”、是對西方的“侵權行為”,最終則是為所謂“侵權責任索賠”服務。本質上就是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把中國放在被告席,事先“推定有罪”,然后通過所謂國際“調查”來尋找“證據”,把國際調查政治化、對中國進行污名化。這樣的“調查”完全是開歷史倒車,與國際公平、正義和法治不沾邊,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接受。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本屆世衛大會通過的決議中所使用的是與中國主張一致的“評估”(review)一詞,沒有出現一次“調查”(inquiry)字眼。而在會后西方媒體大部分報道中,都被曲解為“世衛會員國一致同意國際調查(inquiry)”。顯然,堅持好和維護好本屆大會決議精神,防止一些國家故意扭曲而發起所謂“調查”,在未來不能松懈。
利用國際司法機構的咨詢意見
發表咨詢意見是當前不少國際司法機構的基本職能。這一職能的存在并非為了解決國家間爭端,而是為了回答有關國際組織提出的“法律問題”。咨詢意見在國際實踐中的一個潛在問題就是容易突破“國家同意”這一國際法基本原則,成為一國不經另一國同意就將政治外交爭議交由法院闡述是非曲直的“簡便工具”。以國際法院為例,法院可以根據聯合國大會、安理會決議或世衛大會等專門機構決議發表咨詢意見。在歷史上,至少有兩個咨詢案的提出都被認為與世衛組織的工作職責有關。咨詢案的提出通常僅需聯大或聯合國專門機構會員國簡單多數投票即可實現。在當前個別國家圍繞疫情問題與我國外交對立日益嚴重情況下,特別需要防范個別國家利用特定國際組織尋求司法機構咨詢意見,為“中國責任論”尋找“法律依據”。
在美國挑動下,個別國家與我國圍繞地緣政治、經貿、科技的外交、輿論、法律斗爭日趨激烈,企圖以國際話語權和法律訴訟等方面的優勢打壓我國主權權利、安全利益與發展空間,并使我國長期承受道德、道義上的壓力。對此,中國不能放松警惕,要堅決遏制誣告濫訴,同時要秉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攜手抗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