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播+"新形態及其傳播本質
王天一 孟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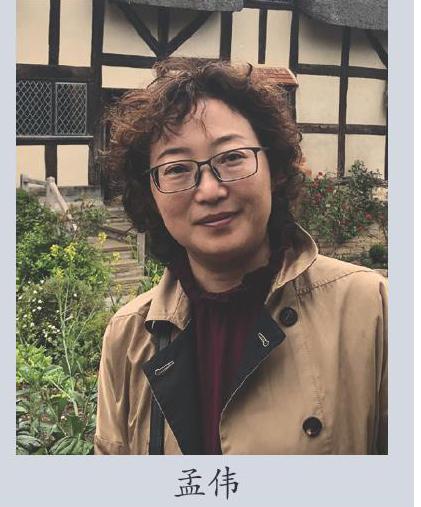
【摘要】隨著媒體深度融合,跨界發展成為檢驗媒體生存和發展的試金石之一。廣播與其他行業的跨界發展,或者其他行業與廣播的融合交互,促使廣播進入一個機遇和挑戰并存的“大音頻”傳播語境。本文從“廣播+”的新形態入手,探究其背后的深層邏輯,從聽覺傳播本質的延展、對個體日常生活的深度參與和對社會治理能力的提升這三個方面進行觀察分析,探討“廣播+”的傳播本質與核心優勢,闡述新時代廣播的媒體價值與發展潛力。
【關鍵詞】廣播+ 媒體融合 聽覺本質 共享 社會治理
【中圖分類號】G220 【文獻標識碼】A
隨著互聯網經濟的蓬勃發展,跨界(crossboundary)成為活躍在人們社會生活中無處不在的熱詞之一。與媒體相關的跨界研究在2010年前后較多出現。所謂跨界,就是對既往傳媒業固有的業態邊界的打破,包括傳播者的跨界、傳播渠道的跨界、傳播內容的跨界、產業資源的跨界等等。①在此基礎上提煉出跨界整合的概念,即媒體要超出自身的范圍來實現更大范圍內的社會要素和產業要素的重新組合,②跨界融合與媒體融合的研究相互交叉滲透,區別在于媒體融合是各要素在媒體產業內的融合,跨界融合則是從媒體產業向外擴散,體現出媒介向其他領域滲透和社會媒介化的過程。
當前,新技術力量驅動下傳媒業邊界消解,主要體現在三方面:公共信息生產領地邊界的模糊、媒體渠道邊界的侵蝕、媒體產品與市場邊界的模糊等。③媒體開始像水和空氣一樣滲入到其他不同產業形態和社會領域中去,成為社會融合的催化劑。④憑借技術手段與媒體自身屬性的結合,媒體可以嵌入到各類社會行業中,推動社會媒介化進程并構成新的信息傳播形態。
過去幾年,就廣播媒體而言,打通線上線下運營渠道,聯合實體消費開展線下活動,實現“廣播+”;整合音頻、視頻、圖文、線上互動等多種制作和傳播手段,在內容生產環節跨界;在金融、體育、教育、親子、健康、汽車、電競等產業領域發揮廣播優勢,以服務為導向,在垂直領域實現產業的跨界發展。廣播媒體跨界的直接動力多來自媒體運營和生存的壓力,這種跨界本身對于傳統媒體的傳播本質、對于媒體的社會參與價值、對于媒體與日常生活均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又將如何影響媒體未來的發展趨勢?探討這些問題,除去媒體新技術對于媒體自身的重大影響,似乎更應該思考廣播跨界背后的深層傳播機理。
一、“廣播+”中聽覺傳播本質的延展
廣播的發展,拓展了人們以“聽”為主的感官體驗,回歸了人們對于“聽見”的本質需求。法國作曲家皮埃爾·舍費爾(Pierre Schaeffer)將聽覺行為分為四種模式:傾聽(Ecouter),指有意識地辨別聲音的來源,將聽覺指向某一事物,從而獲取聲源的某些信息;聽聞(Quir),是基于聽覺的生理感知,被動地接收聲音,缺乏對聲音內涵意義的理解;聽取(Entendre),強調在聽的過程中有意識地接觸想聽到的那個聲音,對聲音進行特定條件的選擇;聽懂(Comprendre),指通過聽覺理解事物的信息,強調聲音作為符號的意涵。⑤廣播在現代音頻技術支持下提供給受眾多樣化的聽覺體驗。媒介的人性化進化趨勢讓廣播模仿了人類口語傳播時代自然的交流方式,人類早期的神話、傳說、歌謠等敘事活動及其聆聽方式也在廣播中得到重現,因此,確如美國媒介環境學家保羅·萊文森(PaulLevinson)所說,廣播因聽覺傳播的特性依然占據著媒介生態位⑥。基于這種音頻本體地位的發展,廣播有能力重建個體與社會的關系,從而發揮出更深遠的社會文化影響力。
2018年4月,北京廣播電視臺與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和繁星戲劇村進行跨界合作,共享各自的資源優勢,實現了廣播聽眾和話劇觀眾的雙向導流。劇院和電臺是如何在各自不同的領域中找到合作與發展契機的?我們回到廣播發展早期,轉播或者直播戲劇、戲曲、音樂會等曾經是廣播傳播的一類重要的節目內容。1950年2月,原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錄制并播放了新中國第一部廣播劇《一萬塊夾板》,開始了以音頻的方式闡釋戲劇的靈魂的實踐。從一般的認識上來講,盡管舞臺表演的視覺體驗是戲劇的核心,但音頻本身通過聲音的引介,也可以調動起受眾建立在視覺、味覺、觸覺等綜合體驗基礎上的聽覺聯想,形成一個自足的、豐富的內心體驗。廣播與話劇跨界,以純音頻傳播為主導,實現與受眾的接觸。
如果說視覺體驗本身是作為戲劇欣賞的關鍵,那么廣播媒體人在小劇場的表演則讓聲音占據了表演的主導地位。這與傳統意義上對舞臺藝術的理解有所不同,是廣播跨界后對于聲音如何在戲劇舞臺上發揮獨特欣賞價值的體現,是對“看”戲劇這一傳統欣賞方式的一種多元化的延展。這種“看”與“聽”之間相互跨越的嘗試,或許是媒介融合后人類感官體驗融合的一種新的體驗方式。
2019年5月,云南廣播電視臺經濟廣播、交通廣播與云南蘸水戲劇工作室聯合,將廣播讀書節目《月色書香》與小劇場話劇相結合,首創國內“有聲現場劇”,把聲音傳播的要素延展到實體舞臺層面,這可看作是基于媒介屬性本身與舞臺藝術門類的融合,為大眾媒體內容創新提供了源動力,體現了聲音創造的活力。
眾所周知,隨著媒體融合趨勢的推進,內容創新越來越成為媒體間的核心競爭力所在。那么,如何實現內容創新,對于媒體人而言,對于節目形態本身的創新是一種常規形態,在節目形態創新背后的源動力是什么?這個源動力既有用戶需求和用戶自制內容的刺激因素,更有對于媒介本身張力的一種激發,在于與其他傳媒形態、藝術形態的碰撞中實現內容的創新。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隨著媒體的深度融合,媒體介質對傳播內容的影響正在消解,越來越多地整合了所有傳播方式的特性,進一步消除了傳統媒介的邊界。廣播媒體的跨界是主動尋求融合的表現,在媒體介質自有的邊界之外探尋更廣闊的生存空間,拓展媒介滿足人類傳播需要的能力。可以說,廣播的跨界發展,是將聲音從以電臺為主渠道的媒體機構中釋放出來,探索音頻離開廣播平臺的生存狀態。在上例小劇場這個實體空間中,聲音將現實空間和受眾想象空間合二為一,也將聲音本身在廣播中所獨有的互動性、沉浸性和共在感推向現實的話語舞臺視覺空間。音頻特質與視覺特征的結合,對于廣播跨界帶來的內容創新動力至關重要。“有聲現場劇”通過模仿純音頻媒體的表現形式凸顯重聽覺、輕視覺的特性,這是一種大膽的突破,對于一般觀眾而言是一種挑戰。在演出現場,工作人員給每位觀眾都發放了眼罩,希望觀眾閉上眼睛用聽覺感受故事,這種表層屏蔽視覺的方式使觀眾更專注于所聽到的內容,其視覺聯想更具有私人性,卻又把表演者和觀眾置于同一現實空間中,物理上的空間共處,體現了觀眾之間以及觀眾與表演者之間的“共在”。這是一種奇妙的媒體和藝術跨界的體驗,也是私人化與共在感的一種融合,而這正是廣播媒體的本質特性所在。與其說廣播借助舞臺藝術延展了表達的渠道,不如說舞臺藝術借助廣播作為獨特大眾媒介的核心特性,延展了舞臺藝術表達的邊界。
隨著語音合成技術的發展,任何文本都可以方便地轉換成聲音,從這一層面來看,超短文本形成的“有聲讀物”在生活中隨處可見,人工智能(AI)管家、智能音箱等都通過音頻作為入口,音頻成為人們開啟日常生活的隱形鑰匙。由于音頻對其他行業的高度滲透性,即使離開廣播平臺,高質量的聲音內容依然有著介入和影響人們日常生活的能力。
2019年,在浙江廣播電視集團舉辦的“運動嘉年華”線下活動中,其旗下民生資訊廣播的主持人和運動達人、聽眾一起感受運動狂歡,進行虛擬現實(VR)游戲、定點投籃、水上接力等活動,(15)活動同時在“抖音”等平臺進行視頻直播。活動現場、視頻直播與廣播直播間全方位互動,帶給受眾全場景的體驗。浙江廣播電視集團通過各項體育活動線上直播和線下體驗,用聲音加強了與體育愛好者的互動,也讓體育產業成為廣播營收新的支撐點。
2020年2月,在芒果TV熱播的慢綜藝節目《朋友請聽好》從另一個側面顯示出廣播跨界融合的源動力,這是一檔以廣播電臺直播為核心、以聲音為媒介,主打傾聽與分享的慢生活綜藝類節目。何炅、謝娜、易烊千璽三位好友在節目中創辦廣播小站,分享并傾聽受眾的故事,很多觀眾都感慨說:“這是一種很溫暖的感覺。”(16)慢綜藝體現出的生活氣息很容易讓人想起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全家人圍坐在收音機周圍收聽廣播的記憶,感受心與心的交流。
為什么廣播能以這樣一種形式跨界到電視綜藝節目中?核心在于廣播是注重心靈溝通的媒介,具有較強的人文意識。廣播是具有社交性的媒介,節目所復現的正是受眾所懷念的家庭共同收聽廣播的日常生活狀態,同時表現出類似夜話節目的情感貼近性,發揮了廣播的情感治愈功能。把握住廣播音頻傳播的根本優勢,融入受眾的日常生活,是廣播跨界融合的核心認識。
三、“廣播+”與社會治理
1992年由28位國際知名人士發起成立的全球治理委員會提出:治理是個人和公共或私人機構處理共同公共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治理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基礎是協調與合作,并沒有簡單的模式或規則,而是廣泛的、充滿活力的、復雜的進程,處于持續的互動之中。(17)治理的核心在于“善治”,即一種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黨的十九大提出“打造新時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共建共治共享”指明了當前社會治理的方向。廣播作為主流媒體,是連接政府與公眾的橋梁紐帶,肩負著促進新聞信息流動、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營造健康向上的社會風氣、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重任,應積極做好服務人民群眾、引導社會輿論、行使輿論監督的工作。
廣播在社會治理中的跨界,可以在發揮廣播社會責任的基礎上,作為社會治理的主體之一,通過直播談話、公益幫忙、情感熱線等各類節目構建溝通平臺,推動社會共同行動。城市廣播與社區廣播則可以將不同類型的本地化服務與社會治理相結合,如2018年江西廣播電視臺財經廣播與江西省慈善總會聯合打造的全國首家慈善公益廣播,為社會愛心救助開辟了新的通道,為慈善事業提供了媒體保障,顯示出廣播通過跨界融合參與社會治理的強大活力。(18)
整體來看,廣播與政府部門的跨界合作,也是政府向廣播借力進行社會治理的方式,深刻體現出政治媒介化(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的趨勢,即媒介與政治呈現出融合的關系。媒介技術改變了政治傳播形式,使政治信息的表現力增強,同時也為政治提供表達和溝通的平臺。(19)
四、結語
廣播跨界的核心和實質,在于廣播作為傳統主流媒體,深具融合性、創新性的媒體價值,廣播是深具責任與擔當的媒體。隨著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媒體環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傳播始于一聽、一看、一見中的生活日常,感人至深,異彩紛呈。老廣播,新聲音,仍可譜寫新時代華章。
注釋
①喻國明:《2011:中國傳媒產業發展關鍵詞》,《中國記者》,2011年第1期。
②喻國明:《嵌入圈子功能聚合跨界整合——“關系革命”背景下傳媒發展的關鍵詞》,《新聞與寫作》,2012年第6期。
③彭蘭:《正在消失的傳媒業邊界》,《新聞與寫作》,2016年第2期。
④韓立新:《時空轉移與智慧分流:媒體的分化與重構》,《新聞與傳播研究》,2016年第5期。
⑤Pierre Scheaffer. Treatise on Musical Object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7).P80-83.
⑥保羅·萊文森:《人類歷程回放:媒介進化論》,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7月版。
⑦⑧曾少華:《“廣播+”:廣播在互聯網時代的融媒戰略》,《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5年第10期。
⑨《廣東電臺音樂之聲:2019,我們相融相變》,2020年1月3日,“賽立信媒介研究”微信公眾號.https://mp.weixin.qq.com/s/U-OV6KhFbtVhjaNgxV3Upg.
⑩《河北交通廣播:2019年打響四場戰役,取得新成績》,“電臺工廠”微信公眾號,2019年12月27日,https://mp.weixin.qq.com/s/uUqroYFIUp86FyzkllHuNA.
(11)孟偉、宋青:《守正、跨界和高質量:2019年廣播音頻媒體發展概述》,《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20年第3期。
(12)孟偉:《音頻媒體研究》,光明日報出版社,2019年版。
(13)張璐、張蓉:《廣播與出版跨界合作形成有聲閱讀新模式——北京人民廣播電臺<長書天地>節目的<紅案白案>案例》,《中國廣播》,2018年第4期。
(14)《<全民閱讀“十三五”時期發展規劃>發布》,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2/27/c_129421928.htm.
(15)鄧文芳:《體育賦予廣播新的活力》,浙江省廣播電視局網站,http://gdj.zj.gov.cn/art/2020/1/6/art_1228992007_41467059.html.
(16)周詩浩:《<朋友請聽好>打開這檔慢綜藝聽見從前網友大呼治愈》,東方網,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13news/auto/news/china/20200227/u7ai9121363.html.
(17)[瑞典]卡爾松、[圭]蘭法爾主編:《天涯成比鄰——全球治理委員會的報告》,中國對外翻譯出版社公司組織翻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5年9月版。
(18)王平湖、萬芳:《共創·共融·共美開拓慈善事業新局面——江西財經廣播“992.久久愛”上線一周年綜述》,《聲屏世界》,2019年第11期。
(19)王慶:《政治媒介化與黨管媒體的地方實踐邏輯——基于“海口強拆”事件的個案研究》,《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8年第9期。
(本文編輯:李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