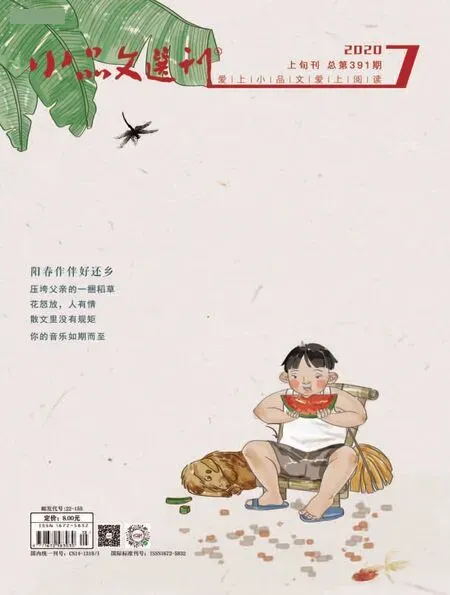穿越叢莽
王川
異地的清晨,一切剛剛覺醒,大亮的天光籠罩陌生的事物,仿佛時間重新開始。

天氣薄陰,霧靄繚繞。沒有幾絲風,卻感到濕潤的沁涼在皮膚上游走。在進入山林之前,我抬眼看了看像是突然高聳到眼前的嶗山,山頂巨大的巖石從云霧中探出來,搞不清楚到底是山在云海里,還是云海在山里。這云海的嶗山,這在海濱矗立了億萬年的嶗山,自一早起,就不想揭開她的面紗,始終在半遮半掩里隱藏著矜持的神秘。
初夏的嶗山被一層厚厚的植被包裹,蔥蔚蓊郁,萬木崢嶸。這在齊魯大地的諸山中并不多見。記得上次來嶗山,摯友中有京師教授者論說此中緣由,稱嶗山乃花崗巖體,形成于白堊紀初始,有地質特稱曰“嶗山花崗巖”,其異于石灰巖處,乃是經風霜雨雪、流水剝蝕之滄桑變化,而利草木衍生,故植物茂密,景色藩秀。我不知此言真偽,但可反證之:我所在城市周邊眾山,盡石灰巖質,狀若饅頭,其頂渾圓,而裸露者眾,多植柏樹和灌木,品類單一,罕見巒壑競秀、纖皴巧斫、臻臻簇簇、樹茂林深者。教授事文學而研地質,莫非此二類相通乎?
尚未收攏游思,身體便已陷入到一團密不透風、東西莫辨的綠海之中。山看不見了,眼前只晃動著濃稠的綠色。幾步之外,繚繞的霧氣遮住了一切。稍頃,細雨又飄飛起來,好像要糅合著這觸手可及的綠一起貼在我身上。山麓的樹木出奇地茂密茁壯,最初的一段行走我們幾乎被淹沒在灌木叢中,橫七豎八的枝條掃過赤裸的胳膊,時常要抬起手臂遮住頭面。許多大樹的根凸起,橫穿小路,裸露于地表,仿佛大地的筋脈。在山里,或在南方的城市,我總喜歡辨認更多的植物,繁茂的、交錯起伏的花樹令人欣悅,那既是世界的一部分,又是世界之外的一部分,在它們面前,你會安靜下來,感覺到兩個世界實際是一個,花與樹通過軀干、葉脈、氣息把它們連接起來,也把你包裹進去。嶗山這地方,是亞熱帶和北溫帶的交接處,所謂亞熱帶之終,北溫帶之始,所以,我看到一些叫不上名字的樹,有著熱帶叢林樹種的特征,長長的葉尖兒垂而朝下,像是總要準備滴水的樣子,植物也有擴充領地的靈性么?但更多的還是那些常見的溫帶灌木叢,在斜坡、峪谷、沖溝、崖縫間擁簇、交疊、纏繞、沖蕩、競逐、蔓延,活生生地泛濫著;而它們下邊的草叢植被更以最駁雜、紛亂的方式,繁茂蓬生著各種或長或短或寬或扁或尖或圓的葉子,開著花的或不開花的,好似一片從未有人闖入的中草藥種植園,沒準兒你還可以采到一些白花蛇舌草帶回去泡水喝。沿途開著一簇簇白花的稠李時常吸引著我的視線,它的花型很像家養的茉莉,卻居然開在樹上。不過,錦帶花更令人矚目,它比稠李還多,潔白、淺粉、紫紅色喇叭狀花朵一叢叢綻放,在綠色植物的襯托下顯得格外奪目。在最初的路段,青澀的核桃、山楂、桃子,時常吸引我們停下匆匆步履為其拍照——那些花朵和果實上懸掛著的晶瑩水珠,一時變作了為人矚目的大自然杰作。各種花草和植物的氣息摻雜在一起,濃郁的香氣撲鼻而來——更像是一種藥香,不容分說地涌入我的肺里,我喜歡那味道。“惟山深多生藥草,而地暖能發南花”,顧炎武如是說。地質、氣候、土壤,造就了嶗山植物的奇跡,既繁茂又質樸,像一個豐富、內向、強大的個體,一個成熟、沉默、深邃的男人。
在山麓腹地,這些雜草與灌木濕漉漉、綠生生地覆蓋了黝黑蓬松的腐殖質土壤,使蒼白或肉紅的巖石偶爾露出一星半點的堅硬質地,甚至逐漸淹沒了所有的路徑——其實根本就沒有路徑,我們完全是沿著一條石塊和石條堆砌成的“路”行走,這當然是人的智慧使然,只有不朽的石頭才能為人在植物輪回的四季深處標識出行走的方向。
德國占領青島時(1897-1914) ,在嶗山開辟了16 條通道,致游人接踵而至。我們選擇的這條路不可能是其中的任何一條。我們只能聽從于石條的引領,不敢涉亂草一步,且腳板盡量踩在翹起的石棱上,以免滑倒,步履謹慎而快捷,因為稍作停留,前邊的人便會像站立的蜥蜴一樣倏忽不見影跡,若是遇到岔路,很可能會迷失于山野莽叢之中。走在最前面的領隊時常喊山,如虎嘯猿鳴,用以提醒后邊的人隨時判斷、矯正自己的方位。他與我們一樣,根本望不到被叢林遮蔽的山峰和天空,但他熟悉通往山頂的路。既然我們的目的并不是去參觀“九宮八觀七十二庵”,我們就應該選擇這樣的方式穿越的叢林、谷地和山脈,這多少更像進入了嶗山的古代。確實,在水泥筑起來空間里呆久了,一旦進入沒有水泥的地方,我就有種穿越感,包括對現世存在的恍惚,就像奧利維婭·萊恩在《沿河行》一書中有意無意中所說的那句話:“有時,獨行徒步者會感覺時光倒流,仿佛自己站在一個另類世界的門檻上……”我跌落進了無邊的叢林之海,好像在一片遠古的時光里沉沉浮浮。
漸漸地,腳下這條石板路已很難再定義為路,隨著坡度的增高,大多地方失去了路的形態,更像是一堆一字排列、隨便丟棄的亂石崗。然而又的確是一條路,也許曾經是要在這山溝里修一條延伸至山頂的石板路的,由于雨季水量豐沛,原本靠下滑的力咬合擠壓在一起的石條,被一瀉而下的山洪沖亂,泥漿變成了潤滑劑,修路者只好放棄了進一步的努力。這倒為獨辟蹊徑的登山者提供了便利,他們對路本沒有什么過高的要求,包括對世俗的人生之路。
盡管水沖雨打,這石條路確乎仍是“新”的,我疑惑它貼土的一面和鑿痕之間為何沒長滿青苔,莫非不久之前這里果真是人跡罕至的叢莽?不,這石頭下面一定隱藏著一條年歲久遠的山間小徑。我不明白在這半原始的山林中鋪設石徑的意義,它不像是城市舊街巷里的經年石板路,被踩踏、車碾,被人間的歲月磨洗——越是光可鑒人,越是容顏蒼老,會保留很多追憶和回聲,會記住很多悲喜與蒼涼……而這匆匆而過的石板路不會被誰記起,它們只能與寂寞的山林相伴,在天空下、在大地上慢慢地變成粉末,最終化入黝黑的泥土,成為植物的營養、螞蟻和蚯蚓的巢穴。那個時候,我們早已消失。然而,它卻給了我們一次“尋異鄉”“走異路”、在泥濘的雨中攀登嶗山的機會,并讓我再次感知到時間在城市與莽野中所具有的截然不同的流速;短暫和悠長,單純與重復,更在時間和空間中鋪設了不同的路,我們時常喜歡在其間來回挪移,既要在輕度的冒險里觸摸生命短暫而單純的“突圍”,又要在庸碌的日常中服從命運悠長而重復的安置。這大概就是所謂生命與生活的語境吧,在嶗山兩天的跋涉中,我看到了它們交疊的折光在我心中不停地掃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