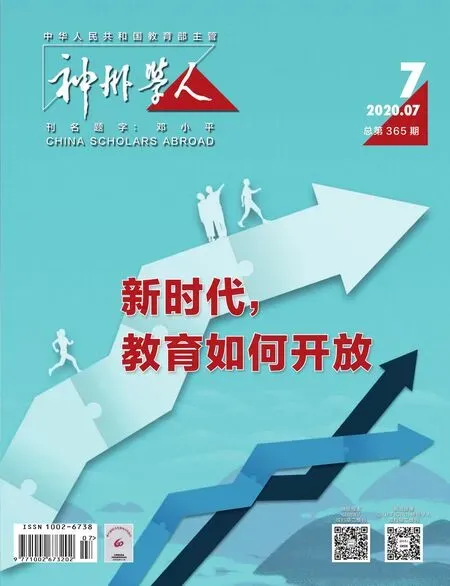海外中醫藥發展的追夢人
文| 李文臣
1970年夏天,王海東出生在一個中醫世家。他的母親是一位中醫大夫,對于中醫,王海東最初的印象就是經常會有患者來家里找母親看病,后來他才逐漸知道母親給患者看病用的方法是中醫的“四診”——望聞問切。耳濡目染,王海東從小就接觸到《中醫三字經》《藥性賦》《湯頭歌》等中醫書目,并時常誦讀。
1996年,26 歲的王海東遠赴澳大利亞求學,隨后幾十年間,他在海外始終沒有離開自己熱愛的中醫藥領域。

1997年3月,王海東在堪培拉理工學院為第一期中醫班學員授課
中醫路上三部曲
1988年9月,王海東以優異成績考入遼寧中醫學院(現遼寧中醫藥大學)中醫系中醫臨床專業。大學期間,王海東的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多次獲得獎學金和各種榮譽稱號。1989年9月,王海東通過競選擔任了校學生會主席。1993年7月,王海東以排名第一的成績留校。1995年,他作為 青年骨干被選派參加由大學舉辦的英語進修班。從那時起,到海外發展中醫藥的夢想在他心中開始萌芽。
1996年11月,王海東應邀赴澳大利亞堪培拉理工學院訪學,作為當時澳大利亞最年輕的中醫界訪問學者,他擔負起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中醫藥課程的建立與發展任務。經過持續努力,1998年,王海東與弟弟王海松兩人一起推動建立了被澳大利亞政府承認的中醫文憑課程,填補了當時中醫教育在澳大利亞首都地區的空白。2006年,在學校的大力支持和有關單位資助下,他們又成立了澳大利亞國家中醫藥發展中心。在此期間,王海東積極促成由遼寧中醫藥大學承辦的、中華中醫藥學會主管的中醫藥學術刊物《中醫藥學刊》海外版的合作發行等一系列工作。
中醫藥的療效是其生命力的根本所在,從2001年起,王海東開始進入澳大利亞中醫臨床領域,他經常組織國內專家交流,還雇傭當地中醫師,并帶動中醫學員一起工作。經過幾年努力,他建立了覆蓋堪培拉市南中北區的澳大利亞首都中醫健康中心連鎖機構(簡稱“首都中醫”),成為澳大利亞頗具規模和信譽的中醫醫療服務機構。現在,“首都中醫”已為數以萬計的當地民眾提供了中醫診療和保健。這一實踐,大大提高了澳大利亞人對中醫藥的認知。
躍身中醫藥產業濟滄海
當一名中醫是王海東的夢想,但他的夢想不止于此,他立志要推動海外中醫藥產業的發展。然而,創辦或經營中醫藥企業就意味著進入了商界,風險極大。王海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為更好地管理和運營企業,王海東開始攻讀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專業碩士學位。之后,隨著中醫藥產業化發展工作的不斷推進,他一方面積累了不少管理方面的知識,另一方面又逐漸發現自己在中藥領域的知識儲備不足,于是萌生了攻讀中藥學博士學位的念頭。恰巧,時任南京中醫藥大學副校長、中藥學專家蔡寶昌教授訪問澳大利亞,了解到王海東的想法,建議他讀自己的博士研究生。通過幾年努力,王海東獲得了中藥學博士學位。
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以下簡稱“世界中聯”)副主席兼秘書長李振吉曾對王海東說:“你想讓中醫藥走向世界,就要真正了解中醫藥,一定要深入到企業和機構任職一段時間,才能了解中醫藥產業發展的實際并產生更多體悟。”
為了更好地用實業推動海外中醫藥發展,2008年王海東來到國內最大的中藥配方顆粒生產企業——江蘇江陰天江藥業擔任副總經理,當年負責分管的外貿銷售業務雙倍增長。之后,他又出任南京中醫藥大學產學研基地南京海昌藥業總經理,出色地完成從制藥機械到中成藥相關企業的收購工作,為公司節省大量并購資本。同期,王海東還作為中國南京中藥飲片質量標準國際論壇秘書長,成功組織了由南京市政府主辦的首屆中國南京中藥飲片質量標準國際論壇。
為了更進一步增加自己的實踐經驗,2013年8月,王海東受聘于馬應龍藥業集團,負責組建馬應龍研究院并兼任馬應龍連鎖醫院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在此期間,他提出多專業一體化、標準化、信息化和國際化的四化一體管理發展模式,獲得武漢市“黃鶴英才”榮譽稱號,并得到獎勵資助100 萬元。他將大部分獎金奉獻出來,用于助力企業后續發展。其間,他還幫助企業成功融資3000 萬元,解決了當時企業的迫切需求。
推進中醫藥公益結碩果
用發展中醫藥方面的公益事業,來推動海外中醫藥發展,是王海東的又一條追夢之路。
成立一個國際性中醫藥組織,是王海東實現推動中醫藥公益發展的首要選擇。2016年,在世界中聯大力支持和王海東的努力推動下,世界中聯中醫藥國際化品牌研究專業委員會在湖北隨州正式成立。中醫藥國際化品牌研究專業委員會的成員包括來自世界不同國家很多中醫藥和非中醫藥領域的專家、學者和企業家們,大家憑借著對中醫藥事業的熱心、情懷與奉獻精神而不斷努力著。
抓好中醫藥品牌是王海東的公益理念之一。中醫藥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也是民族的瑰寶。近些年來,隨著國家經濟不斷發展,中醫藥在技術、產品和服務等方面的需求越來越多,希望在海外更好地樹立中醫藥形象的呼聲也越來越高。王海東說,如果不好好發展中醫藥,我們就無法堅守這一寶貴財富和優良傳統。“我們必須做出能夠凝聚大家智慧和才華的事業。”
王海東逐漸堅定了自己的想法:要從打造品牌的角度出發,更加注重品質、注重標準和質量控制。
2001年,王海東組織協調相關機構共同拍攝完成《當東方與西方相遇》(East Meets West)中醫藥主題電視片,發行到世界6 個國家和地區。2004年8月,作為堪培拉國際中醫藥論壇秘書長,王海東聯合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堪培拉大學、堪培拉理工學院與遼寧中醫藥大學、南京中醫藥大學、云南中醫學院合作,共同舉辦首屆堪培拉國際中醫藥論壇。
最近,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中,王海東還在網上開辦中醫抗疫公益講座。疫情在澳大利亞暴發以來,他還為當地人免費提供中醫藥抗疫咨詢服務。
中醫藥發展理論思考有建樹
理論是最有價值的貢獻,編著書籍和撰寫文章,也是王海東的重要探索。
王海東先后編著出版《中醫藥國際化之路》和《做自己的健康管家》兩本書。最近,他應中國駐澳大利亞使館邀請,撰寫《從中醫抗疫的實踐談中醫藥海外發展問題》一文。王海東認為,這次抗疫的臨床療效觀察顯示,中醫藥總有效率達到90%以上,能夠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促進恢復期人群機體的康復。一時間,中醫藥在全球范圍內得到廣泛關注。然而,這還不能說明中醫藥被世界認可了,事實并非如此簡單。
王海東說,在澳大利亞,中醫藥發展的外圍環境相對較好,從2000年維多利亞州立法,到2012年7月1日澳大利亞全國立法,中醫在法律上取得了和西醫同等的地位。中醫的地位得到承認,也提升了與西醫的競爭力。然而,這次疫情期間,中醫藥的運用在澳大利亞仍然沒有成為主流。當地中醫機構聯合國內頂級專家舉行的新冠肺炎治療國際學術交流會,也主要集中在華人范圍內,影響有限。
王海東認為,中醫在海外仍無法充分發揮作用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首先,中醫藥品質沒有做到位。如中藥產品,從源頭種植到中草藥,再到中藥飲片及配方顆粒,乃至中成藥等相關產品,總體水準不高,與世界的期望存在差距。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商業發展比較完善,無論從內在品質要求,還是外在設計包裝,到品牌打造等,標準都比較高。相比之下,目前的中醫技術和服務等,從內到外,再到品牌打造等,各個環節都相對薄弱。
第二,法律法規方面存在差異。國內有中醫藥法,國外一些國家也有中醫方面的立法。但是,國外有關中醫藥方面的宣傳包括廣告等都會受到限制。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中醫藥雖在中國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效,但在很多國家無法大張旗鼓地宣傳。一方面因為沒有相應的中醫藥治療標準,另一方面也沒有足夠的有效數據進行科學支撐。另外,西醫藥作為西方國家的主要治療手段,對外來醫藥多少會有一些限制和約束,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醫藥的影響力。
第三,文化差異因素影響。東西方文化的巨大差異,讓發源于中國的中醫藥和源自中國的傳統文化,無論是作為一門學問還是一項技術,都不太容易被外國人所接受。在中國,中醫藥在治病和養生保健方面都很容易被人們接受,這是骨子里文化傳統沉淀而成的。國外是缺少這樣的文化背景和底蘊的。因此,作為源于中國傳統文化的中醫藥,要想更好地走向海外,繼而生根、開花、結果,還需要比較長的時間和過程。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期間,王海東堅持每周進行“中醫與健康”線上公益講座
第四,合作示范效果不理想。多年來,中國一直探索海外中醫藥發展之路,包括建立多種形式的合作基地、中醫中心,以及合作項目等,但總體效果不理想,合作的可持續性不強。這其中牽扯多種因素,體制、人員、內外政策,等等。總之,國際合作目前沒有給海外中醫藥發展帶來更大的支撐和影響力。
第五,人才缺乏。多年來,為讓中醫藥更好地走向海外,國家一直在努力。但是,具備相應能力的復合型人才仍非常緊缺。他們既要具備比較扎實的專業基礎和素養,又要擁有國際化發展意識和視野,還要有機會赴海外參與實踐。培養大量這類人才,仍然任重道遠。
為了海外中醫藥的發展,王海東說,自己會堅持下去。